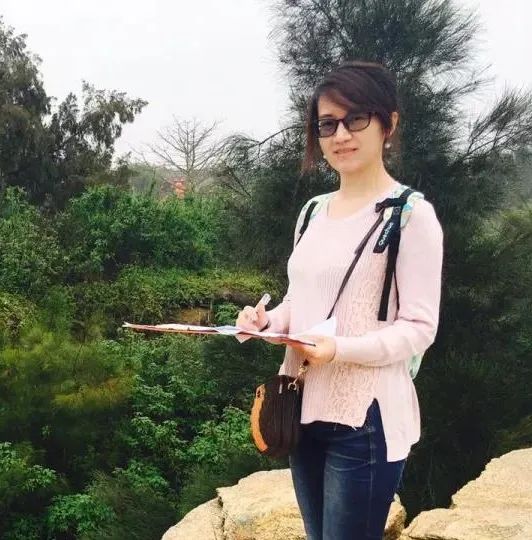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中华遗产》2020年第12期,经期刊同意转载发布。
作者:吕宁、安程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兵锋直指长安。已是古稀之年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亡四川,终于进入成都。街道平静如昨,一位僧人正立在街头,有条不紊地施粥济众。李隆基顿时百感交集,下诏为高僧建寺,赐名大慈寺。从此之后,无数高僧大德、文人墨客由北方南下,以成都为中心,让大唐帝国的佛教艺术,在那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不是第一次了。自魏晋以来,佛教的发展就屡受中原动荡的波及,天下饥乱、四方多难,而“蜀中丰静”、僧侣云集。成都于是开始取代长安、洛阳,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在北方洛阳龙门石窟开凿被迫中止之时,中国石窟寺在蜀地,迎来了又一次发展高峰。
说到石窟,世人无不赞叹莫高窟之瑰丽,乐山大佛之雄壮,云冈石窟之鬼斧。然而这绝世风华的背后,是西域的几代财帛,是北魏皇室的几世庇佑,更是地方的数年盐税的支撑。集天下英华于一域,必然耗资不菲。直到石窟沿着蜀道进入巴蜀,画风忽转,帝王将相的巍峨堂皇,变成了“市民”的虔诚低诵。安岳石窟,就是这样一个散落在荒郊、乡野的佛国。
扼守成渝古道要冲的安岳,是个面积只有六分之一个北京大小的小县,却拥有数万余尊大小造像(含圆雕石刻)。从窟龛形制上,这里不拘一格,大像窟、殿堂窟、摩崖龛、环岩龛,甚至僧房窟,都有出现;从文化特征上,密宗、禅宗、净土宗以及儒释道文化,都有表达。无论是石窟总量、分布密度,还是造像技艺、文物价值,都堪称全国之最。与其它石窟最直接的不同在于,安岳石窟并不是一座石窟,而是一个包括了207处石窟寺在内的石窟群,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卧佛院、千佛寨、圆觉洞、华严洞、茗山寺、玄妙观、孔雀洞、毗卢洞这八处(前七处在国保系统中合并称为“安岳石窟”)。或倚崖取势,大窟大像雄伟壮观;或因地制宜,小龛小像密如蜂房。全县32个乡镇之中皆有分布,不说随处可见,也算得上是星罗棋布了。
何以至此?要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说起。

安岳县孔雀洞孔雀明王龛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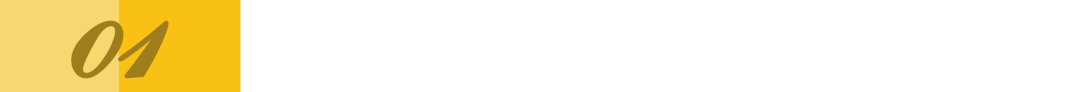
“富民”的崛起
北宋元符二年(1099)秋,眼见这一年风调雨顺、仓廪殷实、家族人丁兴旺,世代居于安岳并虔诚信佛的杨正卿一家人,决定出资开窟造像,为观音重塑金身,偿“厥祖旧愿”。建造和雕刻持续了整整八年,至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方才大成。杨氏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水陆斋会,“开四大部经”,观者云集,盛况难得一见。时至今日,我们在被称为圆觉洞之冠的“莲花手观音窟”内,除了正中高度超过6米、手执莲花、璎珞花冠雕刻异常细腻华美的观音像外,还可以看到侧旁杨氏一家六口的供养人像——第一排的杨元爱、胡氏与常人等高,推测为杨氏长辈,二人身着宋代百姓常见的圆领窄袖长袍和直领对襟配百褶裙,神态慈和虔诚,双手捧着香炉等物做礼佛状;后面则依次站着“女功德主马氏”、“男功德主杨正卿”等四位晚辈。莲花手观音窟正是安岳石窟最典型的“户营”石窟代表。
纵观全国,若以出资“甲方”而论,石窟寺可分为由皇室、地方政府拨款建造的“官营”、由寺院或高僧募捐的“僧营”以及由老百姓自掏腰包建造的“民营”三大类。官营石窟一般选址在政治经济城市附近或交通要道附近,耗资和规模都相当可观,其背后往往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僧营石窟仰赖寺庙经济水平和当地信仰风气,有时也会和官营结合。这两类石窟在安岳都比较稀少、前者甚至基本没有发现。安岳石窟多为民营,这又分为以一户或同族为单位的“户营”和以结社、结会为单位的“社营”。而无论是居于主要地位的“户营”还是少量的“社营”,背后都是颇有家资的“富民”。
“富民”,又被称作“富室”“富户”“富人”“富姓”“多赀之家”等。按照中国经济史学者林文勋教授等人的观点,富民主要是乡村经营土地的富裕者,也包括工商业致富者。他们的身份是“民”,拥有财富,没有政治特权,同时还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富民”这个称谓古已有之。但在中古之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富民”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社会稳定的中间层与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尤其在乡村,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扩张宗族势力……都离不开“富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富民”就是近代意义上“市民”阶层的雏形。
正是这个阶层,支撑着蜀地成为唐宋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颗明珠:唐朝时,成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会。到南宋,四川已经超过江浙,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整个四川的粮食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茶产量占全国一半,商税额全国前二十的城市,四川有六个……显而易见,蜀地的“富民”格外地富。而安岳所处之普州属剑南东川十三州之一,在整个唐宋,剑南道的经济规模基本都位于巴蜀之冠。剑南东川以盐业、矿业、手工业和商业著称,普州则是巴蜀地区重要的葛布和绢产地,其境内盐井就有31处之多,数量为蜀地之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普州的户数在贞观年间为 25000 余户,在开元年间增长为32000 余户、67000人,到了天宝年间上升到74000人。这种稳定缓慢增长的态势,既不像益州(成都)、邛州(邛崃)那样户数人口一时激增,也不像渝州(重庆)、荣州(荣县)那样户数人口都锐减,更没有像果州(南充)、陵州(仁寿)那样出现户数激增而人口锐减的反常现象。这反映出安岳的社会经济相当之稳定,虽然经济的绝对水平不如成都,但对于佛教而言,这样安稳的地区环境,反而是难能可贵的、最利于扎根与发展的条件之一。于是,当佛教重心南移、儒释道三教逐渐融合,普遍信佛的风气就在安岳迅速流行开来,“……普人届朔望之期,毕敬毕诚,顶礼三宝,粥粥乎信善也……”,手有余钱的“中产一族”——“富民”,纷纷为信仰出资,开窟造像蔚然成风。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昔日的盛景,可从千佛寨、圆觉洞、净慧岩……的题记中瞥见一角。位于安岳县岳阳镇贾岛村的千佛寨,是安岳众石窟中开创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窟龛数量最多的石窟寺。这里题记众多,早到唐开元十年(722年),晚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虽然大部分内容仅简单交代供养人、时间和造像主题,但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隐匿于正史之外,却是构成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真正的“民”生。
千佛寨第58窟和60窟就颇有意趣。第58窟塑有坐佛一尊,题记刻载“奉佛弟子王天麒同室邹氏……”,第60窟则以解冤结菩萨为主,刻载着“奉佛弟子王天麟同室汝氏……”。明显二位供养人是兄弟俩。这生活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1)的两人,或出自一户、或各自立业,他们感情颇好,相约建造相邻的两窟,或为前程,或为康宁,在此处虔诚地镌刻下自己与妻子的姓名,奉上钱财、祈求祝福。想象这样的场景,不由的让人会心微笑。

工匠:无名与出名之间
如果说“富民”崛起是基础,全民信佛是动力,那么,石材和工匠则是安岳成为“中国石刻之乡”的必要条件。
安岳地区的岩石,普遍天然外露,且多为红砂岩、泥岩,石质细腻松软、颜色灰中带暖,是非常优良的雕刻材料。俗话说:“靠山吃山。”当地人自汉代起,就习惯了挖凿洞窟、营建墓穴、垒筑石阙、雕刻画像砖的生活,对凿刻的爱好,又反哺造就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影响力辐射到大足等周边区域。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安岳地区的工匠群体,为整个西南地区晚期的石窟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工匠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中,往往是失声的。川东的情况则稍有不同。转捩点发生在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的冬天。
作为常年在安岳、大足两地进行石窟创作的文昌父子三人,面对大足即将完工的八角形陀罗尼经幢(该经幢现存于大足石刻博物馆内),既欣喜,又不甘。思虑良久,父亲文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拿起刀,在遍是经文的幢身一角,刻下了三人的名字。他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字,开创了此后百余年间安岳工匠开窟造像后的署名之风,这也是迄今发现的川东石窟最早的工匠署名。从而让我们有机会窥见,那些隐匿于造像背后的大师群体。从这处题记开始,150余年间,文氏家族六代子弟,在安岳、大足两地的石窟作品中,留下了17个名字:文昌、文惟简、文惟一、文居政、文居礼、文居用、文居安、文居道、文仲漳……除文氏之外,伏姓、罗姓、吴姓、周姓等家族或工匠,也以同样的方式,刻字留名。统计署名者的籍贯,“东普”“岳阳”“普州”频频出现,无一例外都是安岳的古称。而在籍贯之后、姓名之前,又往往有“镌作”“处士”“攻镌”等字样。据专家考证,“匠人”“镌匠”“镌作”,是自称,体现着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而“都作”“小作”则可能是石刻匠师中的小头目称谓。地位最高的文氏家族,有时被冠以“处士”之名,可能是“未仕之士”的意思。称“岳阳处士”的文惟简,或考取过宋元佑(1086—1094年)年间的进士,是少见的“士人工匠”。
至于他们的手艺如何,无需开口,有作品说话。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吕宁(左图)、王麒(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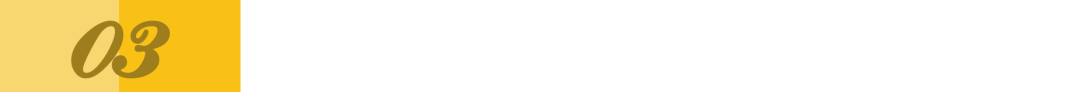
世俗的美感
安岳县石羊镇赤云乡油坪村的厥山上,有一毗卢洞。毗卢洞现存五座洞窟之一的观音堂,内有北宋时期雕刻的水月观音像一座,传说出自文氏工匠之手,被誉为“全国最漂亮的石刻观音像”。

水月观音像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水月观音,是观音三十三变相之一,多与水中月影有关,故名。只见那观音头戴镂空宝冠,身着薄如蝉翼的长裙,袒胸露臂,跷脚而坐,显得风流倜傥,潇洒自如。匠人的雕刻技艺,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轻柔飘逸的彩带,还是行云流水的长裙,都仿佛现实存在一般,真切动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并不流于形式,它依托于创作者对光学和力学原理的娴熟运用,有更深层次的实际意义。比如,观音肩上帔帛垂于足下两侧,与脚踏的莲花石连接,空悬的莲花与下垂的帔帛互为依靠,在生动写意的同时,又不失牢固。再比如,与寻常见到的微闭双眼、视线朝下的菩萨像不同,这尊水月观音作睁眼状,眼珠似乎还可以转动,余光又非常开阔,游人无论站在他的正面还是侧面,都仿佛沐浴着他平和慈爱的目光。一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就这样被手艺人藏进了他的作品中,不露声色。
观音像右下角,有一通明万历年间的装修碑,碑文写道:“大士像于毗卢山之右,森严神妙,有动静语墨之机,紫竹飞篁,有风暗雨露之态,诚人间稀有者”,“盖世佛像无不精研,其最著者,唯观音庵,栩栩如活,飘飘成仙,朗之生敬,望之俨然”。
这尊水月观音像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审美高峰时代,也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时代。安岳石窟在这样的时代下,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宋代的美学、宋人的哲思,在窟中幻化出别具一格的石刻艺术。那里的佛可以拈花微笑,菩萨更是和蔼可亲。前朝宗教与世俗的疏离不见了,他们不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反而充满了人性之美和世俗之美。
安岳县华严洞的“十大弟子”像亦是如此。以半圆雕手法塑造的十尊菩萨坐像,通高4.1米,分列左右两壁。左壁由外到内是贤善首菩萨、普觉菩萨、辨音(观音)菩萨、清净慧菩萨、金刚藏菩萨。右壁由外向内为圆觉菩萨、净诸业障菩萨、威德自在菩萨、弥勒菩萨和普眼菩萨。这十尊菩萨,简直就是宋代安岳人对于“美”的最高表达。她们眉眼柔和、浅笑嫣然,岁月剥离了身上的彩绘,却不曾让五官减色半分。加上镂空的饰花宝冠、颈间的珠串璎珞,以及行云流水的帔巾衣纹,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气质高雅、身份华贵。洞窟崖壁上方,“剪云补衣”“众妙香国”等经变画跃然壁间,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宝塔宫阙无不生动活泼,且极富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这些雕刻,让人能明显体悟到一种有别于云冈、龙门石窟的美感:不同于堂皇大气却严谨拘束的皇家风范,这里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洋溢着“市民”阶层对于美的追求和表达,亲切温暖,活泼生动。哪怕是严肃的涅槃像,也流露出些许“随意”。

华严洞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吕宁
安岳县城以北25公里处八庙乡的卧佛院,有一尊安岳石窟最大的卧佛造像,开凿于盛唐开元时期(也有人认为开凿于贞元年间)。这尊21.3米宽、11米高的大佛,选址在山林掩映之中、溪流水涧之后,让到访者的寻佛之旅,多了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趣味。
卧佛最奇特之处,是他的朝向——头东脚西,呈左侧卧状。据《大唐西域记》载,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国收了关门弟子善贤之后,便“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大般涅槃经》更详细描述了他当时的睡姿:“……于七宝床右胁而卧。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因此,莫高窟、大足宝顶山等绝大多数卧佛,都严格按照佛教典籍,塑造成右卧状。而安岳县八庙乡的这尊释迦牟尼像,却偏偏左胁而卧。
关于其成因的猜想,有一种说法认可度最高,即这块石材虽然体量够大,形状却不满足右卧的雕刻需求,结果,安岳工匠灵机一动,就改成左卧了。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在官方看来可能要掉脑袋的大罪,在民间,就成了信佛、向佛“自由心证”的见证。

©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张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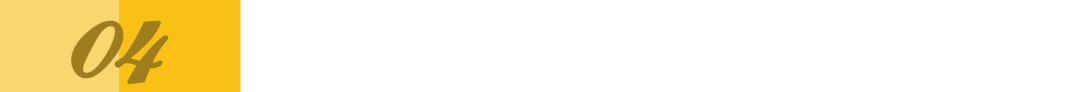
真实的力量
通过“世俗”的手法,表达对“信仰”的追求,除了体现在对“美”的理解上,安岳石窟的另一个特点——真实,也是其他石窟所少见的。
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含蓄内敛、意在言外,“表现”和“写意”是艺术的最高追求,石窟寺与壁画创作也不例外。因此,与西方不同,我们很少能看到直接表达“痛苦”和“死亡”过程的作品,多是以后果或影响来映射,比如死后的极乐世界或阿鼻地狱。
安岳石窟却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这项规则,历史在这里具象成一幅幅平常人的市井百态,甚至出现了真实到近乎可怖的场景:毗卢洞《柳本尊十练图》和千佛寨《药师经变相》就是例证。
柳本尊“十炼”修行图,记叙了自称密宗第六代祖师柳居直的修炼过程。他是唐代乐山人,修持“大轮五部咒”有成后,在川西武阳(今新津县武阳镇)、峨眉、成都、弥蒙(今成都青白江区弥蒙镇)等地设道场,收弟子,弘扬密法。前蜀(907年-925年,五代十国之一)主王建曾授予柳本尊“唐瑜伽部主总持王”的称号。
柳本尊走的是极端苦修的路子,毗卢洞的《柳本尊十练图》,即以高超的造像技艺和成熟的艺术处理,分十组呈现柳氏炼指、立雪、炼踝、剜眼、割耳、炼心、炼顶、舍臂、炼阴、炼膝的场景,如同一本刻在岩壁上的连环画。逐一看去,画面相当写实。
一边,是柳本尊右手执刀,左手将剜下的眼珠,置于跪侍举起的盘内;另一边,他又将左袖卷起,露出胳膊,右手执刀欲砍。剜眼割耳后,虽有佛或菩萨现身作证,并鼓乐齐鸣,但情状之残酷,还是令观者惊心动魄。这并非佛教秘法,而是地道的四川地方性教派——川密,是佛教传播的地方化。这个过程也对四川石窟地方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千佛寨的唐代密宗代表作《药师经变相》,在题材选取上并不少见,但安岳雕塑的真实性却与众不同,且以内容生动和保存完整著称全国。作品将病死、受王法死和被虎、豹、蛇咬死等场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直面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毋庸置疑,这绝非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审美,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创作者以一种直白的力量直击人心,令人感受到对信仰的执着。
从初唐、盛唐的卧佛院、千佛寨、玄妙观、黄桷大佛等,到中晚唐五代的圆觉洞、净慧岩、菩萨湾、灵游院等,再到两宋石窟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孔雀洞……安岳石窟,依靠唐宋时期崛起的四川“富民”阶层,在本地工匠巧手施为之下,沿着佛教入川的传播路线,分布于整个县域的西北至东南。它们灿若星子,但相较于其他集中开凿的石窟来说,其保护、管理和利用的难度,也无疑更大。我由衷地期待,它能借由现实的需求,获得未来腾飞的契机。

相关链接:
【学术分享】基于监测大数据分析的广元千佛崖保护性建筑实际效果研究
作者:吕宁
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综合一所主任工程师。师从吕舟老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古建筑和石窟寺保护研究;在国内外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3个重点国家课题,负责保护实践二十余项,包括保护规划、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修缮设计、文化遗产监测和数字化等。
扫码查看清源–吕宁文章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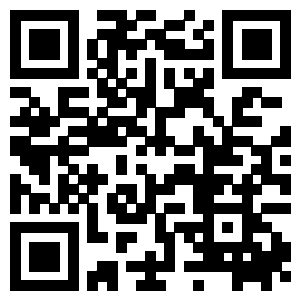
作者:安程
建筑学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者。现为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科研发展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研究方向为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与环境监测、文物风险分析和预测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课题,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劣化风险监测分析技术和装备研发”等7项国家级、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清源–安程文章合集
*本期编辑胡玥,排版廷廷。头图照片©清源文化遗产 拍摄者:王麒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请留言联系清源或邮件bjchcc@126.com。未经同意禁止转载。
清源文化遗产
我们是一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第一线的青年,跟您分享实践思考、学术成果、思想碰撞,以及深入遗产地带来的好吃好玩。
*有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或疑问,直接微信回复公众号。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清源文化遗产):【遗产撷英】安岳石窟:“市民”的佛国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