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带给人的灾难与舆论的混乱,恐怕已经说得太多。作为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实践的积极推动者,我曾向身边的朋友、媒体人征集面向城市规划者的问题。不少朋友都提到,针对类似的疫情,城市规划可以做什么?
因为并未参与过武汉公共卫生设施的规划编制工作,本文只以一个普通市民和城市规划工作者的角度,提供一些泛泛的回答。

1月31日,排队买口罩的居民。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规划与人——口罩来自何处?
城市规划可以做什么呢?所有救命的医生、药材、口罩,我们一概生产不出;所有外卖、快递、测量体温的服务,我们一概负责不起……感觉城市规划师在这种关头只能望洋兴叹、隔岸观火,发挥不出任何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价值。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职工作就是给城市所需的一切活动提供空间。
比如,城市规划师会给一座城市安排工业用地,只有在工业用地上,才能建工厂,有了工厂才能生产医疗设施和口罩。那么一座城市该有多少土地用于生产口罩呢?这就涉及到复杂的产业规划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现在,中国口罩的产能据说是每天两千万只,平均每65人每天可以用上1个口罩,或者一个人平均两个月才能用到1个口罩。
这样一算令人出一身冷汗,但是一定程度上这是必然的,因为产能是根据市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按照社会需求峰值来设计。如果按照社会需求峰值来设计,每天工厂最多可生产一亿个口罩,那么平日就会有大量口罩卖不出去,或者大量机器闲置,长此以往会导致企业破产,这是社会资源和就业者的共同损失。
不仅口罩如此,所有的工业都涉及同样的问题,因此,每座城市该有多少工业用地,是一件复杂而令人头疼的事情,城市规划者每天就是与这样的事情打交道。

许多商场都开始测量额温进出
当然,相比这些把“救命粮”送上门的服务,我们不妨看远一点,看看救命粮是在哪里生产的。那就是农田、果园、菜园。这次很多公众号报道了菜农、果农的损失,令人心里十分难过。农业是第一产业,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靠农业吃上饭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弹药,可能会任人宰割,如果没有粮食,必然是自寻死路。因此,一个国家必须拥有的耕地面积是有下限的,若低于这个下限,粮食对于这个国家就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个下限叫做“耕地红线”,所有关心自己是否吃得上饭的人,都不妨抽时间关注一下中国的“耕地红线”。
说完了一二三产业,我们再看看连接产业和人口的“血管”,也就是中国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在这次疫情的应对中,很多地方采取了“封路”的方式,甚至把路挖断了。看到类似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心情很复杂。隔离是抵御传染病最有效的方式,但是道路本身是国家宝贵的公共设施,造价很高、功能很大,怎么能说挖就挖?运输蔬菜、口罩、医疗设备都需要道路,运输患者、医生也都需要路。这就提醒了我们一点:道路是城市的血管,只要城市中还有人活着,就不能断了给活人输送物资的血管。
以上讲的是城市对于人的影响。那么人的活动对于城市有怎样的影响呢?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感染了新型肺炎,应该做什么呢?凭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第一反应当然是去大医院。可是,考虑到肺炎的感染性,这位疑似患者去往大医院的一路上,就可能感染给许多人;如果万幸这位疑似患者其实并没有生病,那么他(她)到了大医院之后,将遇到许多其他疑似患者,从而暴露在相对较大的感染风险之下。对这位疑似患者本人或者全社会来说,“大医院”的就诊路径都是有风险的。那么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身边几公里内都有一个小的门诊或者医疗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备检测和隔离患者的一切设施与服务人员。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医疗点的存在,如果觉得自己感染了新型肺炎,第一反应是去这个小的医疗点。一旦患者确诊,就会有严密的隔离交通措施,将其移交送往集中的治疗点(大医院)。这样的话,由于医疗点较小,会造访的患者较少,那么到这里之后自己感染的风险也比较小,而抵达它的路径上感染别人的风险也比较小,整个城市的公共环境就比较安全。这样不是比较好吗?(1月24日,武汉市发布了《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7号)》,要求对发热病人进行分级诊疗,减少定点医院的医疗压力。——编注)

夜晚的街道,一位小哥在直播喝酒
可是,现实中我们发现,家门口的“社区卫生站”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就促使城市规划者反思——我们花那么大力气规划小的医疗服务点,政府花那么多精力管理这些服务点,关键时刻这些基层卫生服务却发挥不了作用,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防疫意识的不足。全国各地的防疫动员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开始的,小社区卫生站物资、服务水平长期缺位,一时补不齐,而居民也没有去这些地方看病的意识。于是,这些本可以协助整个城市发挥分区隔离作用的小医疗点,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管理制度的封闭。这里有个“有趣”的案例。笔者的同事是一名“外地务工人员”,大约半年前,这位同事曾经找到自己家附近的“社区卫生站”接种流感疫苗。这样的行为可谓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然而他被拒绝了,理由是“外地户口”。
“户口”这件事对城市生活、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影响太过广泛深刻,以至于所有人提到“户口”自然心有戚戚。可是所有管理人员似乎都忘了,病毒是不讲户口的,以至于医疗服务如果将“外地人”拒之门外,就会给病毒大肆传播的可趁之机。
这就不由得令我们思考,公共服务的根本职能是什么,难道不是服务社会吗?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当公共服务的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区别对待时,影响的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教育、文化、医疗无不如此。可悲的是,这件事却是一个大肆传播的病毒“迫使”我们正视的。
在这次疫情中,我有一个感觉,听到了很多“中国加油!”的口号,可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似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割裂、隔离的城市、社区、小区,在它们的夹缝中,很多“外地人口”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我不由得想,人类防控病毒其实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人分成感染病毒的人和待观察的人,救治前者,隔离后者;二是将人分成本地人和外地人,服务前者,驱赶后者。
再怎么看,都应该采用第一种方式,才能有效地甄别和消灭病毒。然而,“户口歧视”之下,许多个体和集体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们忘了,针对户口而非病毒的区别对待,攻击的不是疫情,而是人。而每个所谓“大”城市的运转都离不开外来人口。

等着接单的出租车司机
更别提所有医院、家庭都在“抢”的医疗物资,生产者是谁呢?几乎全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聚集在大城市或劳动密集型城市,不是为了占资源,而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钱的方式,就是给大城市乃至全社会提供人人需要的服务。
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等同于市民拒绝吃、穿、用。因此,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几乎是来者不拒的,但好像只想用外来人口的劳力,不想为其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因为公共服务需要政府花钱来买。
对于户籍人口,政府只好责无旁贷;对于非户籍人口,就能省则省,能甩就甩。于是,学校、医院都不考虑外来人口的使用需求。直到疫情爆发,政府才会发现,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无法对抗“无差别攻击”的病毒。我不由得希望,在席卷国家、城市的下一次灾难来临前,政府和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允许人用脚投票,平等的公共服务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城市自保机制,缺的不止是口罩
在这次疫情中,还有一些声音在攻击“食用野生动物”。吃野味自然应遭批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这次疫情真的是吃野味引发的,是不是该惊醒更多人:我们的城市真的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今天因为吃野味引发传染病,明天会不会是抽烟,后天会不会是喝水?从个体的行为失误到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之间,有没有什么机制在保护我们?还是说任何人都必须谨言慎行,否则自己一着不慎,就可能引发全社会的动荡?
我想这也是本场疫情中最让人失望、恐惧的一点:本该发挥作用的城市自保机制层层失灵。
从防疫意识的缺乏,到疫情讯息的阻隔,从应对手段的迟缓,到医疗物资的缺失,再到物资分配的不均,更别提“逆行天使”被患者攻击,微商贩卖假口罩了——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仿佛有人故意给病毒作“神助攻”,令人不由得想问:“你究竟搞清自己站哪边了吗?”
原因很简单,太多人习惯了“向上负责,一手遮天”“只管自己,罔顾其它”,而病毒却来自政治链条之外,威胁社会整体。恐怕就像口罩短缺一样,我们没有储备足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来应对忽如其来的恐慌。

执勤的保安
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工作者,我想问,我们该为这些正直又诚实的人规划怎样的城市?有没有可能让城市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遇、服务和尊重,让每个人在其中有权利为自己发声,也有义务听取其他人的声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城市成为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共同体,而非只顾私利、只往上看的一盘散沙?
或许这是城市的真正使命——让人走到一起,从而活得更好。而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
(作者系城市规划工作者,现居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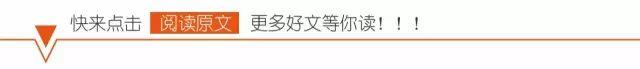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市政厅):“隔离”日志|疫情攻城,一个城市规划工作者的思考
 健康城市:应对新冠疫情专栏
健康城市:应对新冠疫情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