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到位于湖北G县的老家,总会有几次搭乘乡村客车的经历。
回家的路线基本上是这样的:在深圳北站乘高铁到武汉站或孝感北站下车,再搭省内长途客车到县城;或者在罗湖火车站乘火车到武昌或汉口下车,再转省内长途客车回县城;如果选择从深圳宝安机场飞武汉天河机场,同样要搭乘长途班车回县城。不管我选择何种交通方式,都需要先到县城中转——我所在的L镇,是飞机、高铁、火车和长途班车都无法直达的地方。
乡村客运班车接过了从县城到乡下老家这最后一段旅程的接力棒。
G县地处湖北东北部,国土面积26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95万。2016年,G县GDP为260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6亿元,经济发展在湖北的80个县(市、区)中位于第二梯队,居中等偏下水平。
G县县城常住人口12万左右,城区公共交通长期以来仅靠1路、2路两条线路的公交车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出租车支撑(因黑车众多及客源不稳定,出租车数量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城区尚且如此,城区之外的公共交通政府更是无力顾及,由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个体客运联营体便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连接G县县城和乡镇农村的一条条公路上奔跑的17座小型客车,便都来自这些客运联营体——受路况限制,载客量更大一些的客车无法在乡镇道路上顺畅通行。
民间自发组织的客运联营体
去年9月中旬,我因家中事务回了一趟G县。G县的中心客运站是全县所有乡村客车到县城的终点站,每条线路的乡村班车都在这里有固定的停车位置。如我所料,开往L镇的“万山”中巴车依然停在老地方。我在客运站刚刚走下从高铁站开来的长途大巴,就径直坐上了这辆“万山”。
在G县,几乎所有的乡村客运采用的都是这个本省品牌的17座中型客车。这一天是周日,我上车的时候大约10点半,车上只有六七个人,司机,售票员,两位老年妇女,另外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我是车上除司机以外的唯一成年男性。司机和售票员都很面熟。
在“万山”中巴车之前,承担农村客运任务的先后分别是拖拉机、农用三轮、农用四轮,这些车辆都归G县农村的运输个体户所有,这个群体基本上是一群散兵游勇。在驾驶技术方面,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很少有人取得正式的驾驶证;农用车没有客运资质,自然没有办法办理营运证。
车主们各自为政,除了要和跑同一条线路的竞争对手争夺客源,还是交通运政、城管、交警等部门的重点盯防对象。车辆在县城没有固定的停靠点,不得不一边行驶一边下客,车主必须时刻提防“大盖帽”的出现,稍有不慎就会被罚款、吊销证照或扣车,有些类似于“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被罚款和扣车的次数太多,再加上车辆平衡性差、路况糟糕和超速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一些运输个体户入不敷出,不得不把车卖掉,转而谋求别的生计;另外一些懵懵懂懂的人则选择进入,同样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铩羽而归。从司机、车辆、道路到管理,彼时的乡村客运市场都极不规范。
一直到2000年左右,个体运输户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再这样干下去毫无出路,便提出“抱团取暖”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的客运联营体:车主带车加入联营体,车辆必须是正规的客运车型,档次、型号大致相当;车辆统一调度、排队发车,前一班车发车后,后一班车再上客;加强监督,每班车上安排一位司机、一位售票员,司机与售票员不能有亲属关系,两者要相互核对和确认每班车上、下客人的数量和票款,票款收入每天上交联营体;收入由车主共同管理,所有扣除成本后的收益由全体车主平均分配。
事实证明,尽管没有注册法人,但这种公司化经营的联合体非常管用,它的出现,结束了农村客运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无序竞争、自生自灭的恶性循环状态,个体运输户成为稳定的农村客运从业者。从此,车主们一兴俱兴、一败俱败,他们强大起来,在票价制定方面更有话语权,在与大盖帽们打交道时也更有底气。
最终,政府意识到了客运联营体的作用和力量,开始对他们加以引导和规范,包括鼓励他们考取驾照、办理行车证,并为他们组织安全培训、核发线路牌、设置乡村班车固定停靠点等。车主们由“黑”变“白”,他们彻底告别过去的身份,一个个扬眉吐气,有一种成为“正规军”的自豪感。事实上,这些客运联合体的股东们也由此过上了好日子,比更多人提前迈入小康。
上座率不高的班车
从L镇到县城的班车一共五辆,L镇一带的人,几乎都和他们有过交集。所以,胸前挎着印有“湖北省客运总公司”字样土黄色帆布小挎包(乡村客运班车其实和湖北省客运总公司毫无关系,但售票员也许认为拥有这样一个挎包会比较体面)、在客运站候车大厅前拉客的售票员,基本上都能精准地从一堆堆人脸里辨识出目标客户。她会走到你的跟前,帮你拎起你背包,或者拉上你的旅行箱,说:“到L镇的吧?跟我走!”
乡村班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一般都是坐满即走。但是最近十多年,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经商、到城镇居住,再加上小轿车和摩托车的普及,即便是在客运旺季,17座的中巴车也很难保证每班车都能坐满再发。在我的记忆中,近几年来,除了春节,“万山”中巴已经很少有满座的时候。
这次是我2017年第四次回G县,前几次回乡时,班车的上座率都没有超过50%。司机和售票员显然对这样的局面习以为常。事实上,乡村的凋敝让他们早已对这门生意不抱太高的期望:售票员不再勤快地跑到客运站前的广场吆喝、拉客,端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也不再一遍遍用目光机警地在汽车站来往的人群中甄别潜在乘客,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其实,不同线路的乡村班车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比如开往L镇的班车,就需要和开往C镇的班车争抢去D镇及沿途的乘客。从县城通往L镇和C镇的班车都要经过D镇,之后分道扬镳,一个往南一个向北。
我上车后不久,司机发动了引擎。带着孩子的女人话多、语速快,穿着一件花上衣,看样子和售票员相熟,从我上车起,她们之间的聊天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从谈话内容看,花上衣在县城买了房子,老公在外打工,她在家照看两个孩子上学,有时周末带孩子们回乡下看望公婆,再顺便捎带一些油、菜、鸡蛋、花生之类的农产品,为县城的小家补充给养。
花上衣说起了她昨天打麻将的遭遇:“手气不好,打了十来圈,输了四五百。能赢六张的和不了,别人单钓能赢牌,老是杠上开,买马还都有,你说气人不气人?真是手痒。以后不抹牌了,再抹把手剁了。”
花上衣说得咬牙切齿,还配合做出了一个剁手的动作,售票员脸色严肃且频频点头。但我知道,花上衣的话不能当真。哪怕发下比这更毒的誓言,几天之后依然会被忘在脑后,她们的身影照旧会在遍布县城和乡镇的茶馆出现。
在G县,所谓的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聚集了家庭妇女、无业青年、留守老人和其他闲散人员。作为一个人口净流出大县,近年来,除烟草、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外,G县大多数产业并不景气,但“茶馆业”却始终一枝独秀,可谓“街街开茶馆,户户麻将声”,几乎快要成为G县的支柱产业。
花上衣和售票员聊得正欢,她的一对儿女此刻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大约八九岁的男孩正在手机上专心致志地玩“穿越火线”。她的姐姐,一个十岁出头、穿着红裙子的女孩儿,正把头搁在弟弟的肩膀上,两颗小脑袋凑在一起,四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姐姐时而拍手,时而跺脚,时而为弟弟的低级操作发出几句抱怨。弟弟顾不上回击,随着游戏的进展,嘴里不断发出“嗬嗬呦呦”之类含混不清的感叹词。
前方迎面开来一辆小车,班车突然减速避让,男孩身体前倾,头部撞上前面座位的靠背。他捂住脑袋,“哇”地哭出声来,但眼睛仍然黏在手机上。花上衣呵斥男孩:“哭什么哭?早跟你说过别只顾着玩游戏!把手机给我!”男孩不肯给,母亲作势要打,他这才万般不舍地把手机交了出来。
只在春节涨一块钱车费
车子开出一段路,售票员暂时中断了和花上衣的聊天,开始履行卖票的职责。从县城到L镇大约13公里,车费五块,乘客若在沿途下车,车资按距离远近分别为两块、三块、四块不等。乡村班车只收费、不给票,这是G县乡村客运的传统,大家对此都不以为意。
此外,G县乡村客运的另外一个传统是:车费只收现金。我提出用微信支付车费,但售票员对我摇摇头:微信不行,支付宝也不行。事实上,我是想了解一下互联网对G县的影响到底几何。看来,乡村客运仍然是被移动支付遗忘的一个角落。
在我的印象中,L镇到G县的车票价格已经维持了五六年之久——只有春节期间(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会上涨一块钱的车费。司机老魏告诉我,客运联营体没有因为乘客减少而提高票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这样做不但徒劳无功,还可能会让客源流失得更快;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农村客运施行补贴有关:乡村客运班车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燃油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客源不足带来的损失。
一般来说,乡村客运班车在收取车费方面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有时候,你会在同一班乡村客车上看到截然相反的场景:有人抢着为同乘的亲戚或相好买票,彼此之间争得面红耳赤;也有乘客为了能少给五毛钱,一路上都在和售票员讨价还价(这样的乘客多半是在中途上下车)。
我所乘坐的这班车上就出现了其中的一幕:车上一胖一瘦两位大妈是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她们都要求为对方付车费,像是比赛似的,都在努力往前伸着胳膊,争着把手中的纸币举到售票员面前,以至于钞票都快戳到售票员的鼻孔。大妈们手中的纸币,面额分别是十元和二十元,而她们从县城回L镇的车费刚好十元。见多识广的售票员犹豫了几秒钟之后,接过了选定的那张十元,并对失利的胖大妈给予了安慰:“不着急,反正以后还要坐车的。我记住你们两个了,下次我一定只收你的钱!”但胖大妈仍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她从座位下面的塑料袋里摸出几个橘子往付钱的瘦大妈手里塞。
车到L镇的终点站,我下车后,听到身后又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回头一看,原来是胖大妈又在拼命往瘦大妈手上拎着的袋子里塞橘子,瘦大妈不从,转身疾走;胖大妈把塑料袋放在马路上,手里拿着几个橘子,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着。
(作者现为深圳富士康的工人。在《中国作家》《百花洲》《长江文艺》《文学界》等刊物发表散文、小说,曾获第二届、第三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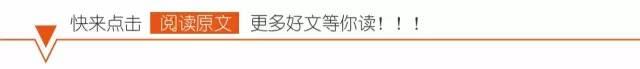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