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24)12-0004-06
【中图分类号】TU981
张庭伟,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系荣休教授。
精彩导读
近年来脑机接口(BMI)技术的发展,说明人体研究正在取得突破性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指导研究的理论日益完善。例如,长期以来人们虽然已经知道人的呼吸由脑子控制,但是对其机制不很清楚。后来的研究发现,呼吸受到自主意识和生理性需求两重生理机制的控制,人体对缺氧及呼吸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感受器分别位于脑干的延髓和颈动脉体(神经),它们控制着不同情况的呼吸功能。这个认识提升了呼吸研究的理论:如果把呼吸功能作为研究目标(因变量),那么影响目标的自变量就包括了上下呼吸道各器官、脑子中的脑干、中枢神经的脊髓及其周围神经系统等部分,因此,研究呼吸问题必须从更高层面的脑及神经系统着手,而不能停留于较低层面的气管、肺等熟悉的呼吸器官。由于人脑的活动情况不可能像骨骼和肌肉的活动那样显而易见,人类对信息的接受-反馈过程复杂而高速,故人脑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不存在定论。
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展,对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借鉴,使人们认识到从更高层面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得到的感悟是,讨论城市规划更新式转型,不能仅停留在规划自身。如果把规划更新作为目标,那么自变量就必须包括规划工作的性质、对象、工具,及规划师自身的观念问题,要全面理解中国国情这个更高层面的因素对规划的影响。
根本而言,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是执政者以公权力进行经济政治活动的工具。现代城市规划始于为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如哈维(D Harvey)所言,地方建设不但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活动[1]。城市规划同样也是政治活动。经济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一切行业产生影响,促使行业更新以适应变化,包括规划行业在内,这是铁律。可以当代美国规划演变的历史为例。
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上,经历了1990年代IT革命带动的增长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GDP年增长率超过2.5%,经济结构出现转型。主要城市的经济从制造业转向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及以IT为基础的现代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推动了并得益于全球化。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产业集中于东部沿海,高科技产业则集中在西部沿海,传统制造业衰退并逐步外迁到发展中国家,由此使美国的人口和企业都出现较大流动。相当多的人口从东部及中西部迁到西部和南部,从市区迁到郊区。很多工业城市人口减少,税收减少,对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的投资减少,失业补助等社会福利开支却增加。由于城市化率已经很高(2022年为85%),私人拥房率也已达68%,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因饱和而停滞。一些城市不但停止增长,而且衰落甚至破产(如底特律)。低端工作从白人转到黑人,最后由拉美移民接手。原住居民失业,不得不依靠救济,一些人怪罪于外国廉价产品的蔓延,却忘记了廉价产品客观上有利于保持低通胀;抱怨移民的入迁,自己却不愿接受低端工作。政治上,保守的共和党更加右倾,民主党则渐渐受激进派控制,两党矛盾增加。制造业衰退使曾是中产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失业增多,工会会员减少,工会影响力式微,动摇了二战以后工业资本和工会在政府协调下共治的体制。过去代表工会的民主党的成分发生变化,自奥巴马主政以来,民主党渐渐成为受过教育者的政党(支持者也包括绝大部分规划师)。25岁以上美国人中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占38%,他们较多分布在东、西部沿海地区,从事较高收入的高科技、金融工作,支持民主党自由派。他们与生活在美国中部、渐渐降为社会下层而怀旧的白人工人农民存在矛盾,带有民粹倾向的白人劳动阶层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一部分民众支持“小政府、少干预、低税收”等共和党口号,狭隘地以维持美国白人的传统优势为诉求,愤恨所有新兴力量的挑战;另一部分人则倾向民主党“公平、民主、扶弱”的“政治正确”,支持处于少数地位的有色人种、不同性取向群体和移民,却忽视了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民众。在两党基本盘已经固定、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民主党力争少数群体的支持,也是为了获得这少数能够左右选举者的选票。所谓的“政治正确”往往沦为虚伪的双标,并非真正民主,而是把不同意见都当作“政治不正确”加以排斥。这样的分化加剧了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贫富等结构性矛盾,两党的极化则挤压了历来领导国家、持中间立场的建制派势力,这样的局面延续至今。
如同一切行业一样,城市规划行业的生存取决于社会需求。美国社会的变化引发了需求的变化:虽然GDP仍有增长,但城市化停滞,建设减少,社会分化……传统承担着物质性建设工作的城市规划何以应对?1980年代后,美国规划界出现了密集的争论,表现之一是规划理论的大论战,焦点是“规划可以做什么?”即“Everything”“Nothing”与“Something”的争论。一些规划师认为城市规划可以继续从事物质性规划,也可以主动参与社会规划,规划仍然可以“Do everything”。也有规划师认为物质性建设减少而社会问题遍地,它们不是规划师的专长也无法解决,所谓大有作为,其实是“无所可为”——“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planning is nothing”。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规划仍然可有所为“Do something”,但不能事事介入,规划师是协调者而不是决策者。
起着行业指导作用的规划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以建筑美学为基础的古典规划理论(如华盛顿规划及芝加哥规划,由执政者决策);以理性为前提的功能主义现代规划理论(如《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和卫星城理论,由执政者及精英决策);听取“社会人”需求的当代规划理论(如协作性规划,也包括生态城市、健康城市等主题性规划,提出规划师是利益相关方的协调者,要引导公众参与,共同决策)。较激进的规划理论家指责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负面作用而加以排除,呼吁公平城市等理想目标。他们集中在高等院校,口号动人,学术影响很大,可惜与现实脱节,对规划实践影响有限。
在社会变化中,政府要应对大众意愿又有自己的政治议题,对作为执政工具的城市规划有什么要求?规划又如何应对执政者和公众的要求?在美国,市政府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维持选民支持,争取选举连任。执政者往往在三方面采取措施:一,应答社会舆论,满足选民(特别是基本盘)的主要社会呼吁以巩固选票;二,经济是关键问题,政府提出增加收入、减少开支、控制通货膨胀等措施以安抚选民;三,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就业,要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的选票。规划是一个中性的执政工具,不同政党在使用规划工具的做法上有侧重。在民主党大本营的芝加哥,1980年代以来的规划界也出现了变化。
第一,固本守正。强调城市规划的法定地位,巩固城市规划所具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公权力,即城市用地管理权,依照地方立法批准的区划法规(Zoning)来决定城市土地的用途、开发强度(容积率)和建筑特点,颁发建设许可证,是由国家规划法(Planning Enabling Act)授权、经地方立法确定的城市规划部门的核心业务。由于美国没有法定的国土规划及区域规划,城市土地管理是宪法确认的地方政府的权限。例如,即使是具有全国影响的“精明增长”政策,也非国家政策,而是美国规划学会(APA)提出的建议,推荐给各级议会立法后采用。所以美国的规划行业相比欧洲处于弱势,也因如此,美国规划工作就更加立足于已建立的法定城市规划,这是百年来美国规划行业的基石。
第二,关注民意以取得公众支持。规划部门加强对社区的服务,规划师下沉基层,深入街区,了解公众需求,共同制定居民满意的社区更新方案,采用公私协作(PPP)实施规划,以公众的支持来增加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及社会对规划正当性的认同。
第三,减少规划开支。美国的规划管理部门历来和规划设计机构分离:规划局属于政府机构,但一般不包括设计部门。所有规划设计任务均在设计市场招标,以减缩规划局的编制及制订规划的费用。
第四,调整规划局工作业务。规划局一方面巩固土地管理职能,另一方面新设为了增加城市收入而出现的职能。1989年笔者在芝加哥规划局实习时,那里有四个主要职能部门:土地区划管理、社区发展及住房(覆盖除中心区及关键地带外的社区)、中心区发展及规划、历史保护。目前它有五个职能部门:保留土地区划管理;扩大社区发展部门,把政府对社区更新的投资、特别对是对小微企业的资助纳入规划局的工作范畴,包括规划局和经济发展部门合作,通过规划划定TIF地区、经济赋权地区(Empowerment Zone)(均为政府认定的重点更新地区),以公共投资注入这些有潜力的贫困社区,协助创业,增加就业,改善人口流失、税收减少的情况。同时规划局和住房局协作,增加低房租出租房的供应。原有的中心区发展及规划部门,扩大为谋划全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用地开发政策主管部门。保留历史保护职能。最后,新增加了土地出让及再开发处,负责出售市政府所拥有的公共土地并指导再开发,以增加城市财政收入。
第五,适应人才向大城市迁移的态势,做好城市更新以满足需求;积极支持私人资本投资于更新项目,协调政府目标及私人开发项目。除了联邦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美国建设投资的主体一直是市场。近年来由于人才流向大城市,中心区的房价上涨,住宅是私人资本的主要投资项目。同时,老旧的办公、住宅、商业建筑衰败空置,需要拆除重建,管理更新项目是规划局的主要工作。在芝加哥,由于波音公司总部等迁入落户,高端人才随之进入,规划局和各利益相关者致力于不断完善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吸引力,芝加哥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美最有吸引力的大城市。
第六,改组各类规划机构的领导班子,大幅增加女性、非白人规划师进入领导层,以回应美国社会对多样性、特别是增加女性领导者的呼吁。过去十年来,从全国性规划组织到地方规划局,女性领导者已经基本上替代了原来占多数的白人男性规划师。2024年,美国规划学会(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APA)由一位黑人女性主席领导,秘书长及司库两位都是白人女性,候任主席也是白人女性,主要领导中没有男性。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lanners,AICP)有一位白人女性主席,秘书长兼司库是白人女性,候任主席也是白人女性,同样没有男性。这都和二十年前完全相反。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 of Planning,ACSP)三位前任主席也均是女教授,目前的男性主席来自于南美洲圭亚那、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三位副主席则均为白人女教授。在地方层面也一样,2024年芝加哥规划局长是黑人女性、7位副局长由四女三男组成。当前美国规划专业的女学生占55%左右,更多女规划师担负起领导责任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第七,规划教育力求和规划就业挂钩,有序配合。政府规划机构的规划师职位,优先录用规划专业学位者,即“职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的规划硕士(MUP,约占全国规划机构人员的45%),也录用其他专业的硕士(约占20%)。规划本科生的就业包括社区组织、NGO、各级议会成员的助理,以及政府规划机构的助理(约占规划机构30%)。规划博士主要成为大学教师,也有加入研究机构、智库等[2]。规划院校注意根据社会需求调节招生,例如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任教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规划硕士生从1980年代的200名减到161名(153名两年制城市规划硕士MUPP,8名一年制城市设计硕士MCD,2024年数据,下同),博士生从40名减到19名(PhD,包括留学生),2010年新设的四年制本科生有97人(城市事务学士BA),所以规划学生总数未减反增。客观上一些城市的人口减少,相应规划局的人员也有减少。如芝加哥市人口从1980年的300万人下降为2020年的275万,规划局人员也减少到目前的170人。规划本科生增加而研究生减少,反映了规划就业市场的变化,说明社区及非传统的规划就业机会增加,而本科生的就业具有更大灵活性。
第八,规划行业各专业组织、学术刊物分工协作,互相支持,共同应对社会变化。美国规划界的行业组织是美国规划学会(APA),包含了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ICP),两者的学术刊物是《美国规划学会会刊》(JAPA),重点是规划在社会变化中的应对及工作交流。规划教育工作者集中在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学术刊物是《规划教育研究》(JPER),关注规划理论及规划教育问题。还有相当一批专门性更强的规划组织及各自的学术刊物,如交通规划、规划理论和历史、城市设计等,它们以各自的刊物及具体成果应答社会需求。此外,有很多与规划相关的其他行业组织,如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AAG)、城市事务联盟(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UAA)等,这些组织及其刊物与城市规划有分工也有跨界协作,各种组织都有自己的社会联系,争取了社会各界对城市规划的支持。
虽然仍然面临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美国规划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了近年来政府、公众和资本三方面需求的变化,使规划工作得以稳定运作,可作借鉴。必须强调,美国的国情和中国有很大差异,一些做法仅适于美国。行业更新式转型往往是外部压力的结果,很多变化并非规划界的主动所为而是被动应对,未来规划理论的更新和学科的转变,仍然有待与时共进。
上述分析说明,作为应用科学和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在外部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中作出改变,是国际上的普遍现象,外部压力也可以成为规划行业更新的动力。面对挑战,城市规划必须进行更新式转型,既有固本,又有更新,但不会消亡。
作为公共政策,规划是公权力进行经济政治活动的工具,而公权力则由公众授予执政者。不同国情下公权力的授权、运用途径不同,国情对一切公共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构成“笼鸟关系”:国情是笼,公共政策是笼中之鸟。城市规划同样受到国情的制约[3]。对执政者而言,规划是执政工具,通过规划对土地空间进行谋划、管理,应答公众的意愿并体现其政治经济理念。经济政治因素与规划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行政性需要。土地空间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及社会运行载体,各级执政者都需要有一种工具来管理它们,规划就是这个工具。不同层面的规划具有不同类型,如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等,不同国情条件下这些规划的地位不同。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治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上国土广阔,人口众多,城市土地公有。中央政府考虑的大政包括国土使用对国家粮食生产、生态可持续发展等战略问题,空间规划体系中层级最高的国土空间规划乃是中央政府的首要抓手,基本国策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来宣示。然而,国家的宏观决策需要落地,尤其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实施国家土地空间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具有法律作用的地方性详规/控规,它们管理体系成熟,从业人员众多,有明确的法定地位,且直接牵动民生民意,所以包括详规/控规的城市规划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国家治理工具的“刚性功能”,是国家治理必要的结构性支撑。二是政治性需要,中央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的需要,对国土空间管理的重点及政策作出调整,处于规划体系下位的城市规划也因此变动,具有“塑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如何运用城市规划工具,但不改变城市规划作为刚性工具的基本性质。因此,应该全面理解城市规划不变和可变两方面的性质,要固守不变的行政性功能,服务好各级执政者及民众的需求,也要认识到政策与时俱进的动态性。
和所有公共政策一样,与时俱进是城市规划的基本性质之一。规划的角色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规划是“白纸上画图”的开路先锋,无论在1950年代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还是1980—1990年代深圳、浦东等地的大开发时期,城市规划都做出了贡献,也因较高的曝光率而受到执政者和公众的好评。但是在高速发展之后,城市规划更加长期的作用是土地空间的日常管理并参与城市社会的治理,这是城市规划自身可持续运行的核心,可是少为人知也少有向执政者宣传的机会。因国情差异,各国规划界都在探索如何在城市治理中起作用,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途径,因为治理的主要对象不仅是相对稳定的物质环境,而且是在物质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城市规划是否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取决于各级执政者的认可和公众的认同。
3.2 城市规划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
城市规划的基本工作对象是城市土地空间,基本服务对象则是执政者及公众。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有密切关联,但不完全相同:规划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物,服务对象是人。在规划工作的人、土地、经济三要素中,人是首位的——是人在土地空间中的活动使土地空间成为规划的工作对象,而人的需求变化是规划工作变化的根本原因[4]。所以服务对象的重要性大于工作对象。
规划的基本工作对象是土地空间,土地空间作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生产资源及社会载体,是一个“巨集”,可以按不同目的分成不同的“子集”。例如从人居活动角度,可以分成“宜居”和“非宜居”。在“宜居”土地空间中又可粗分为城市和乡村;在城市地区中再细分为居住、生产、交通等;在生产活动中则分成工业、农业等。在“非宜居”土地空间中,也可以分为自然性非宜居(高山、沙漠、水域)、政策性非宜居(边境、军事、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区)等。国家层面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对象是整个国家的土地空间“巨集”,包括陆域水域、宜居非宜居,面极广而难以细化;地方层面城市规划的工作对象是子集里的子集——城区及郊区中居住、生产、交通、休闲活动的土地空间,面较窄却必须深入。在城市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规划的工作对象相对稳定,主要是土地空间这个“物”。后高速时期,规划必须通过协调方式,工作对象中有大量鲜活的“人”,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甚至合二为一。
规划的基本服务对象是执政者及公众,都是具有可变性的“人”。城市规划发展至今,涉及的内容已经外延到制度建设、社会进步,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在中国,中央领导一再强调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规划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国策。生活现实中,各级执政者则是规划部门的直接领导。在高速发展时期,地方执政者把城市规划当作重要工具,重视规划在增量空间开发中的经济贡献,他们是规划师的主要服务对象。由于增量空间里往往居民较少,故原有居民并非规划关注的重点。在后高速时期,存量空间中原有居民很多,公众成为规划师的主要服务对象,规划师为了处理社会问题,必须增加社会性、政策性,包括公共财政方面的知识。
可见新时期城市规划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虽然基本相似,也都有改变,意味着规划师要固本,也需要更新知识、工具和理念。
3.3 城市规划的工具
规划工作的范畴包含多方面,规划工具也包含多方面,各有不同属性。作为执政工具和公共政策,规划首先以法律规范为工具。制订法律规范的基础工作是理解城市、理解社会,这就需要分析工具。最后,为了把政策落实为物质性实体,规划也需要设计工具。讨论规划工具,有几个观点:
第一,必须把规划本质的政策性与规划工具的技术性区分开。规划工具不是规划目的,而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以公共政策为本质的城市规划,其最终目的是为人民建设城市、治理城市。现代技术,无论是大数据、AI、智慧城市等都是技术工具,是为规划本质服务的,对技术工具的追求无法替代对规划目的的追求。
第二,现代高科技为人类造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风险,已是一个共识。技术向善,善用技术是前提。人是第一位的,要防止见物不见人。例如应用大数据是为了提升城市分析的质量,提高法规规范服务公众的精准性,而不仅是分析顾客上网、购物的喜好。
第三,一切技术的背后是人,人的理念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和采用的手段。规划的目标是长期的,成就是累积的,要防止短期的功利主义导致行动方向的迷失。
第四,当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工具,尤其在分析工具、设计工具方面,新技术在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例如可以完善情景规划,利用AI和HI(human intelligence)结合,组织公众参与,开放性地编制不同情景条件下的规划方案,使城市规划从传统的土地空间、交通情景分析进入更加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公共财政、生态情景分析,这将为城市规划开创全新的平台。
一切事业的更新,本质是人的理念的更新。规划的更新式转型也意味着规划师自身理念的提升。提升规划师理念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这里仅就理性这个重要问题做一些讨论。
首先,现代规划理论建立的“理性规划模型”(the rational model),仍然是当代规划理论的重要部分,不同的是现代规划理论相信规划师作为专业精英的个体理性,而当代规划理论则转向公众共识所建立的集体理性,但是两者都依从于理性模型。理性模型的核心是人类决策必须具有理性基础,从建立目标,到分析现状、提出解决措施,到落实措施、反馈得失而加以改进,都应在理性的前提下,因为规划就是谋划,必须理性办事而不能率性任意,可以说没有理性基础就不能称为规划。反观规划实践,成功的案例肯定基于理性分析及理性决策,能够顺应公众需求,符合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而失败的案例无不因为盲目决策,违反客观规律,中外都一样。城市规划的更新式转型尤其要强调理性分析及科学决策,善用高科技,减少武断行事。
其次,从现代规划理论的个体理性转变为当代规划理论的集体理性,说明了两者的重要差别:个体精英无法替代公众共识;理性不能覆盖多样性;“刚性”单一的理性应该尊重“柔性”多面的人性,因为人性包含着不少理性以外的部分:人性=理性+N。要警惕规划理论所提倡的理性也存在着缺陷,僵化了教条却忽视了远为复杂的人性。规划界都赞同雅各布斯(J Jacobs)在指出美国大城市的弊端时对当时规划的批评,老太太所赞美的城市街道的活力,归根结底根植于尊重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在雅各布斯研究城市的同一时期,费耶阿本德(B Feyerabend)也在哲学层面研究理性的局限。他表达了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反感,认为那往往是片面的,有害于人类发展。他指出:西方文明已经丧失了太多的多样性,本来自然界的多样性因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得以加强,但后来无论是自然的多样性或文化的多样性都被以理性之名而同化、变得单调,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告别理性》[5]。在当前的城市更新中,也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问题。上海淮海路上过去林立的各种商店、饭店,被城市更新后的几个大型商场、购物中心所替代,同时消失的还有原来人头济济的人群。美国的购物中心都建造在郊区,适合他们的汽车生活方式,淮海路历来以步行和公交为主,大商场背离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貌似高大摩登的“白象”沦为空荡的摆设,也有背于当时决策者的构想。街道活力消失,根本原因是由于不尊重百姓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更忘记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央精神。
参考文献
[3] 张庭伟,于洋. 国情·公共政策·规划理论——城市规划理论及“笼鸟关系”[J]. 城市规划,2022,46(10):7-17,38.
[4] 张庭伟. 城市规划学科的学理问题[J]. 城市规划,2023,47(11):51-56,66.
[5] 费耶阿本德. 告别理性[M]. 陈健,柯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在后台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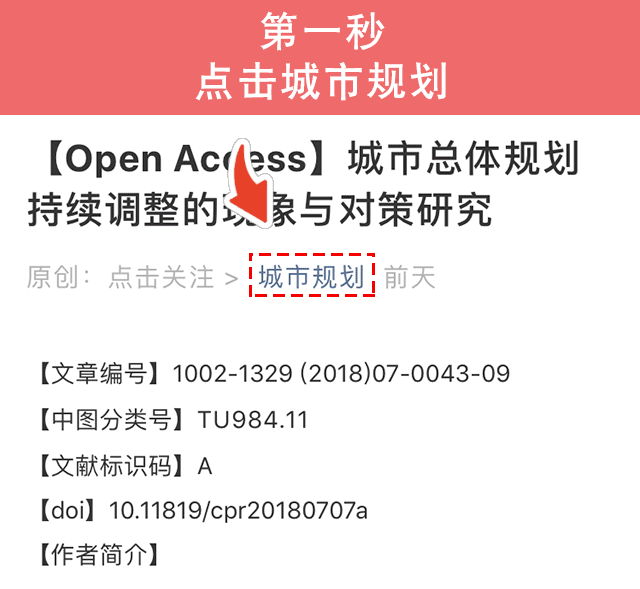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Open Access】解析城市规划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