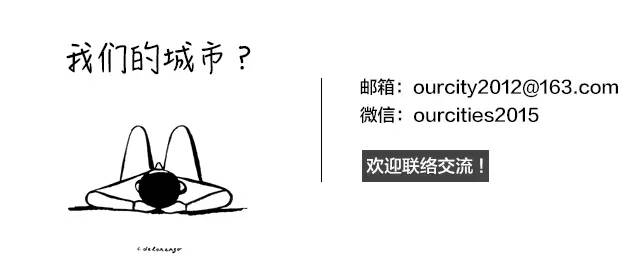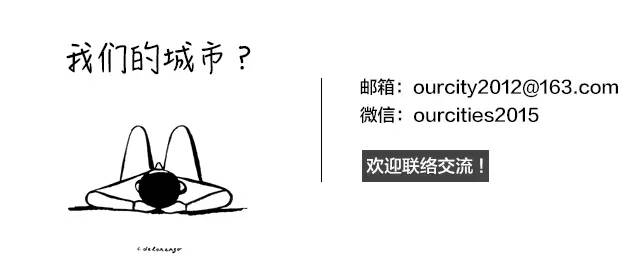2015-07-05
分类:乡土文化
阅读(132) 评论(0)
编者按:是上海人排外?还是外地人排上海?如果城市能让所有居住于此的人感到公平、认为城市属于生活此地的人,上述两个问题都不会发生。现在的上海经济繁荣、又国际化,但到底这些是因着资本打造,是拿着纽约、伦敦的模板在复制,它不是为了生活在这城市里的人民考虑。你看那静安寺附近幽静却离繁华商业地段不远的小区,所住者何人?一个个打造起的商场真正消费客群又是谁?上海,如果要打破这些问题,唯有走出自己的路!
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中,我们感受着更多的城市气息,每一分一秒无不被城市化的进程包围着。从城市发展的视角来看,准确把握上海市发展环境的时空特征,选择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制定有效的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对上海市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这其中很重要的“人”的因素,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上海像一块巨大的吸金石一样吸收着全国各地优秀的知识分子及农村务工人员,每一个人都怀揣着梦想来到上海准备一展才华,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无形对上海本地人造成了空间上的排挤,上海成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可我们也更多地看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当看到“上海——我的better city”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上海铺天盖地的“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宣传语,我这个外地人对所谓的“城市化”颇有感触。
就城市化的概念来看,人口学家认为,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地理学家给出的定义则是,地理学所研究的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就从这些概念定义上来讲,与其在上海谈“城市化”,还不如谈“上海化”。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最发达的城市,现阶段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树立自己的独立的城市性格和城市文化,去成为一个坐标和榜样。中国人不喜欢摸着石头过河,总是喜欢找个榜样,找个模子,学习一下,搬过来用一下。但就现在的上海,试问我们是要借鉴东京还是新加坡抑或是纽约?上海城市化发展到这个阶段不可能再去借鉴他山之石,因为他山石此时已经攻玉难下了。
上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一句“阿拉上海人”,告诉全国人民,就是上海。国家本就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各民族、种族,地域的人融合的一个共同体,我们合理生存未必要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实行文化、风俗、习惯、语言上的同质性为前提。但就在全国文明的大都市上海,上海人讲上海话被认作为是“排外”、“不友好”、“不团结”的行为,是缺乏文化素质的表现。在上海,本地人发现自己的家园越来越陌生,大街上充斥着“满大人”的官话和他方异乡的鸟语土话,同时空气中依然回荡着“本地人排外”的责骂声。同样,上海人本身也存在一种危机感,如今在上海这个地方的不都是上海人,准确的讲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2009年12月23日一句“圆润的抱团离开”,上海就像下了圆滚滚汤圆的锅整个都咕噜开了,为什么?因为,在上海这个城市奋斗的几乎所有外地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生活,但还不是“上海人”,于是上海人向来的排外的传说就成为了一个合理的借口。究竟是上海人排斥外地人,还是外地人排斥上海?真正的老上海人实际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
之前看过一篇关于所谓上海的七大类中青年阶层的生存现状,虽然说不上多么的客观准确,但是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大上海的现状,他们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基本处于中下层,而金领阶级以上年收入15万以上基本都是外地人,而住在棚户区的除了民工最多的就是老上海人,随着离大世界百乐门距离的遥远,注定了那些原来所谓排外心理也被逐渐的边缘化。所以现在仍然去拿所谓“上海人排外”来说事,尤其是身在上海的人,是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对上海的不信任。可能这种不信任,是由于上海还未曾带来一种归属感,外地人即便是有了上海户籍仍然难以自信的去说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上海本不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城市,你可以看到世界多元文化在这里的融合交错,五光十色流光溢彩,你可能会很快地迷恋上上海,但却很难爱上上海,因为它总是很陌生,或者说是冷漠。但上海却是缺乏被爱的城市,因为“我们不是上海人,我们只是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相比鹏城深圳的“人人都爱深圳”,上海无疑是悲哀的,外地的人们来上海工作了,生活了赚钱了,却又都在排斥上海。“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余秋雨在《上海人》中如是说。这里的上海人我们且可以认为既有迷恋过去黄金时代的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们,还有的就是这些拿了上海户籍的外地人们。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被城市化,人性也被城市化。但上海,在“城市化”中,是否能更加“海纳百川”去寻找自己的风格?面对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我们如何解决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尴尬的境遇呢?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化的措施就可以完成的,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尚且互不和谐谈何人与自然的和谐?说到底我们要融合人首先要融合人们的心,让外地人找到这种归属感,也要让上海人重塑主人翁地位。难道上海就甘于接受外省市铺天盖地对上海的讽刺、嘲笑和丑化吗?当然不是,因此,不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应该要从内心里去接纳对方,爱上海爱他人,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感情出发影响行动。
“上海我的家,我是上海人。”居住在上海的外地人需要拥有这种自信,而上海,真的需要新时代的品格,一个家训。不管“阿拉上海人”还是“我们是上海人”也许将来的“we are shanghairen”,上海成为来这里人的精神之家的时候,这样的上海才能称得上“上善若水,海纳百川”。
▌本文选自当代文化研究网:《“城”长的烦恼》,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