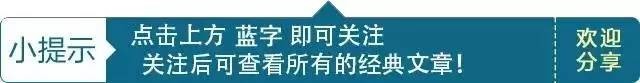
探寻散逸民间的乡音故事;
触摸谆谆流传的乡土人情;
述绘咱厝咱人的心乡映像;
荡开游子家人的乡愁涟漪;
记忆你、我还有他们曾经的故事
时代是人才的摇篮,环境是人才的课堂,这是人生的哲理。闽南地处滨海,和台湾只隔一个海峡,人们视海为陆,不畏风涛。十七世纪的我国,内而明清的改朝换代,外而西方早期殖民者的凌扰,海疆多事。闽南人处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名人,文武忠奸,朝野愚贤,统而有之。郑成功、黄道周、李光地、洪承畴、施琅这一大批闽南人,都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我不想品藻人物,但人一旦成为名流,自然在史籍记载上和人们的传说中,都留下大量痕迹。清初名将官封靖海将军靖海侯的泉州人施琅,人称施将军的旧事,无例外地也流传于闽南人及台湾人的言谈之中。
施将军遗迹遗事不少,倘若重弹老调,便使人厌腻,我只想说些这位大将的性格、住宅、坟墓等的片段新谈。
忆清初安溪翰林陈迁鹤为施琅题像赞,有“归黔黎于故土,开郡邑于遐荒。……两岛八闽皆诵德,千秋万祀永流芳”之句,于是我先说说他的遗像。施的画像较多,不再介绍。至于塑像,我见过两尊,一尊泥雕的,高约尺余,全身端坐,原来供奉在泉州风池巷他的故居正厅。形状威武,手足以木为之,所以能动,他的子孙数百年来每逢冬夏,都要为之换装。那套小小的朝衣补服,绣得很精致。这一尊可惜在“文革”中被砸坏。还有一尊巨型石像,高近丈,武装正坐,以整块白花岗刻刻成。此像原来置于泉州东岳山上,后来祠宇破坍,石像就露坐在风霜之下,几经岁月而不为人所知,因此逃过红卫兵“破四旧”之劫,保存下来了。前几年衙口施姓族裔探知此事,悄悄地开了一辆大卡车(传说是拖拉机,编者注)把石像运回衙口,奉祀在其大宗祠的后厅。饱经炎日严霜的施将军,终于安然返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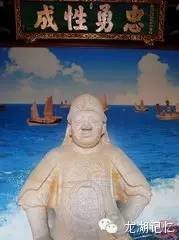
施将军的府第有二,一在泉州城内凤池现晋江农校校园内,被称为“清朝元勋第”,二进七开间,建筑规模魁雄,砖木结构厅口屏风木雕艺术甚精,梁柱粗壮,现尚保存完好。市文管会已立碑加以保护。另一在晋江衙口村,现已废圮了(2003年,在晋江市政府发动下,海内外乡贤捐资,按照”修旧如故”的文物维修原则修葺,并辟为施琅纪念馆,编者注)。
施将军的坟墓,民间传说他怕后人毁墓,设疑冢数座,同一天有四具棺木出泉州四个城门,使人莫辨其真。这个故事当然有趣,却不一定事实。他的墓确葬在惠安县黄塘虎窟乡,至今犹存,列为惠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少川按:施琅墓于1991年被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墓范围宽广,几近百亩面积。墓丘及墓沿为三合土结构,墓庭两边的石刻翁仲、石虎、石羊、石马和石华表都还完整。只是墓前石碑坊已毁,三座原立有康熙皇帝三道御制文的石碑亭,仅存其一了。墓道之南有清溪一道,迂回蓄水,增添墓园秀景(林少川按:施琅墓已于1995年修葺一新)。
施将军的纪念牌坊本有多处。在泉州南大街立有“上将能宣力,南纪尽安流”的大型石坊。此坊在民国时代因扩展马路拆掉,碑石散失。近经泉州市文管会寻访,收集到残余石刻数方,藏于该会。在同安县城东二里多的大路边,也立有“绩光铜柱”石坊,现尚完好无损,巍然耸立,为同安县文物保护单位。
泉州俗语说:“猪母近戏鼓脚,不会吹箫也会拍拍”。最近我国音乐界很重视泉州的南音,在泉州成立了中国南音学会,我曾应邀出席成立典礼。虽然我近泉州的戏鼓脚已数十年,吹箫和拍拍却统统不懂,为祝贺该会的成立,我只能做点秀才人情,挖点南音史实,聊当献礼。就在史料的校勘中,我忽然发现被认为是一介武夫的施将军竟然是一位南音研究专家,并对南音的发展和传播出了一些力量。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六载施琅“既平海岛,从容坐镇,日与文士诗人宴游酬酢,颇有东山汾阳风度。”乍看似乎施琅在台湾是与文人饮酒赋诗,和南音没有关系。后来查《靖海记事》中施德馨撰《襄壮公传》,有一段类似的记述:“(施琅)性好音乐至晚年尤甚。 尝集诸词客制新声谱之乐府,饶有东山、逸趣。’’原来施琅本是南音爱好者,老年时更加喜爱,在台湾常邀集文士制作南音新词。所谓“东山逸趣”是借晋朝宰相谢安隐居东山日日丝竹管弦的典故,来形容施将军在台湾大唱南音弦管的情况。施将军把泉州的南音推广到台湾,对南音的倡导和曲词的雅化,都有所贡献,这些事过去人们都不很清楚吧!
观施将军之像,容貌魁梧;读施将军之传,虎胆雄略;特别在台湾役成功之后,他对郑成功的子孙,不报复私怨,说明他气量恢宏,就是这个名将,却也有其不足之处。当年清廷对台湾,有两个军事布骤:第一步收复金厦,这一功被泉州人万正色所得。万(正色)官封提督,其故居尚存,泉州市文管会也已立碑保护了;第二步进兵澎台,这一大功又被泉州人施琅所得。照理说这两个同乡大将,应该和睦才是,不料竟是互相矛盾,真是出人意外。现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廿二日汉文《起居注》所载,关于施、万的矛盾,康熙皇帝早已知道。这一天上朝,康熙查问刚从福建视察回京的内阁学士石柱,君臣在金銮殿谈话记录照抄于下,以供读者一阅:
“上顾石柱问曰:朕前日未曾问得提督万正色、施琅若等品行啊?石柱奏曰:相传旱路提督万正色为人忠厚和平,居官亦优,别无称赞之语。上曰:万正色前督水师时,奏台湾断不可进取.朕见其不能济事,故将施琅替换,令其勉力进剿,台湾遂一战而范。万正色、施琅二人可相和睦否?石柱奏曰:二人见面佯为和好,阴相谮嫉,甚不和睦。上曰:施琅何如?石柱奏曰:水师提督施琅人材颇优,善于用兵。但既成功,行事微觉好胜。上曰: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持功骄纵,此理势之必然也”。
施将军和万提督都由郑成功部队转化而来,都为大清朝立大功,但彼此“佯为和好,阴相谮嫉”也算是我这次披露出来的新资料。“粗鲁武夫,未尝学问”,这是康熙皇帝的评语,我认为还中肯,有学识就该团结,诸君意下如何?
人才难得,机缘难遇。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新中国,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建设而效劳,应是一项神圣的任务,我读施将军旧事,难免有新的感怀。
(载于《闽南乡土》1985年第3期)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