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自1924年出台第一部《土地整合法》至今,已累计实施土地整治项目560余项,涉及近250万公顷土地(占荷兰约50%的国土面积),基本实现了乡村地区全域覆盖。经百年规划实践,荷兰在农地重划、乡村地区土地综合利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一套完善的政策工具与规划管理制度。荷兰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政府主导的国土开发模式,与我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01
理念导向:从“农业促进”转向“多元价值”
二战后,随着荷兰乡村地区发展,非农活动用地需求日益增长,迫使当局开展新一轮乡村土地政策探索:1947年出台《瓦赫伦岛土地重划法》,首次将户外休闲、风景管控、生态保护等多元目标,融入农业优先的乡村土地整治;1954年颁布第三版《土地整理法》,明确项目需预留不超过5%的土地,用于兼顾生态景观、基础设施、村庄改造等公共非农目的;1985年,《土地开发法》正式取代《土地整理法》,进一步弱化了“农业优先”的理念,转而强调要实现公共利益、消除大型基建项目负面影响等多元目标,并制定综合开发、土地调整、协议置换等多种政策抓手,农地重划仅为其一。自此,荷兰乡村地区土地整治从单一的农地重划,逐步转向多元导向的土地开发计划。期间,除了国家层面的土地整治法案不断迭代,针对荷兰西北部地区的《再开发法案》、应对特定灾害的《重点地区重建法案》等地方法案陆续出台,进一步丰富了荷兰乡村地区土地整治政策体系,强化多元价值导向,并有效指导土地的保护与开发。

荷兰乡村地区各时期土地整合法和
土地开发法演变梳理
图源:项目组整理
为确保乡村土地开发项目充分体现多元价值导向,1985法案确立了“自下而上申请、自上而下审批”流程:农户个体、农协组织及基层政府,均可向农业渔业部发起立项申请;由中央部委组织省市政府与相关利益机构代表,设中央土地开发委员会(CLC)共同决策项目是否具实施价值,再下发至省政府核查区域规划符合性、列入项目执行清单;任命由农户、相关机构和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乡村土地开发委员会作为项目全过程执行主体,在省政府、以及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服务署(DLG)、国家地籍署(Cadastre)、农业土地管理署(BBL)3个专业政府服务机构的技术支持下,开展项目规划编制与实施工作,从而高效统筹协调多方利益诉求。

荷兰乡村地区土地开发项目流程(1985法后)
图源:项目组整理
02
管理机制:从“城乡分治”并入“全域共治”
尽管荷兰不存在户籍或土地权属上的城乡壁垒,但鉴于乡村规划起源于由农业部门牵头的土地整理法案,而城镇规划侧重于住房和建成区的管控,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目标及管理制度上分歧,与我国规划语境有相似之处。
1965年,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出台《空间规划法》,首次明确省级乡村土地整治项目必须符合区域空间规划蓝图、市级法定土地利用规划必须覆盖乡村地区。1985年,《土地开发法》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乡村地区需纳入全域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并允许土地整治项目突破乡村空间限制,在大城市周边等城市化地区实施。
各项目的执行主体(乡村土地开发委员会)作为媒介,在编制阶段,需整合城乡规划、风景园林、水利交通、经济测算等多专业的意见形成具体方案,并为国省市政府与相关主管机构提供跨层级的协商平台;在实施阶段,组织地籍登记、施工建设、资金安排等多环节工作,以及职能部门征地收购、土地划拨等多部门协作。最终在城乡“一张图”上,实现多专业、多部门、跨层级、全流程的全域共治规划管理。
03
分配原则:从“单方激励”迈向“多方共赢”
项目费用早期由业主承担,市场动力不足。为加快推进土地整治工作、激发参与者积极性,政府推行系列针对性政策:一方面,出台了多种财政激励或福利津贴措施,如1938法案加大了政府对总费用的补贴力度,1954法案承认合约租户与业主同权、弃农散户获“一次性补贴/固定月薪/转业培训”,1985法案允许“协议土地交换”模式免征财产转让税、全额补贴所有权交换成本等;另一方面,明确了私人土地“同类同质同农业价值”的土地再分配原则、以及“谁获利、谁承担”的费用分摊原则(即农户按获益多少承担相应比例的费用)。
同时,为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多方共赢,荷兰土地整治自1954年引入“扣减”制度,要求各主体贡献出3%(后改为5%)的权属土地,用于道路、水利等基建改善项目(默认主体均从中直接获益,政府不予补偿),或用于生态保护、户外休闲类公共项目(若主体无获利,政府给予补偿)。此外,允许地籍署为公共利益以市场价自愿收购或强制购买所需土地,再直接划拨或交换给相关承建部门、或暂存土地银行。
2007年新法颁发后,荷兰土地整治的事权(尤其是融资责任)下放至省级政府,更关注各方收益与成本平衡。近年,荷兰积极探索 项目“瘦身”(限制单个项目面积不超2000公顷)、公众宣传(农户年地均生产成本可节省200-300欧元)、路径创新(小范围“自下而上”实施模式)等,鼓励社会参与,致力实现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土地整治项目高效实施。
04
对广州的启示
(1)因地制宜,构建目标多元、路径多样的整治政策体系
立足不同项目需求,围绕生态保护利用、现代农业促进、产城乡融合、农文旅融合等多元目标导向,细化完善农用地整治、低效建设用地再利用、综合治理等多类整治模式的选用指引与实施路径,可进一步补充特定地区、特定整治模式的地方细则,丰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使用场景。
(2)综合规划,强化城乡全域全要素管理
充分发挥土地整治综合性规划作用,建立整治项目与区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双向协同机制,对上落实总体目标、对下优化局部空间。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现城乡全域全要素管控,除水田垦造、增减挂外,扩大探索森林、河湖、海岛等其他自然资源要素流动途径。
(3)政府搭台,探索多方参与的可持续运营模式
政府主导组建“部门协同、多方参与、上下联动”的具体项目实施管理主体,明确各方“投融建运营”全流程的事权责任。一方面以金融工具、财政资金支持基础环境和设施建设项目先行,撬动社会资本后续投入,另一方面“点、线、面”结合用活土地要素,支撑“美丽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链的前期培育孵化与后期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升综合经济效益持续赋能乡村发展。
参考资料:
[1]【Fachbeitrag】Henk Leenen: L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therlands
[2]【荷兰土地及水资源管理服务署DLG】Adri van den Brink: Mordern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3]【荷兰地籍署Kadaster】Marije Louwsma: Land consolidation in a modern setting
[4]【粮农组织国际专题讨论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土地碎片化和土地整理 | Jack Damen:Development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from project objective to project instrument
[5]【中国土地】扬·范·瑞能:荷兰的土地整理与农业发展
[6]【国际城市规划】张驰 张京祥 陈眉舞:荷兰乡村地区规划演变历程与启示
供稿|规划设计一所
技术审核|总工程师办公室
文图编辑|办公室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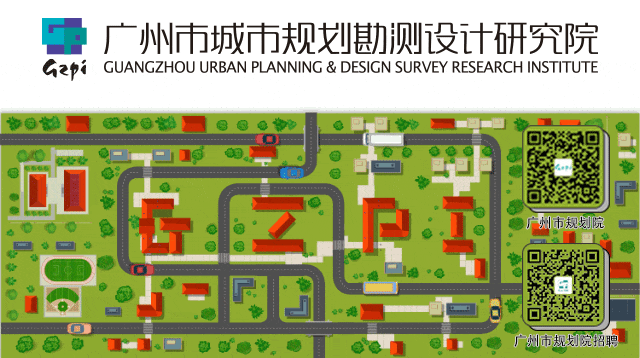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广州市规划院):海外观察|荷兰乡村地区百年土地整治政策探索回顾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