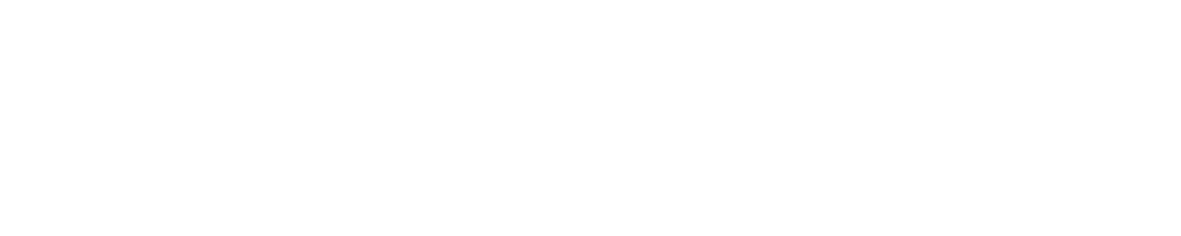

种树、骑自行车、把厨房垃圾做成堆肥等,都是在救地球。
上中学时,我在渥太华的一家杂货店当打包工,那是一个正在中产阶级化的后格兰诺拉的居民区,结果,我投身于八十年代场最激烈的社会战役的前线,让丈夫跟妻子掐架,小区的四邻掐架的命题是:是用纸袋,还是用塑料袋?






既如此,我们惟一的选择,是采取一种偏向非人类中心生物圈平等主义的全新生态意识。人类必须懂得,物种万千,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并不享有对地球及其资资源的特权。其他物种都有对我们的道义权利,我们没有权利置人类的繁荣于非人类生命之前。我们目前对世界的剥夺和干扰,不只过分且每况愈下。从深生态视角看,每个人都有义务设法扭转局面。

■本文摘自《叛逆国度》一书,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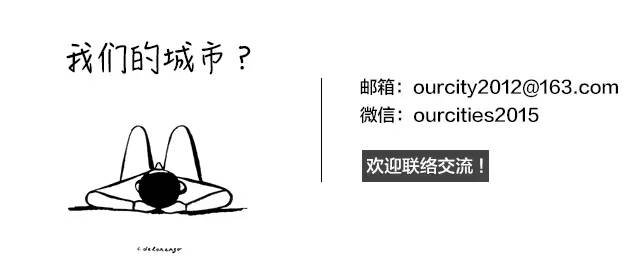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