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旨在考察臺灣戰後到2012年為止不同時期「以農之名」所發起的社會運動,透過比較不同時期農運的原因及訴求來呈現當前農運的意義。農運所涉及的問題不只在釐清運動參與者的階級屬性,同時也涉及到社會運動歷史性的理解。探討農運是什麼,其實也就是在探討我們所處社會的性質、我們所處世界的境況及我們所處時代的特徵。由於原文篇幅較長,我們選取文章的主要内容,分多期進行推送。
臺灣戰後農運的演變軌跡
農運是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結合發展下的產物,它既是現代性發展的結果,也是現代過程所產生問題的表徵。在工業革命及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以前,「民變」的參與者必然包含眾多的農民,這時區分某一「民變」是否為「農民民變」,並無助於界定此一行動的社會性質。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面臨工業的資源爭奪,農村面對都會的競合,農民具有不同於其他階級的利益,這時「農運」也才有了獨特的(sui generis)意義。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分析了19世紀中葉法國農民的狀況,他認為: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繫,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馬克思1995〔1852〕:677-678)
政府與農民的關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型態而轉變。馬克思的分析所對應的是19世紀歐洲的歷史脈絡,與21世紀初的臺灣未必相符,但他對農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說明,卻為我們提供了考察農運的線索。如果19世紀中葉法國的農民必須依賴政府保護他們,將政府視為自身利益的保護者,因此任由行政權擴張以支配社會,那麼在20世紀和21世紀初的臺灣,往往正是因為政府的政策作為無法保護農民,甚至是由於政府的政策作為使農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才讓農民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正是以政府為抗爭對象,人民才會旗幟鮮明地「以農之名」發起運動。
然而社會運動要能夠發生,不只要有課題上的重要性,也必須要有條件上的可能性。戰後臺灣在1947-1987年間實施戒嚴,期間雖然也有以農民為主要參與者的集體行動,但都還只停留在地方民眾抗爭的層次,而沒有「以農之名」來組織社會運動,一直要到1987年解嚴,才第一次出現旗幟鮮明的「農運」。然而此時的臺灣,經歷了四十年的發展歷程,早已從一個農業為主的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為主的社會,並且正在冷戰末期的全球經濟再結構過程中,積極尋求與世界貿易的主導架構接軌,而農業保護正是為了尋求與世界接軌而必須拋棄的籌碼。此時的農業發展面對著與此前截然不同的歷史性,農民同時面對著資本開發力量對農業資源的侵奪以及國外農產品的競爭。也因此,1987年以降的農運發展是三重歷史性交互作用下的產物:第一重是臺灣此前的經濟發展過程造成農業部門的整體衰微(農業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邊緣化、農業生產環境的破壞、農業工作者及農村人口的老化),第二重是臺灣在後威權時代的政治重構,第三重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轉變。
以下我們將依序回顧:(1) 1987-1989年的農民運動;(2) 2002年的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3) 2009-2010年間的〈農村再生條例〉修法運動;(4) 2010-2011年間的反農地徵收運動。我們的考察重點如下:說明三農問題在不同時期如何成為社會運動的原因、不同時期的農運各自提出了什麼樣的訴求、誰是運動主體,並以上述問題的說明為基礎進而分析這些運動的社會性質。
討論這四項運動,並不意味著在1987年之前不存在以農民為主要參與者的集體行動,然而因為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考察晚近農運所呈現的歷史性,在此問題意識下,解嚴前的農民集體行動乃至日本殖民時期的農民運動並非本文所要闡述的重點,而只是作為說明農運性質轉變的歷史參照。無論如何,為了讓解嚴後「以農之名」所發動的農運其性質及意義能夠充分地呈現,在對上述四項社會運動分別進行闡述後,我們會簡單回顧1920年代日本殖民時期及1940年代戰後初期的農民運動,再進入農運歷史性轉變的整體分析。
八〇年代末農運
1. 運動成因及訴求
1987-1989年間,臺灣發生了一系列的農民抗議行動,其中1988年5月20日在臺北街頭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讓這一系列行動被歸結在「五二○事件」的名稱下進入社會運動的歷史。
這場農運的導火線是農產品進口問題。1987年12月8日,面對政府開放水果市場當作平衡中美貿易的籌碼,造成水果滯銷、果價慘跌,由臺灣中部東勢、石岡、和平、卓蘭、梨山、新社等地果農組成的「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動員了三千餘名果農赴立法院請願,是臺灣戰後「第一次大型的農民集體遊行示威活動,首開日後農民運動的先河」(李疾 1988)。梨山農民權益促進會的代表和宜蘭的農民代表提出三點訴求:(1) 改善水果進口政策;(2) 加強德基水庫水土保持工作,解除在1989年以前砍伐集水區溫帶水果的計畫;(3) 減免國有林班地百分之二十的果樹代金。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的代表也提出幾項訴求,包括儘速成立農業部﹐設立農業氣象台,全面實施農保,限區限量限時進口水果,以及開放農地買賣使用之限制等(何明修、蕭新煌2006:90)。往後三個月,全台各地的農民相繼成立了十四個農權會(李疾1988:122)。
1988年3月16日,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結合了其他農民權益促進會,再次於臺北市發起抗議行動,對「中美貿易談判」提出控訴。運動參與者聚集在美國在台協會、經濟部國貿局、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地請願抗議,除了各地農權會之外,並有工黨、綠色和平工作室、環保聯盟、進步婦女聯盟、高雄後勁反五輕自救會、民進黨立委助理、北區八所大專院校學生共同參與(何明修、蕭新煌2006:91)。抗議中提出了反對美國農業帝國主義的口號,並主張在「農、工、商並重」的原則下,讓臺灣的整體經濟得到均衡發展(李疾1988:123)。
歷經1988年3月16日、4月26日中部果農抗議美國農產品進口,5月16日高雄縣六百餘位農民因省政府不同意高雄縣政府提前辦理農民健康保險而包圍省政府,這一系列抗爭到了5月20日升至高點,雲林縣農民權益促進會於臺北舉行五二○大遊行,全省農民權益促進會數千位農民參與(蕭新煌 1991)。
三一六和五二○分別代表了農運發展的兩種不同路線。在三一六和四二六行動後,農運的領導幹部形成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派認為應該下鄉從事組織扎根工作以累積實力,另一派則主張以更激進的訴求和行動方式向當局施壓。五二○行動正是由抱持後一種主張的組織者所發起(李疾1988:125)。根據鍾秀梅的分析,1988年的農運以五二○行動為分界,之前的行動以《夏潮》和部分《美麗島》雜誌的知識分子及山區農民為主;而五二○遊行則以《新潮流》政團為主導,表現出較濃厚的政治色彩(鍾秀梅2011:28-29)。由此,在運動路線的差異之外,運動訴求的內涵也有所不同。
在五二○遊行之前,農運有三大目標:(1) 自主之農業政策;(2) 產銷民主化;(3) 全面改造農會。在此三大目標下提出七項主張:(1) 要求政府當局訂定明確的農業保護政策;(2) 全面實施農民保險;(3) 改革產銷制度,防止中間剝削;(4) 急速防治工業廢水污染農地,訂定〈農業資源污染防治法〉;(5) 推動計畫生產;(6) 提高農產品收購保證價格;(7) 廢除水利會(鍾秀梅2011:28)。五二○遊行提出了七大訴求:(1) 全面辦理農保及農眷保;(2) 降低肥料售價;(3) 增加稻穀計畫收購量;(4) 廢除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5) 水利會納入政府編制;(6) 設立農業部;(7) 開放農地自由買賣(蕭新煌 1991)。對照兩者,可以發現農民保險、農產品收購(價格或數量)、農會及水利會改造是兩組訴求的共同點,在此之外,前者更關注於農業保護政策、產銷制度改革、防治工業污染、推動計畫生產等與農業經營環境的維護與改善相關的項目,而後者則更關注於農政部門地位提升、肥料售價、農地買賣等非著眼於農業經營環境維護的項目。在這些訴求中,特別要注意的是最後一項:「開放農地自由買賣」。
2. 五二〇農運中的「自由化」
農地無法自由買賣,源於1930年〈土地法〉第三十條的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有權之移轉無效。」此項規定於國民政府遷臺後沿用。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的工業化進程中,許多農業土地被用來蓋工廠,為了防止工業擴張持續侵毀優良農地,1973年8月的行政院會決定,「嗣後農用良田,不得再行轉作他用」;「興辦工業人不得使用一至六等則農田設廠」。同年9月,行政院發布〈農業發展條例〉,其中第九條規定:「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農業用地變更為工業用地時,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規定農地農有和農地農用,目的在保護農業發展的土地根基,但這也就意味著將農地從一般的商品範疇中排除出去,由國家以法令來管制其流通。然而在以農養工的政策影響下,農業勞動收益微薄,農家下一代往往無人接續務農,導致農業勞動人口日漸老化。另一方面,解嚴後對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挑戰中,農地限制買賣被理解為威權政體對人民自由的箝制,因此農地去管制也變成反威權、爭自由的一種表現。農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對待,結合上當時臺灣社會亟欲推倒威權政體的各項管制,使得農地開放自由買賣成為五二○農民運動的訴求之一。
農運中出現開放農地自由買賣的訴求,從更大範圍來看,事實上是在後解嚴時期整體「自由化」運動中的一個環節。由於自由化運動的目的在推翻黨國威權體制施加於社會之上的各種管制,從而不只是在政治上,並且在經濟上都以「自由化」為訴求及目標。政治自由化與經濟自由化在此找到了共同基點,在甫解嚴的臺灣表現為具有矛盾性格的農民運動。其矛盾性在於,農運的導火線是開放農產品進口,而開放農產品進口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雷根政府貿易制裁壓力下所做的讓步,換言之,也就是臺灣為了與美國推動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政經秩序接合所讓出的籌碼。臺灣農民提出限制水果進口的主張,卻同時主張開放農地自由買賣,也就相當於在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經秩序的同時,要求按照經濟自由主義的邏輯,讓農地成為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
五二○農運終究沒有扭轉農產品開放進口的世界貿易遊戲規則,但卻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與農運之間的矛盾關係悄悄地揭開了序幕。悄悄地,是因為這項矛盾在解嚴後臺灣追求自由化的社會潮流中,根本不被運動組織者及研究者所注意。彼時,研究者關注的是長久被威權政體所支配的人民如何成為行動主體,以及社會運動如何能夠開展和持續。
3. 五二〇農運的性質
五二○農運清楚地標舉了農民權益的旗幟,甚至以「農權」作為運動組織的名稱。對於這場運動的社會性質,蕭新煌(ibid.: 82)曾有如下的評論:
自1987年底至1990年夏這兩年多的農民運動,其最大特色是經由動員小農長期以來對國家農業政策不滿的心理與情緒,轉變之而成為一種基於「受害者意識」的集體抗議行為,抗爭對象是農村社會以外的國家機器。
然而農民是否能在運動之後維繫能量,並透過組織行動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成為扭轉自身命運的行動主體呢?當時學者的看法毋寧是有所保留甚至是悲觀的。蕭新煌認為:「如果農運團體不將農運場域從城市轉回農村,那麼小農性格的蛻變契機將無法保固和持續」(ibid.: 89)。要將農運場域轉回農村,是因為農運還有另一重要使命:「農村社會內部的改造」(ibid.: 86)。這不只意味著在都會區動員抗爭之外必須回到農鄉在生產場域組織農民,這同時也意味著農運涉及的不只是農民的階級利益,還涉及到農業的存續與農村的興衰。但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中,學者關注的焦點主要還是在於「社會改造」,農村改造被看成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環。
對於農運的未來,除了蕭新煌提出社會運動的性質診斷,趙剛也從歷史發展趨向提出了如下的判斷:
從世界體系的層次來看農運,則無論頻率、規模和影響力都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境況。對照這個沒落中的世界農運的大環境,臺灣農運的黎明曙光,可能也是日落餘暉。(趙剛1989:213)
就臺灣特殊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而論,作為當今解嚴後眾多社會運動一支的農民運動,可以說有歷史上與結構上的必然性。但是,如從臺灣今後階級與政黨關係的重構,與世界農運史的角度來看,臺灣的農民運動將不會像工運、學運、環保運動,甚至婦女運動一般「方興未艾」。長期而言,農運的前景將是黯淡的。(ibid.: 223)
在1980年代末,趙剛認為農運前景將是黯淡的。如果經過二十年後,農運在臺灣獲得了新的動力,那麼重要的並不是質疑個別研究者於二十年前針對當時社會狀況所做的判斷在今日是否仍然適用,而在探討社會條件、生存環境以及由這些條件及環境所蘊生的集體行動,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
1. 運動成因及運動主體
2002年11月23日,超過十二萬名來自臺灣各地的農漁會員工及農漁民走上臺北街頭,主辦單位宣稱這場運動共有十三萬五千位農漁民參與,「創下了臺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運動紀錄」(丁文郁總編2005:6)。
之所以發生這場運動,源於當年8月財政部發布〈農漁會信用部分級業務管理規定〉,計畫按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率高低對全國農漁會實施分級管理,因此造成基層農漁會強烈反彈。按照行政院的規畫,經營不善的農會信用部,將由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賠付負債超過資產之差額後,強制讓與行庫概括承受。為了維繫自己的生存,全國304家農會與40家漁會於2002年9月5日共同組成「全國農漁會自救會」,決議發起這場「一一二三與農共生——全國農漁民團結自救大遊行」。
信用部分級管理與信用部存廢並不等同,農漁會也並不等於農漁民。為了將運動發起組織「全國農漁會自救會」與運動名稱「全國農漁民團結自救大遊行」所界定主體的差距在語意上接合起來,全國農漁民自救會喊出的口號是:「支持改革,反對消滅」;提出的運動主軸則是:「農業等於農村,農村等於農會,農會等於農民」(ibid.: 123-124)。在語意的置換中,分級管理被詮釋為消滅,而農會被安插在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經常被並稱的辭彙中,三農變成了四農,農會與農民被等同。
誠然,農漁會信用部與農業金融息息相關。隨著農業金融機構逐漸移轉給以營利為主要目標的財團銀行,農漁民將面對較為不利的融資條件,因此農漁會信用部的分級管理當然與農漁民有關。然而,這項措施衝擊最大的還是農漁會。「對農會員工來說,信用部被接管代表的可能是立即的失業危機,對領導階層來說,則是直接剝奪其掌控地方政治經濟網絡的管道,二者的動員誘因其實與大多數農民是不同的」(林御翔2005:121)。在運動組織者〈給農漁會同仁的一封信〉中,用了如下的口號來呼籲利害關係人進行動員:「有十萬,一切有希望;沒十萬,各自求轉行」(丁文郁總編,2005:78-79。)。當然,達到動員十萬農漁民的目標之後,能夠免於轉行的並非農漁民,而是「農漁會同仁」。總言之,農民並非這場運動的主體,而是農會動員的對象。也因此,吳音寧於《江湖在哪裡?》這本描述臺灣戰後農民、農業、農村沉淪過程的著作中,將「一一二三與農共生」界定為「農漁會遊行」,而非「農漁民遊行」。
2. 成功動員農民的組織條件
然而何以農漁會遊行卻能夠動員如此多的農漁民參與?就算參與遊行的12萬人中有許多是農漁會員工及其親友,但其中的農漁民數目必然也遠遠超過戰後臺灣的任何一場農運。林御翔(2005: 121-122)認為「一一二三與農共生」之所以能夠動員如此多的農漁民參與,原因在於自救會組織幾乎完全承襲農訓協會的人力與硬體資源,讓自救會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就迅速運作起來。透過農漁會綿密的組織網絡與人脈,加上其與農漁民之間特殊的恩庇關係,讓抗爭動員過程的組織成本大大降低(Ibid: 111)。以農訓協會為核心來組織農漁會,以農漁會的網絡動員農漁民,是這次運動可以達成大規模動員在組織層面的原因。
蕭新煌在分析五二○農運時說:「如果農運團體不將農運場域從城市轉回農村,那麼小農性格的蛻變契機將無法保固和持續」,這讓人想起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於小農無法形成政治組織的說明。然而臺灣的小農並非沒有組織,而是由農會系統所組織。農會不只是在生產層面上進行組織,並且以生產為基礎來進行不同層面社會生活的組織。
農會為地方人際網絡的中心,支援農業推廣、訓練工作,除了作為基層金融樞紐,更兼具政策推廣與社會福利功能。在地方選舉層次,農會也兼具動員角色,特殊的組織型態,使農會、農會信用部以及其廣大的會員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此種組織與統一性成為最基本的集體資源,也是對其他資源進行動員的基礎。(林御翔2005:119)
正是由於農會結合了多面向的功能,建構起密切交織的連帶網絡,使得農會和農民難以分割。而農會在提供農民以各項服務的同時,也培養了自己對農民的動員能力。
3. 農民參與遊行的心理動力
組織體系和連帶網絡能夠說明大規模動員在技術層面的可能性,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農民上街頭。關於後者,當時擔任自救會執行祕書的農訓協會企劃處處長顏建賢如此解釋:
本次「一一二三與農共生」大遊行之所以能結合農漁民與農漁會的大團結,實肇因於政府未能在我國加入WTO後,謀求如何振興農漁業、活化農漁村、改善農漁民生活,卻先將農漁民長久依賴的農漁會組織要先「改革」掉,……(顏建賢2003:48-49)
上段文字說明了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發生在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背景中,並且此一政經脈絡是農漁民之所以會被大規模動員在社會層面及心理層面的原因。陳建甫(2005: 193)認為:
2002年1月1日臺灣加入WTO,對大多數亞洲國家而言,加入WTO的第一年通常是農民運動蓬勃發展的一年,但是臺灣卻沉寂了,這次剛好利用農漁會金融改革這個機會,再加上從7、8月開始農產品價格估計調降二、三成,甚至低估到四成的情況下,農民不滿的情緒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挑逗而逐漸甦醒。
農民被動員不只是因為與農會之間的人情關係,而是因為他們自己心中早已有某種不滿情緒,農漁會信用部被接管這件事,只不過是讓農民積累已久的不滿情緒得以被動員而爆發出來的導火線。農漁會信用部可能被接管是農漁會員工走上街頭的原因,農民長期累積的不滿情緒則是農民願意被農會動員上街頭的原因。受邀撰寫運動文告的楊渡提出了如下的分析:「這一次農民大遊行之所以能夠動員這麼多人,根本的原因不僅是農漁會信用部將被全面接管,也不僅是三十六家被接管所傳出的交易太讓人不平,而是農民本身的憤怒」(楊渡2003:33-34)。也正因為農民有許多憤怒,農漁會才能動員農漁民。
農民的憤怒情緒來自於長期以來的生存困境。然而這次運動有試圖解決造成這些困境的問題嗎?讓我們先檢視這場運動的訴求與主張。
4. 一一二三與農共生運動的三大訴求、十大主張
全國農漁民自救會共提出三大訴求、十大主張(詹朝立2003:328-329):
【三大訴求】:
1.搶救臺灣農漁業與農漁民。
2.咱農漁民需要農漁會繼續提供服務。
3.制定以農漁會信用部永續經營為主軸之〈農業金融法〉。
【十大主張】:
1.速依法編足「農業發展基金」一千五百億,及「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一千億。
2.依法落實推動老年農民退休制度。
3.成立「全國性城鄉交流與鄉村活性化」機構,以加強城鄉交流,促進農業發展。
4.本會期通過自救會版〈農業金融法〉,設立「全國農業金庫」,並建立以農漁會為基礎的農業金融體系。
5.修正〈農會法〉與〈漁會法〉,中央主管機關一元化,由農委會監督輔導農漁會。
6.實施股金制度,確立農漁會為多目標功能的農漁民合作組織。
7.停止實施現行農漁會信用部業務限制令,放寬農漁會信用部經營項目。
8.歸還已被強制讓與銀行之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回歸農漁會體系。
9.修正〈金融機構合併法〉,讓經營不善之農漁會信用部得讓與其他農漁會承受。
10.請確實執行阿扁總統競選時所提出之「農業政策白皮書內容」。
上述三大訴求中的前兩條,基本上是重申農漁業、農漁民、農漁會的重要性及彼此的密切關係,第三條制訂〈農業金融法〉才是這次運動的核心訴求。在十大主張中,第一條到第三條分別針對農業、農民、農村提出主張,特別第一條是針對加入WTO對農業部門所造成損失要求給予救助。第四到第九條要求調整農會及農會信用部的經營架構及規定,其中第五、第六條意在修正農漁會的經營架構,第四、七、八、九條是與農漁會信用部及農業金融體系等課題相關的條目。
面對這場運動龐大的動員能量,政府隨之讓步。11月30日召開的「全國農業金融會議」,達成「充實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及農、漁會與信用部由農委會一元化管理」、「設立全國農業金庫為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貫徹金融監理一元化」、「制定農業金融法」及「提升農業經濟的競爭力」等五項共識。〈農業金融法〉於2003年7月頒布,2004年1月30日開始實施,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成立了農業金融局,全國農業金庫也於2005年5月26日正式開業,被強制讓與銀行的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也重新回歸農漁會體系。「一一二三與農共生」的十大主張中,與農漁會、特別是農漁會信用部相關的項目大有斬獲。那麼在農漁會已經「獲救」之後,「農漁會自救會」是否有繼續帶領農漁民解決農民、農業、農村所遭遇的困境呢?
▼
本文于今年九月刊发于
《文化研究》(台湾)2016年秋季刊
由作者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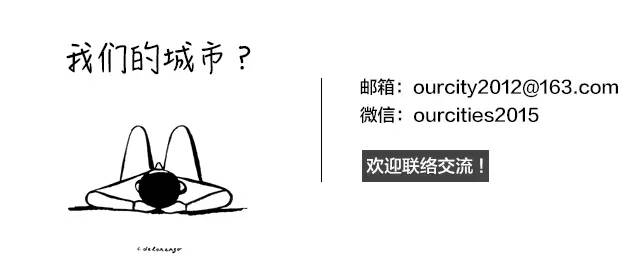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