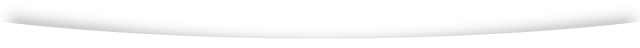
《世界建筑》2017年第8期
价值、阐释与真实:
五龙庙环境整治项目思考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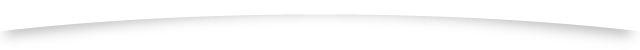
3. 建筑本体的阐释尺度辨析
“存在感”是五龙庙的环境整治中不断被提起的一个概念。王辉不仅要再现这座千年建筑的存在感,也要使乡民获得身份上的存在感。通过改善环境品质,融入当下生活,以及为这个历史村庄的发展引导出未来的方向,从而为道德迷失的村民重建精神体系。但面对即将被岁月耗尽的精神能量,王辉所做的便是利用有限的环境将仅存的能量进行放大,而放大的工具便是对环境进行重新“编码”。然而新的“编码”是否会引起语义的变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异质性建构是否会对建筑本体的解读带来歧义呢?其实王辉深知其中的语言陷阱,“这种植入虽然是从文本的‘元’信息出发,但它已经演绎出更多元的结果,在丰富了原文本内容的同时,也增加了文本的含混性、多义性”。 1(111) 但他依然认为建筑在历史变换中受到“编码”是一种正常现象,一次普通的落架维修或局部材料的替换都是一种信息编码行为,因而环境整治中新信息的介入无可避免。那如何既要对原有单薄的信息进行增殖,又要避免陷入列斐伏尔所警告的陷阱呢?“一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让新的信息与文物本体保持必然的关联性,保持文物本体的核心性加强,而不是被稀释;另一方面,这种再创造的主题是为了实现设计主旨的手段,而不是主旨本身,即用空间体验的明线激活工作目标的暗线。” 1(111) 这是王辉在阐释五龙庙历史价值时所采取的手段,但即使对于“元”信息的小心翼翼的“编译”依然没有躲过列斐伏尔的警告,那些因阐释而生的符号开始在设计的过程中不断蔓延。 ④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保证内容的真实、完整与准确性可以说是阐释工作的前提条件。在环境设计过程中,王辉及设计团队对五龙庙、南禅寺、佛光寺和天台庵的斗拱进行了足尺仿制,并置于旁边的斗拱院。正是这些模型(图示化的符号)在表达原对象的形制之时,也表达了自身的存在。使用混凝土与钢板(佛光寺大殿斗拱模型)进行木斗拱的仿制与其材料属性也不相符,灰色混凝土以及黄色喷涂钢板所焊接的摹品斗拱散发出的冰冷气质与刻满岁月印记的原木斗拱相去甚远,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图5)。材料的替换或许会给摹品带来戏剧性的展示效果,但同样也容易引发普通游客的错觉。诚然,现实中不乏将斗拱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构件予以展示的案例,但基本都是在所模仿的对象没出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即便要进行摹品的制作也应使用原有斗拱所用木材进行足尺复制,尽可能全面展示其特性、尺度与建筑其他部分的构成关系等,而非进行关键材质的替换。

图5/斗拱庭(摄影:张建军,2016年6月)
其次,五龙庙及山西部分经典寺庙建筑被浓缩为一系列的简图展示于东西两侧的庭院。在序庭中,墙面上的序列图示描述了山西传统建筑的发展线,用以说明五龙庙在此演变中的角色。同时,正殿的等比剖面图也被镌刻在地面之上(图6)。与置身于大殿中的观察方式不同,人们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观看方式在解读五龙庙建筑。这些图示成为阐释五龙庙历史价值的元语言,也正是这些从主殿抽象而来的图像剥夺了本体的话语。通过这些符号(元语言)的不断复制与增殖,现实本体被抽象符号逐渐替代。观者的目光也转而聚集于异质的摹品与抽象的图示之上,随着阐释方式的增加与规模的增大对于建筑本体的弱化也就愈加明显。这些图示的出现转移了人们对于近在咫尺的原件的观察,也削弱了五龙庙大殿作为一个整体给人带来的感受。

图6/序庭(摄影:张建军,2016年6月)
那么什么是正常的阐释呢?笔者认为,这还是要回归至对于建筑本体的展示中,特别是在阐释对象并没有离开原有存在环境(即非异地展示)的情况下,无需借助大量的图示、模型,以及视觉化的手段对其进行辅助性说明。就本案来说,近在咫尺的大殿本身便是最佳的述说者,让五龙庙自身去述说这千年来的沧桑变化,而我们能做的则是摒除多余的干扰,为他提供一处符合其独特气质与历史价值的物质环境,而不应削弱或剥夺其作为阐释主体的地位。即便要对某些重要或特殊之处进行释义,也应尽可能以文字或少量图示(不影响展示主体地位)作为引导,而不是制作与本体相似或重复的展示内容。在建筑遗产的展示与阐释过程中,建筑本体始终是表达的主体,其阐释的方式与程度应符合本体的特质与可承受范围,且不可让冗余的符号与图像将其遮蔽。因此,笔者不赞成部分学者所说“环境整治对象选择错误”的观点。环境的整治不应因保护对象是唐代还是清代,是稀有还是数量众多来确定,而应建立在细致的研究与审慎的判断之上。
4. 历史语境及其真实性解读
如果从王辉所设定的“编码者”与“解码者”的身份来分析,让文保学者们最难以接受的或许是他利用环境“绑架”了建筑,即通过现代简洁的外部空间环境设计将这座千年古庙从恒定的传统语境中剥离出来。正是这种“视觉效果”与“身份变迁”促使五龙庙在“重生”的同时,也被抬上了展品台。建筑与环境的对立使得正殿与戏楼从“历史的证言”变成了“历史的展品”。这是典型的后现代建筑设计手法,通过并置不同时代的元素来制造空间张力与历史想象。在这里新建的庭院既是一台信号增强器,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展品台,其功用是让两座历史建筑从日常用品转变为一件艺术品,如同置于客厅的一件家具被移入了博物馆的展厅。作为展品的主殿与戏台尽管没有被移入异地的博物馆,但是一座新建的博物馆却将它们纳入其中。尽管这种作为展品的内质转换是从五龙庙被划为历史保护文物时开始的,但“展台”的出现却空前放大了文物建筑作为艺术品的这一特性。尽管建筑依旧,但是人们对这座古庙的认知却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新环境所营造出的氛围已经对五龙庙的建筑本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凸显这所千年庙宇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建筑周围的场地被仔细地清理,地面被覆以浅色砾石,周围的隔墙也被一种黄土机理的陶质挂板所包裹(图7)。这些景观性的隔墙在改变空间格局的同时也将因阐释而增殖的符号围合其中。精心布置的庭院开始散发出广场般的特质,这种非中国传统所有的西方城市舶来品已经融入了五龙庙的宗教空间。也正是在这忽明忽暗的空间与符号变换中,五龙庙作为博物馆的身份得以呈现。 ⑤ 客观来说,环境的调整确实在视线上使得五龙庙更加突出,新建隔墙也都确保了建筑主体的景观效果呈现。 ⑥ 但“异质材料的介入”“新的叙事线索”以及“空间形态的调整”都促成了全新的场所认知与空间体验。随着周边庭院的设立,观者的目光已经悄然转移,原来对于建筑本体的视觉探索,转移到了对于抽象的图示的解读;对于建筑整体的空间感知与体验,也转移到了对于单个摹本部件的观察;建筑本体所具有的无形的价值也被分散到周边有形的仿品与图示中。

图7/从思庭洞望正殿(摄影:张建军,2016年6月)
这种现代(环境)与传统(建筑)上的碰撞在相对保守的观者眼中产生的是一幅超现实的图景,一种空间感知上的不真实。如前所述,环境是一种语境,这种语境应符合建筑本体的特质,其作用在于如何呈现建筑本体,而非自我呈现(图8)。对此《内罗毕建议》的第4条曾作出如下规定: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得到积极保护,使之免受各种损坏,特别是由于不适当的利用、不必要的添建和诸如将会损坏其真实性的错误或愚蠢的改变而带来的损害,……也应十分注意组成建筑群并赋予各建筑群以自身特征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对比所产生的和谐与美感。 5(94) 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在讨论“价值与真实性”的第5条中也指出: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语境、时间演进,真实性评判可能会与很多信息来源的价值有关。这些来源可包括很多方面,譬如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感情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因素。 5(141) 而《准则》第42条也指出:优先利用属于文物古迹的建筑进行展示和游客管理,尽量不建新的设施。如确实需要增加新的展示和游客服务设施,必须确保新建设施不损害文物古迹及其价值,并把新建设施对文物古迹和周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尽可能远离文物古迹本体)。 4(29-30) 上述条款的核心意思已经清晰地表明:文物古迹的价值有赖于“文化语境”的真实性,与历史以及当下的身份(将其置为何物)密切相联,同时也涵盖了建筑本体与周边环境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既可以是环境从属于建筑,也可以是建筑从属于环境,但在五龙庙这个案例中,显然建筑的价值决定了它是“主人”的身份,而环境则应该从属于建筑,它既不应成为另一个展示的主体,也不应成为主体的华丽背景。

图8/戴克里先浴场遗址(图片来源:http://www.lazioeventi.com,浴场的周边环境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其历史状态,仅在靠近城市道路的入口处进行了硬质铺装,其他区域及植被均未进行改动,远处内庭院的斜向小径也形成于古罗马时期。)
5. 结语
笔者并不反对环境的整治与改造,而是赞成符合遗产身份的有限度的设计。文物古迹的保护、修复与改造应尽可能地尊重原有场所的精神与文化的语境,尽可能减少对古迹显著特征与自然环境的破坏。避免因符号的移植、借用与阐释对建筑本体的理解造成歧义,应尽可能减少因异质材料的介入而带来视觉的碰撞与冲突。尽管五龙庙的环境整治存在着许多争执与质疑,但仍是对我国当代文保事业的一个有力推进。从整治的结果来看,一个满足乡民日常休憩与精神寄托的场所显然比一个无法还原的历史环境更加符合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这对缺乏公共空间的乡村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文物建筑虽是历史证言的载体,但是社会在发展,载体也在岁月的消磨下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我们的保护理念,还是具体的实施方法都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客观来说,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无时无刻都面临着一种取舍与权衡,没有一栋历史建筑的保护可以符合所有原则,也没有任何原则适用于每栋历史建筑。这既需要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勇气去做出抉择,也需要根据每一座历史建筑的实际状况去做出理智判断。
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注释:
④ 符号学认为:一般语言分为“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而两者指明的外在物体则称为“指称物”(referential)。传统观点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是精确对应的,但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以来的科技及社会发展使得二者之间的稳定关系发生了变化。正是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图景冲击导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通感观念的消失(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M].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112)。在由技术性幻象营造的氛围中,客体被抽象为符号,并取代了现实中的本体存在。指称物的消失使符号脱离其物理基础成为最高本质,即“元语言”,而对“元语言”的随意调用、扩展、引申、编译、延宕与书写则造成了“能指”与“所指”间的紊乱。对此,列斐伏尔说到:“身处此世,你却不知自己立足何处;如果你想将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便顿时如坠五里云雾。”(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M].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25)。
⑤ 此处的“忽明忽暗的符号”与王辉先生在其文中的“明线”“暗线”相对应。
⑥ 五龙庙的环境调整具体如下:正殿和戏台之间通过压缩东西厢院墙的距离而获得更好的尺度关系;南侧广场路边通过拆掉一处房子而获得向田野敞开的视廊;北侧通过观景台看到中条山和古魏城墙遗址;用种植由临近黄河边采集来的芦苇勾画无水的五龙泉。
参考文献:
1 王辉. 广仁王庙环境整治设计的理论性思考[J]. 世界建筑,2016(7).
2 米歇尔·佩赛特,歌德·马德尔. 古迹维护原则与实务[M]. 孙全文,张采欣 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53.
3 China ICOMOS.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Publication by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2.
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5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郭龙,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
相关链接:
美术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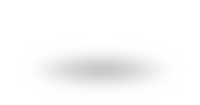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