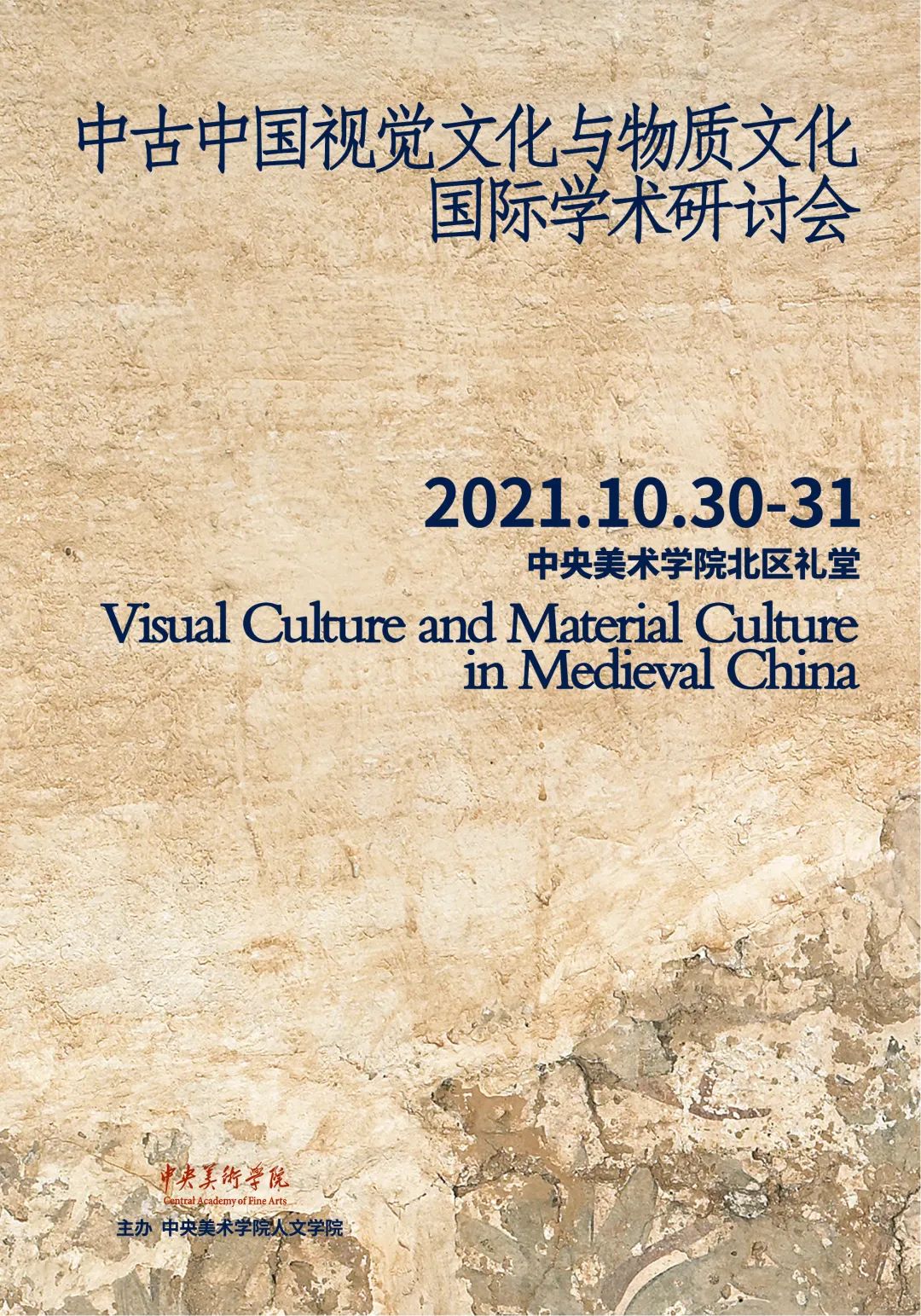
2021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古中国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央美术学院北区礼堂和腾讯线上会议同步举行。本次会议是人文学院继成功举办2017年“美术史在中国”、2019年“明清中国与世界艺术”等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后,再一次召开的学术盛会。来自国内外艺术史、考古学、历史学和科技史界的40余位学者跨越时空隔绝,与人文学院师生线上线下齐聚一堂,切磋学术,气氛热烈而融洽。本次会议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反映了近年来人文学院在追求新文科创新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学界的肯定。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视频致辞
开幕式于10月30日上午举行。开幕式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教授作视频致辞。他表示,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为中国的艺术史与考古学者以及国际同行们构筑了一个广泛交往、深度交流的平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视野、新问题、新材料与新方法,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将“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相连,从多维的研究视角打破传统学科概念,有助于丰富艺术史的书写,建构新的学术研究格局,更有助于重新认识和思考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合为一体的文化生命力,由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美术史研究体系。
范迪安谈到,中央美术学院始终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从当年的美术史系到今天的人文学院,从学科的内部建设到扩展的学术文化功能,从几代优秀的教授学者筚路蓝缕到一批批有志的青年学子竭力传承,积累形成了视角丰富多元、辐射范围宽广的研究与教学格局。这些年来,人文学院坚持弘扬优秀学术传统,积极探索学科发展新的结构与内涵,增加了文化遗产、视觉文化理论等专业,加强了历史哲学的支撑,尤其在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的关联性研究上有了新的拓展,这些都体现了大学文化传承的功能,为新时代艺术人文学科建设打开了新的路径。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致辞,他说道:
最近我在几个地方讲话,开头都表态“我只说三句话”。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不想占用大家专业讨论的时间;不过里面也有我自己个人的原因,因为三句话不离本“杭”嘛,谁让我是个杭州人呢。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叫“我们曾经也阔过”。这句话听上去怎么那么像是败家子说的话呢?正因为家大业大,好像才经得起败家子的糟蹋?但无论如何,我们家曾经阔过,却是千真万确的。中央美术学院曾经于1957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标志着现代美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建成;64年来,美术史学科在中国前所未有地繁荣和发展,或多或少都会与央美美术史这棵大树的栽培或庇荫有关。在中国中古艺术史领域,离开央美美术史前辈王逊、金维诺、薛永年、汤池、王泷、薄松年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开拓与耕耘,其面貌是难以想象的;在座或在线上的巫鸿、罗世平、尹吉男、贺西林诸先生,都是从这棵大树上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果实;当然,他们取得的辉煌的成就,也令母校倍感自豪、蓬荜生辉。
我要讲的第二句话,叫做“尽管我们现在也不穷,但是我们很谦卑”。我们现在是不是很“穷”,好在这次大会上有众多人文学院老师们的在场;他们的发言行不行,实际上不应该由我们,而是由在座的同行和朋友们来评判的。我想强调的是后一个意思:“谦卑”,也就是“低调”——顾名思义,“低沉的音调”,也就是贴近大地的音调——怎么听上去有点像美术考古的意思?对的,低调就是为了贴近大地,去倾听大地深处被埋没的历史文化发出的声音。正是为了听到地下祖先的声音,我们不能不保持谦卑的姿势;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听到祖先的声音,我们不能不秉持谦卑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考古学家的探索与发掘、历史学家的文献考释、科技史家的年代鉴定——没有其他学科学者们的贡献,那些地下开出的人类文明的花朵,是不会自动送到我们这些艺术史家眼前的。哲学家巴赫金曾经说过,“自我是他者的馈赠”;或许我们可以仿造着说,“学科的特性同样是其他学科的馈赠”。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艺术史家、历史学家、科技史家、考古学家们——今天之所以相聚在一起的理由;在于我们自己天生的无知和眼痴,在于我们之所能,只是为被埋没的历史文化,贡献出自己有限的经验和感性——无论是触觉还是听觉、理性还是想象,以便于终有一天,我们能够从大地深处,真的唤醒和复活一头人类文明的大象,直到听见它行走于中原之上的跫跫足音。
我想讲的第三句话,是表示“深深的歉意”。两年来疫情的无常与反复,已使全人类都习惯了一种类似于刘慈欣在小说《三体》中描绘过的那种三体人的生活。在小说中,是因为三颗太阳无规则的运行而导致三体文明百余次地毁灭与重生;在现实中,则是因为病毒无规则的肆虐而使我们的生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封闭与重启。按照原定计划,今天的这次会议本来应该于去年召开;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重温的其实是过去失去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我们的今天是生活于昨天的梦想之中。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危情,又使我们迫不得已取消了线下的相聚,造成了今天,线下的央美人与线上朋友们的分离与分裂,情何以堪;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把未遂之愿投射到明日的蓝天之上,与未来做一次约会。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让我们相约明天,同时开始今天的精彩!
开幕式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贺西林教授主持。
研讨会围绕中古中国“考古新发现”“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理论与方法”“思想与观念”“礼仪、制度与文化交流”六大议题展开,艺术史、历史学、考古学、科技史等研究领域的与会代表就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第一场报告由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张建林教授与北京大学杭侃教授评议。5位发言学者分别介绍了不同地区墓葬或遗址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并阐述了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介绍了咸阳洪渎原唐代壁画墓的发掘情况,重点就康善达和杨知什夫妇墓壁画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文博馆员龙真结合考古新材料讨论了历年来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的思想意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建华使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2018血渭一号墓的情况,肯定了阿柴王陵的吐蕃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利群介绍了近年来邺城相关遗址、窑址、宫城区的发掘情况以及出土的部分宗教造像遗存,强调了遗迹发掘和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谢西营介绍了慈溪上林湖越窑中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概况,揭示了唐五代越窑青瓷,特别是秘色瓷的发展状况和具体面貌。
第二场报告由复旦大学李星明教授主持,围绕中古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展开。山东大学李清泉教授与北京大学韦正教授评议。5位学者就早期绘画的题材、技法、意涵等问题展开研讨。
北京大学郑岩教授以北朝石葬具画像为中心,对相关视觉材料进行了梳理,认为独立的人物、山水、台榭、花卉绘画形式于6世纪已初露端倪,为探究早期绘画分科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央美术学院吴雪杉教授以东晋顾恺之的画论为切入点,对相关视觉材料中人物眼睛的表现方法进行了细读,并将其与印度佛像传统中的“莲花眼”建立关联。中央美术学院耿朔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都谈到了中古墓室壁画中的改绘现象。耿朔以北齐徐显秀墓壁画改绘痕迹为例,总结出技术型调整、题材与构图改动两种情况,并尝试从背景和动因两方面就此做出解释。李梅田则认为墓室壁画改绘的原因包含对前代建材改造、画工失误等因素,并强调了合葬时间和身份等级之差造成的影响。中央美术学院赵伟教授结合文献就唐代赫连简墓“树下老人”图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该图式是道教法师参与世俗丧葬活动的表现,反映了“内儒外道”的生死观。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主持,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馆员和南京大学张学峰教授评议。5位学者围绕不同物质材料遗存发表了有关中古中国物质文化的最新研究。
中国科学院苏荣誉教授以两驾青铜牛车为例,讨论了中古青铜车模的形制结构、铸造技术以及功能内涵等问题,并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整个欧亚大陆。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纪东歌以故宫藏吴晋堆塑罐为引,探究装饰工艺在纹饰图像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对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交融在陶瓷器装饰上的体现进行解析。武汉大学魏斌教授围绕云峰三山北魏郑道昭题刻展开讨论,分别将其赋予神仙思想、逝者纪念及个人修道空间的思想意涵,认为其延续了汉晋以来对神仙世界的想象,与当时江南流行的神仙洞天观念及山中道馆修道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杨军凯以唐康文通墓中出土的彩绘釉陶俑为例,讨论了初唐至盛唐釉陶俑和彩绘陶俑的发展变迁,阐明盛唐之后釉陶俑消亡的主要原因。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教授对金仙公主塔进行了一系列复原性探究,厘清了一座唐代石塔被挪用为金仙公主塔的缘由,由此反思美术史研究中的挪用与误读现象。
10月31日上午进行的研讨会第四场是以“理论与方法”为题而展开的学术对谈,由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主持,来自艺术史、历史学、考古学界的10位学者进行了互动。
对谈会上半场,李军教授围绕美术史学方法论和视觉文化研究等核心问题,结合与谈学者的研究方向进行发问并展开交流。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通过分享自己的研究经历,折射出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术动向。他谈到本世纪初视觉文化研究的流行重写了“美术”的概念,拓宽了美术史研究的范围。广州美术学院尹吉男教授认为早期美术史研究由于缺乏同期材料支撑,“二重证据法”的有效性受到了限制,而美术史家也在不断探求新的方法路径,并点明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面临的特殊语境。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在对谈中强调了视觉材料对中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尤应注意视觉文化的传播与文本材料之间的关系。另外他还谈到了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学说的内在逻辑,特别联系到晚唐五代至北宋的视觉转型问题。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教授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经验,认为方法是潜移默化地融入具体写作中的,同时指出当今美术史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本体,已然切入了思想史、社会史,甚至政治史。
下半场对谈会中,李军教授和与谈学者就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开启话题,涉及对物质文化研究维度的理解,跨学科之间理论方法的借鉴与反思,对未来学术动向的展望等议题。美国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艺术史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反思了以往对传统历史文献和理论框架的过度侧重,以及近十年来对物质性的过度关注。他指出当今艺术史就物质文化研究,需要探寻表层物质性及其背后深层理路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艺术体验的重要性。美国芝加哥大学林伟正副教授强调了器物材质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或可在“材质艺术”的概念下进行物质文化研究。四川大学霍巍教授从考古学角度思考了美术史研究的贡献,肯定了美术史研究在传世作品的年代鉴定上获得的丰硕成果,从美术史研究的角度补足了透物见“人”的维度,为考古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他同时举例说明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方法利于在研究中回归原境,挖掘物质背后的文化思想。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指出,使用美术史方法有助于在历史研究中使图像和物质重回历史现场,从而充分了解历史原貌。浙江大学余欣教授反思了“以图证史”的研究方法,指出图像具有自身的脉络,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另一种文本。他认为“物”的历史学研究当超越物质性和文本性,应将“物”置于信仰、风俗等历史原境中去考察,以此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第五场报告以中古中国思想与观念为题,由中央美术学院罗世平教授主持,北京大学郑岩教授与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教授评议。5位学者的报告皆围绕中古中国宗教美术展开。
北京大学杭侃教授通过梳理云冈石窟的营建时间与过程,对第5窟和第13窟的分期问题进行再思,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加以考察,为探讨石窟中呈现复杂面貌的缘由提供了线索。北京大学李松教授讨论了云冈石窟大佛眼珠的形式、材料和制作方式,并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对佛眼的制作动机和工艺变化进行阐释。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南南从瑜伽系大乘菩萨戒的角度重新探讨了莫高窟275窟的功用,并提及北凉三窟之间的联系。中央美术学院王云教授关注到了一种被释读为博山炉的宗教图案,她结合佛教教义、道教仪式并运用图像对比的方法,指出这类图像与“光明”的意涵有关。中央美术学院郑弌副教授以隋至初盛唐之际法华图像的演变为中心,围绕几组个案探讨了此期佛教信仰与艺术表现的转向问题,旨在建立一种将中古图像复归于整体社会文化景观下进行研究的方法。
第六场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苏荣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李松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评议。5位学者以中古中国的礼仪、制度与文化交流为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
北京大学韦正教授关注到大同寺儿村古墓出土的一件北魏石雕,通过对其细节特征的考证,修正学界对该石雕的原有认知,指出石雕展现了北魏平城时代鲜卑的“军傩”场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呆运对洪渎原唐墓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包括墓地布局、墓主身份、墓葬等级及文化特性几个方面。北京大学沈睿文教授从帝陵择址、陵地布列原则、随葬品禁断及墓葬壁画布局等方面的变化入手,就开元年间唐玄宗对丧葬制度的整顿与重塑展开讨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以“匠心”“匠气”“匠情”三部分,分析了中古时期墓葬壁画中的胡人图像,从而探索当时下层胡人的生活面貌,展示了胡汉互融后的社会图景。西北大学张建林教授针对唐代石窟及墓葬壁画中出现的赭色凹线等起稿痕迹展开研究,探讨了起稿技法的发展路径,并提及在中亚和日本等地发现的相似情况,涉及文化和技术传播问题。
本次研讨会的全部发言均得到各场评议专家的精彩点评。艺术史与历史学、考古学、科技史等学科间的对话,展示了多元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进一步促进了各学科在材料、观念、方法上的不断融合和碰撞,对开拓中古中国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教授主持。贺西林教授就大会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总结,并对全体与会学者、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最后,黄小峰教授和李军教授致闭幕辞,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成果和学术意义,并对会议的圆满完成表示祝贺。至此,中古中国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撰文:袁欣 纪东歌
相关链接:
中古中国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美 术 遗 产
专业学术资讯
优质阅读体验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美术遗产):会议资讯丨中古中国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