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Janus-faced Genius of Cities
源自:Urban Studies, 2021,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11007718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当前城市研究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发展主义论(developmentalist view),认为城市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从雅各布斯的“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到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城市作为创新机器”,再到格莱泽的“城市具备创造协作性才华的能力”等,众多经典论述都指向城市与发展的正向联系。正如斯托尔珀在其著作《城市发展的逻辑》(Keys to the City)中指出的:城市具有一种来源于集聚效应的特殊禀赋,表现在城市提供了一个汇聚不同知识技能元素的行为环境,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本文作者首先肯定了斯托尔珀的城市禀赋(genius of cities)理论,并在集聚效应的基础上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讨论维度:城际网络的外部性和城市建成环境的支撑作用。同时,作为对目前城市理论化中“一边倒”的乐观论调的回应,作者提出城市禀赋具有两面性的(Janus-faced)特征——城市既是“好”创新的源头,也孕育了翻新的剥削手法,即所谓的“坏”创新。由于城市本身的特性,城市是不公平发展形成的关键场所。有关城市角色阴暗面的论述并非无源之水,作者尤其参考了下列重要理论:霍塞利茨的“寄生城市”(parasitic cities)理论,冈萨雷斯的“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弗里德曼的“极化发展”(polarized development)理论,利普顿的“城市偏见”(urban bias)理论和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崛起和作为侵略性世界的城市”(the rise of capitalism and cities as aggressive worlds)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了头部城市的上层精英如何像真空泵(suction pump)一样,源源不断地抽取全球或地区边缘地带和农村地区的资源,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精英阶层,而且使得城市整体人群受益。其结果是城市不仅汇集了知识和财富,也聚合了剥削手段,导致国家和区域范围内的持续性贫困和极化。本文的论点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论据复合了诸多理论,论述过程层层推进,结论具有启发价值,特此推荐给读者。
加纳门禁社区与土地管理面临的挑战——重新评估人们搬入门禁社区的原因
Gated Communities and Land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in Ghana: Reappraising the Reasons Why People Move into Gated Communities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1, 36(3): 307-335
作者:Richmond Juvenile Ehwi, Nicky Morrison, Peter Tyler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自1980年代以来,门禁社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涌现,但有关居民迁入门禁社区原因的学术探讨仍然很少。一些学者倾向于选择使用源自发达国家实践的基于需求的主流观点,探究该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但这些研究对土地管理挑战等当地语境因素的重视不够。此文以加纳大阿克拉都市区为例,通过家庭调查和对关键人物的访谈,分析了加纳土地管理面临的挑战,并论证了这些挑战如何影响人们搬入门禁社区。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与居住在半城市化地区的家庭相比,居住在市中心门禁社区家庭的迁居决策受土地管理挑战的影响显著;而在半城市化地区,基于需求的主流观点和土地管理的挑战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对家庭和专家的访谈亦能佐证上述观点。该研究不仅重新评估了居民迁入门禁社区的原因,还提出了土地管理挑战对家庭迁居决策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门禁社区的区位特征,具体反映在社区的安全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传统土地所有者的行为。研究发现,门禁社区已成为加纳富裕家庭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家庭规避土地管理、土地使用规划和城市治理相关问题的途径。该成果对探究国内日渐增多的门禁社区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参考价值。
我们异乎寻常地在规划中的仁善问题上保持沉默——化解脆弱与痛苦时面对的挑战
Our Curious Silence About Kindness in Planning: Challenges of Addressing Vulnerability and Suffering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21, 20(1): 63-83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
本文是国际知名规划理论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福里斯特教授的最新学术观点,他曾于1980年代末率先研究沟通规划,并成为这一规划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从细微规划实践中挖掘可实践的规划概念和理论。他发现,公平或正义问题在规划研究界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但是“仁善”却不常被提及。其实,仁善不仅是同情别人的脆弱、失落和痛苦,还应包括采取相应行动来减缓这些负面感受。以这一界定为基础,作者通过“同情”这一对他人痛苦情绪的移情,分析了仁善需要的四种务实的判断标准。第一,对他人的脆弱和痛苦的感同身受;第二,从因果关系或精神上对脆弱和痛苦的来源进行测定;第三,采取行动减轻痛苦(与“我能做什么”这一问题相关联);第四,建立采取这些行动的长效动力机制(与“我是谁”这一规划师本体论问题相关联)。当然作者也指出,由于背景各异,善意也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此种行动容易出错,但也容易纠正和提高。
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立场与看法,福里斯特教授还举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例子。在美国克利夫兰,某高速公路修建计划将导致几百位内城居民被迫迁离家园;在加拿大育空地区,城市开发威胁着原住民的引水安全;在澳大利亚英格拜湿地保护区,社区规划师对当地居民担心其公共空间被占用作了疏导工作。他通过记述相关规划师的言行与看法,展现了在面对这些受影响者的脆弱、痛苦的感受时,规划师如何进行带有善意的有效规划应对。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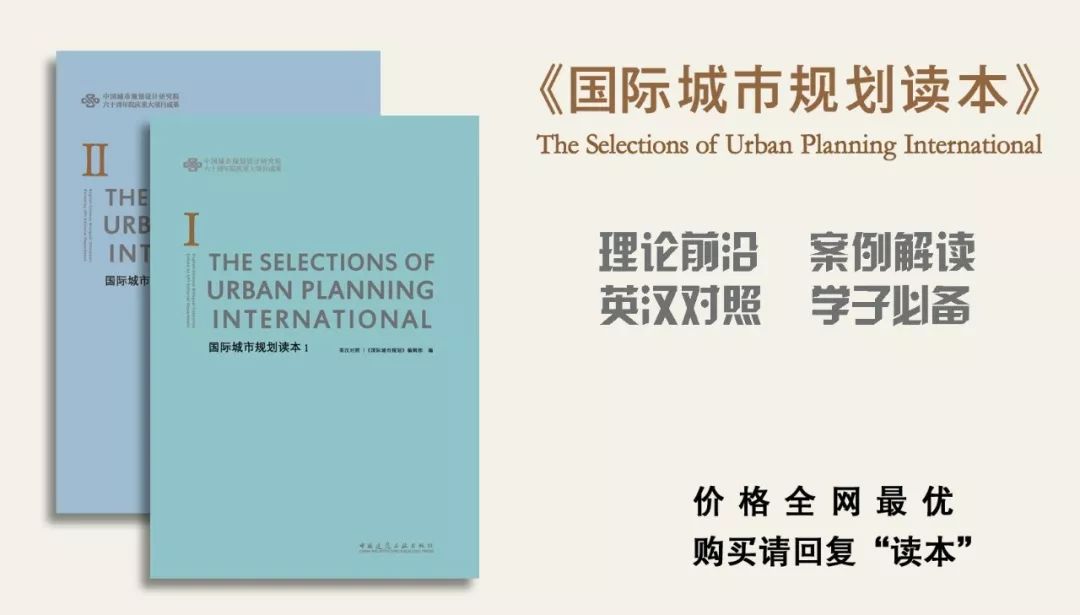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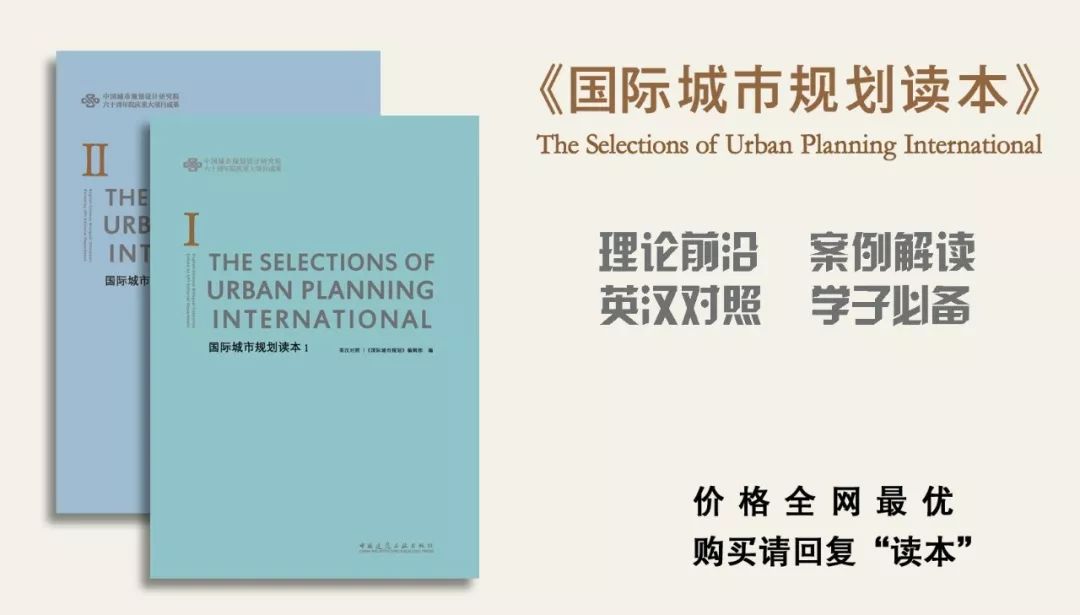
 第十一章《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十一章《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大数据应用》|《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二期讲座课《技术发展与未来城市》 |《新城市科学》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二期讲座课《技术发展与未来城市》 |《新城市科学》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AI 大模型高级研修班》重磅来袭!涵盖八大主题,六大项目实战,四大行业应用丨城市数据派
《AI 大模型高级研修班》重磅来袭!涵盖八大主题,六大项目实战,四大行业应用丨城市数据派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加快赋能应用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加快赋能应用 第十章《基于多元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十章《基于多元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