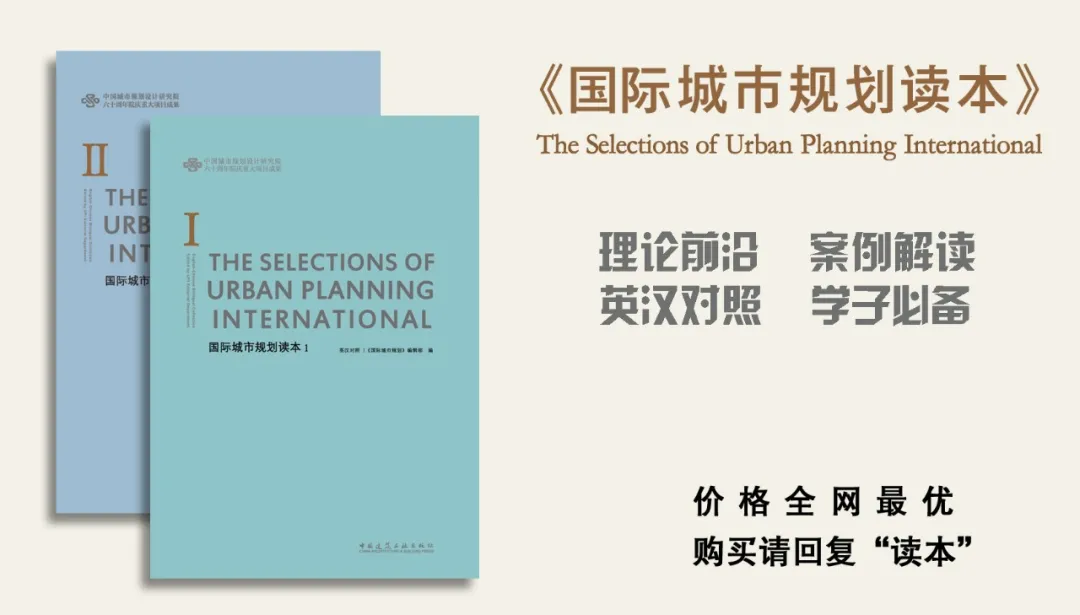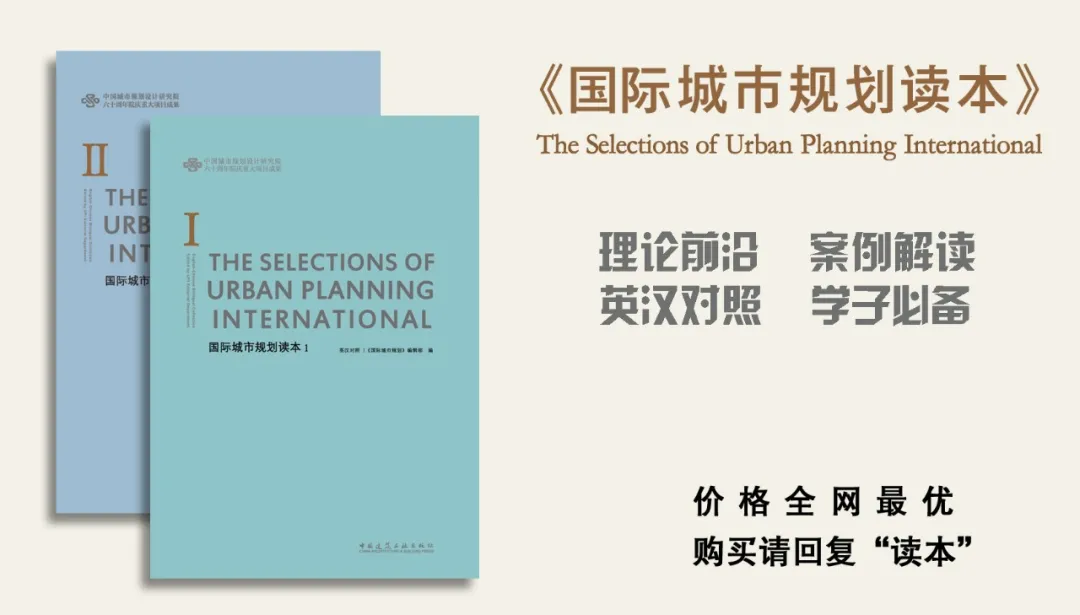【编者按】 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虚实互动、双重集聚与流乡村的类型》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城乡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高,虚实空间互动日益高频。广大的乡村地区借由移动互联网进入更广阔的产业分工体系,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在虚实空间中高速流动,乡村发展已经呈现新的现象与模式。
众多新乡村的持续涌现,表现出流空间(space of flows)在中国的规模、强度和呈现形式的巨大扩展。这一扩展极大地促进了城乡间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使得城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由连接的网络。乡村地区可以自由融入区域范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也因此获得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随着新乡村的蓬勃发展,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迅速展开,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方式、目的和程度存在差别,因此形成的结果和绩效不尽相同。相比欧美受制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的智慧乡村行动,中国深入而广泛的新乡村实践更具生命力和价值。换言之,以西方为唯一参考和理论来源的研究很难深入中国实践,也很难形成对中国乡村发展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
针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新乡村实践,笔者建构了“流乡村”(village in flows)这一概念,旨在整合我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新乡村现象,跳出一般经验描述,形成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抽象和学术表达。基于虚实空间互动与双重集聚的分析框架,流乡村被结构化地定义为“实体分散、虚拟集聚的聚落空间”,它们虽然保持着乡村的风貌,但已经进入区域甚至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从经验中抽象出的概念能否真正成立,需要回到经验中去检验——检验它能否很好地解释当前不断涌现的新乡村现象,同时清晰地区分众多现象之间的差异——分类于是成为问题的关键。
分类通常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通过对大量流乡村的观察,笔者发现它们在形成机制和发展路径上并不完全相同,而核心差异恰恰就在于虚拟集聚与实体分散两大核心特征的差别。一方面,在虚拟集聚的程度上,根据流乡村与外部空间生产性联系的强弱可以明显发现存在“强虚拟集聚”和“弱虚拟集聚”两种类型。具有“强虚拟集聚”的流乡村,通常与外部空间发生着持续、高密度的信息交换,同时较为充分地融入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相对而言,“弱虚拟集聚”的流乡村与外部空间的生产性联系相对低频、低密度。另一方面,虽然流乡村在实体空间层面都呈现出分散的特征,但依然存在不少流乡村的实体空间随着虚拟集聚的持续强化有进一步“导向实体集聚”的倾向,尤其从事加工制造的流乡村,持续的虚拟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必然引致更大规模的实体集聚,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与这类流乡村相对的就是始终“维持实体分散”的类型,即本身不从事或很少从事加工制造,产业发展也不需要或不会引致高密度建成空间,虚拟集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不会导致建成空间的扩大、加密,实体空间发展品质不断提升,但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相对分散的状态。
由于“导向实体集聚”的前提是有足够强度的虚拟集聚,因此理论上不存在“弱虚拟集聚”并“导向实体集聚”的流乡村。结合对真实世界的观察,最终笔者将流乡村划分为三种典型类型:(1)流乡村Ⅰ型:强虚拟集聚,导向实体集聚;(2)流乡村Ⅱ型:强虚拟集聚,维持实体分散;(3)流乡村Ⅲ型:弱虚拟集聚,维持实体分散。UPI
对本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于中国知网检索本文的录用首发版本。
作者: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委员。zhendongl@sina.com
汤剑虹,浙江城市空间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助理工程师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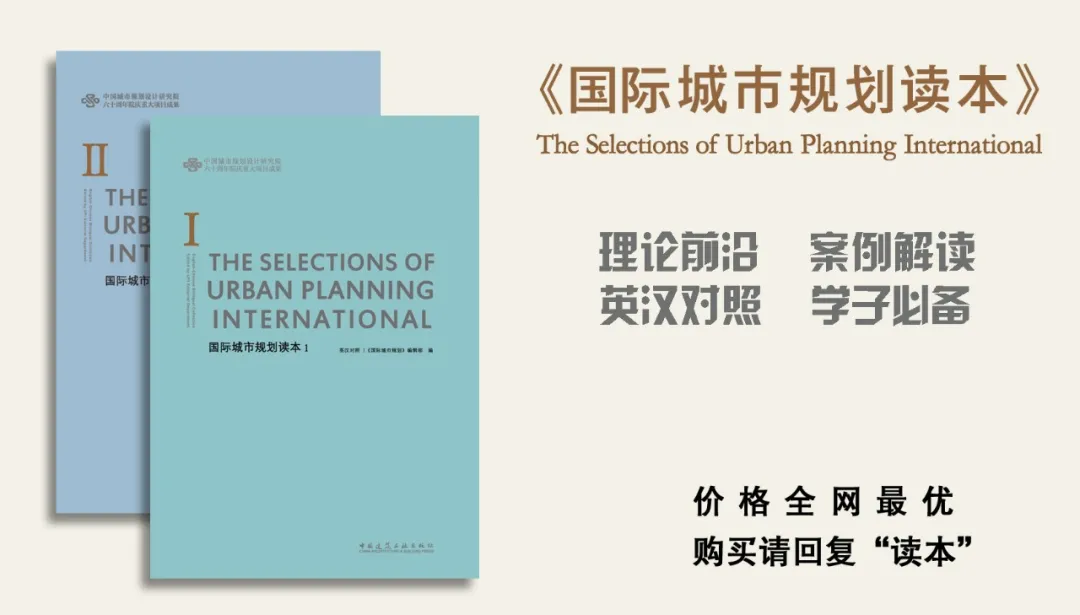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虚实互动、双重集聚与流乡村的类型【抢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