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者按】当地时间7月26日傍晚,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主办城市巴黎开幕,为时4个小时的巴黎奥运开幕式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热点。从空中、到河流,从屋顶、到地面,运动员们乘船入场;艺术家们各显其能,有票和无票的观众都尽情享受;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幻,文艺与体育,将整座城市幻化为一场宏大绚丽的节日庆典。笔者不禁想起20年前发表在《国际城市规划》上的一篇译作——《巴黎是一场节日庆典》,文章以城市规划的视角,回顾了巴黎作为节日庆典之城的历史演变,强调了节日庆典在巴黎的重要地位,以及城市规划为此所需承担的职责——公共空间回归行人,节日氛围回归街道,节日庆典回归城市。回想起来,这篇文章堪称本届巴黎奥运开幕庆典的完美预告和注释,因此建议编辑部在公众号分享,重温巴黎千百年来被节日庆典塑造的历程。
如果说农业是针对植物生活的专用名词,那么城市规划则是针对人类生活的专用名词。一片良田可以令植物茁壮成长,植物长期产生的腐殖成分又可以使土地更加肥沃;同样,一个良好的城市规划可以令人类生活在适宜的环境里和谐发展,文化活动作为人类生活的表达又可以使城市环境和城市规划更加丰富。文化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铭刻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里:它通过人类生活得以表达,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类生活。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vebvre)认为,不应该把城市的媒介作用与其“内涵和外延”分割开来;城市像一本书,映射出人类社会和人类意识的形式与结构。然而,城市不是人类社会的简单映像,要了解城市及其独特的结构作用,就必须将其置于各种社会关联中进行重构:正是这些社会关联在城市中留下了人类社会的印记,构筑了人类社会的格局。蒂埃里·帕格(Thierry Paquot)曾提出要“让城市长久生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要像演员一样进行“表演”,而是要像演员表演一样,在自己的生活地点扮演自己的角色。良好的城市规划应该通过恰当的引导、规定和公共计划,为发挥个体主动性创造条件,而不是抑制个体主动性的发展,它的优秀品质只有在规划实施以后才能体现。伴随生活的发展,城市规划不断孕育成长,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其最突出的外在表现就是节日庆典。
何为庆典?庆典是一种社会和集体活动,是人们为了共同欢庆某一事件而聚集在一起;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活动,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乏味,使人为之一震。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需要进食、睡眠、繁衍后代,需要筑巢造窝以躲风雨、避寒暑:然而能歌善舞、弹奏乐器、刻画人物、描绘风景,共同分享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创造之趣、欣赏之乐,却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各种文明,即使是最朴素的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庆典:显然,这绝非偶然。庆典活动为社会性与创造性的交融创造了机会,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表达和创造社会文化的场所,成为城市中培养个性和发挥天赋的场所。在节日庆典的发展进程中,建筑和城市规划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们不仅融艺术和技术于一体,同时也是建设在庆典活动中被关注和被使用的城市空间的主要途径。
在巴黎,节日庆典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要素,包括场地、环境等等,都已成为巴黎城市魅力的重要内涵:它们铭刻在巴黎的城市历史和城市空间当中,并因此而深刻、生动、风趣和丰富。数千年来,巴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本质,同时又不断融入现代生活的快捷特点:这种“本质”在城市空间中不断渗透,从未停息。巴黎的节日庆典是一部可以触摸的厚重历史,是一个可以度量的地理空间,是由无数细枝末节构筑而成的整体,其中的每个细节、每寸土地似乎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公元前53年,罗马皇帝恺撒征服高卢;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衰落,高卢一直被罗马人占领,史称高卢—罗马时期。当时,巴黎的前身吕岱斯城与其他罗马城池一样,分别建有一座剧院和一座圆形剧场,供公共演出之用。这种对戏剧演出及其场地和形式的重视态度,成为巴黎文化甚至欧洲文化经久不衰的特征;今天,在巴黎依然可以看到这些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例如巴黎拉丁区的圆形竞技场】。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黎一直陷于黑暗和混乱,战争、掠夺和贫困持续不断【历史上欧洲曾不断遭受大规模外来入侵,在法国主要集中在4—10世纪】。
自10世纪起,巴黎进入一个和平时期,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应运而生,在11—14世纪得到长足发展。随着罗马人带入的基督教在巴黎广为传播,宗教建筑大量出现,改变了城市景观;以宗教建筑为核心,新的城市景观逐步形成。一座座教堂,特别是高高耸起的教堂钟塔,使得城市景色以及城市生活充满了韵律,它们像一本本石刻的画卷、一曲曲凝固的交响乐,材料与光线交相呼应,向人们传达着不可言表的心灵震撼;至于那些可以言表的内容,则在教堂内外,特别是盛大宗教庆典活动中,通过人们的歌声传颂着。在城市街道、教堂广场以及达官贵人的宏伟府邸各种形式的戏剧和音乐演出无处不在。
进入16世纪,非宗教性质的戏剧和剧场开始出现【在法语里,作为某种表演形式的“戏剧”以及作为表演场所的“剧场”,使用的是同一个词汇。但是剧场里的演出并不局限于戏剧一种形式,还包括芭蕾、音乐会等其他形式的演出。另外,法国人还用“戏剧表演”“戏剧片段”等用语特指表演形式,用“戏剧大厅”“剧场”等用语特指用于表演的场所。但在最初,所谓“戏剧”主要指舞台演出,所谓“剧场”主要指中等规模的演出大厅】。巴黎的某些地点逐渐成为相关演出的特定场所,例如勃艮第公馆和博韦学院;某些剧团甚至在某个公馆长期驻扎下来。17世纪,在巴黎的网球宫、卢浮宫甚至王宫,都有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1778—1786年间,巴黎先后建起了三座剧院,即奥德翁剧院(现法兰西剧院)、王宫剧院(现法兰西喜剧院)和圣马丁门剧院。
伴随戏剧演出的发展,其他娱乐活动场所也蓬勃发展起来若干花园先后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1640年开放的王室药用植物园以及1666年开放的杜伊勒利宫花园。巴黎的第一座“观景”桥——塞纳河上的“新桥”竣工以后,成为人们欣赏塞纳河两岸美景的场所,并因此吸引了众多游人;桥上不仅有卖甜食的,还常常有街头卖艺和表演木偶的。一年一度的圣日尔曼年会更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1671年巴黎人在这里发现了咖啡,1675年巴黎最古老的两家咖啡馆宣布开张;此后,咖啡馆很快成为一种时尚,到1715年巴黎的咖啡馆已经达到300家。
在18世纪以前,法国王室和达官显贵的庆典活动场面奢华,大多在国王和亲王的城堡和花园举行:卢浮宫、凡尔赛宫以及为数众多的贵族府邸都是举办舞会、宴会、音乐会和戏剧演出的最佳场所,其盛况在画家和作家的笔下都有生动描绘。这些庆典活动大大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艺术传世之作,使我们有幸在今天仍能一睹昔日盛况。尽管当时,公共的音乐和戏剧表演开始有所发展,但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总体上讲,庆典活动是王室精英和富裕阶层的专利,普通百姓无缘享受。
18世纪以后,在巴黎城墙以外的主要大街两侧,相继出现了剧院以及上演芭蕾舞、木偶戏、模仿秀等其他娱乐活动的场所,自1725年起,杜伊勒利宫开始举行公共音乐会;每年都有很多青年画家把自己的作品拿到西岱岛上的王妃广场展览。普通大众更是对各种惊人壮举充满热情,例如乘热汽球旅行。1783年,首批乘热气球旅行者分别从战神公园和猎舍公园升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舞台演出,特别是戏剧演出成为宣传政治主张的一种方式,巴黎人喜爱的宏大场面被搬上舞台。
除上述庆典活动以外,巴黎还出现了各种与特殊事件相关的庆典活动。例如从14和15世纪开始,每次国王隆重返京之时,便是巴黎人大大庆祝之日。路易十四以及后来的拿破仑一世在各自执政时期,都搞过场面宏大的返京庆祝活动。再如,每逢国王加冕、迎接重要人物来访,以及后来新共和国成立、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足球队获胜……等等,巴黎都会举办庆祝活动。
19世纪以后,庆典活动逐渐成为赋予城市生存活力的新方法。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的庆典演出活动更趋普及,场所不再局限于贵族府邸或者教堂广场,时间也不再局限于寥寥无几的重大事件。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重新打造了这座城市,整治城市街道,拆除大片旧房以及有碍交通,特别是行人通行的构筑物,使得巴黎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更加协调统一:最终,在巴黎旧城的土地上,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但是,巴黎的城市精髓没有因此而被摧毁。尽管部分街区被整体拆除【西岱岛上传统的中世纪街区被整体拆除,尤为令人惋惜】,但在新开辟的城市大道两侧或者之间,大量的传统街区被保留下来。“同类而居”成为当时城市人口的分布原则,在每个街区甚至每栋建筑内部,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现象【这一点与过去的描述恰恰相反】。新开辟的城市大道一般宽30米,两侧种有高大的行道树,留有宽敞的人行道:道路两侧的建设遵循严格的建筑规定,沿街立面整齐划一。这些道路渐渐成为人们休闲漫步的场所,其中一些甚至是为了某项活动而专门修建的。例如,在歌剧院大街的尽端,坐落着以建筑师的名字命名的加尼埃歌剧院;当时,整条道路的修建,从道路布局到沿路装饰,都是为了配合歌剧院的建设而进行的。由此可见,在当时,巴黎的庆典活动已不再局限在演出大厅里,也同样发生在城市街道上。
城市中的自然空间同样是节日庆典不可或缺的要素。就像国王有自己的狩猎场一样,巴黎人也拥有自己的娱乐场所。位于巴黎西部的布洛涅森林和东部的万森森林曾经是法国王室的狩猎场,此时被重新规划整治,成为巴黎人休闲漫步之地。相比之下,这里的庆典活动被赋予浓厚的家庭韵味;或是水上泛舟,或是草地野餐,都很快成为巴黎人喜爱的家庭休闲活动。同时,巴黎人还在这两个新建的森林公园里修建了昂贵的娱乐场所——赛马场,一方面炫耀高大的坐骑,一方面展示优雅的骑师。除此以外,新建的两座城市公园,即南部的蒙苏里公园和北部的肖蒙山公园,亦成为巴黎人喜爱的休闲去处。
于是,新建的道路、广场、花园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使得巴黎的城市面貌日趋统一而又不失变化:作为城市中的美丽装饰,它们逐渐成为巴黎的一道亮丽景致,使得巴黎人在自己心仪之余,也乐于向来客展示。不断增多的各类店铺透过琳琅满目的橱窗店面,为城市的街道景致增光添彩:衣衫绚丽的淑女贵妇前来观赏购物,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在炫目的橱窗前后,在宽敞的人行道上,在宜人的绿荫丛中,节日的景致无处不在。路人在注视着城市,城市也在注视着路人;你在人群中欣赏风景,同时也成为他人的观景对象。
这种变化在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之后得到更加圆满的体现。工业发展孕育了建筑革命。1885年,为了提高法兰西帝国的威望,展示法国工业的进步,经拿破仑三世拍板决定,巴黎第一次承办了世界博览会【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世博会不仅展示了在奥斯曼的巴黎治理工程中所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施工机械,并且通过展馆建设充分展示了此类技术进步及其在大型建筑结构中的可能利用。有趣的是,无论在建筑空间还是建筑语汇上,展馆设计都沿袭了巴西利卡和天主教堂的布局形态。其中,工业馆是第一座采用铸铁结构的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央高起的大厅部分跨度达48米,周围环绕着由两排柱廊形成的展厅;机械馆长120米,沿塞纳河而建,采用了窄筒拱顶结构。
1867年,巴黎第二次承办世界博览会,场地选址在战神公园。从5月6日开幕到11月6日闭幕,此次世博会共接待了2500万参观者,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展品,机器、材料、原材料、服装、家具、实用艺术、工艺美术……不一而足。世博会的椭圆形主体建筑由7个向心布局的展厅组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器展厅;它的金属框架高25米,支撑在高19米的铁柱之上,柱子之间是呈农家妇女裙环状的圆拱。
相比之下,更为轰动的是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机械馆,它长420米,跨度达115米。同样是在这届世博会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作为世博会的中心,这座铁塔高300米重7300吨,有1600个台阶,建成之初曾受到众多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的严厉批评,但最终岿然不动,成为巴黎的重要地标。这也是最后一次,人们因为埃菲尔铁塔而对工业发展充满赞美之意。
此后,节日庆典的氛围再次悄然潜入街道。1900年4月14日开幕的世界博览会把巴黎变成了一座梦幻之城。此次世博会选址在托卡德罗、香榭丽舍、协和广场和荣军院之间的区域,占地110公顷,世界各国的展馆在塞纳河两岸一字排开;乘坐色彩绚丽、充满异国情调的各式小艇在水上漫步,不仅可以观看各国展馆,同时还可欣赏坐落在河流两岸的建筑历史遗产。电力照明使得城市大街小巷灯火通明,埃菲尔铁塔亦在灯光中岿然挺立。当年,巴黎地铁刚刚建成通车,被埃克托尔·吉马尔(Hector Guimard)的铁饰艺术装饰一新,因此乘坐地铁观光可谓别有一番情趣。登上苏弗兰大街高过百米的巨大转盘,极目远眺,首都巴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远处,大小宫的圆顶一目了然,南侧是为了迎接俄国沙皇来访而新建的亚里山大三世桥,在大桥两端四个高17米的桥头堡上,安放着四座金光闪闪、巍峨壮观的雕塑。得益于问世不久的电力照明,整个世博会都沉浸在几乎神奇的灯光之中;这不仅使巴黎充满动感,也使得庆典活动更为丰富,从吕米埃兄弟的电影(1895年)到汽车、电话、电报……,应有尽有。这届世博会共接待了5000万名参观者: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为这场庆典添色不少。同时,这届世博会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节日;同年9月22日,22000名市长簇拥着总统爱米尔·鲁伯(Emile Loubet),齐聚杜伊勒利花园,参加共和国国宴,举杯共祝共和国繁荣昌盛。
巴黎的基调:文化之都、精美之都、文雅之都、时尚之都
从19世纪末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经历了被称为“美好年代”的稳定发展,成为全世界的文化中心:有关诗歌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的新观点、新品味、新时尚在此汇聚、在此萌发、在此展示,将巴黎变成一个国际大论坛。各类庆典活动也增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舞会上、在沙龙中,人们谈论着文学、哲学和政治。以前,蒙马特高地因其独特的乡村景致而倍受艺术家喜爱,在1910年以后,它迅速成为众多画家和作家时常光顾之地。
以Rotonde和Dôme为代表的咖啡厅成为人们的约会场所。大街小巷、公园绿地、塞纳河畔、大桥之上,巴黎人构成了巴黎,展示着巴黎的风情。实际上,许多巴黎人并非出生在巴黎,他们却以巴黎人自居,最终蜕变成真正的巴黎人:像普鲁斯特(Proust)、博纳德(Bonnard)、马提斯、德兰(Derain)、毕加索、于特里约(Utrillo)、莫迪格里阿尼(Modigliani)、夏加尔(Chagall)、康定斯基(Kandinsky)、罗丹、纪尧姆·阿波利耐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等名人,都以身为巴黎人而自豪。从早期的蒙马特高地,到日后的蒙巴拿斯街区,来自欧洲、美国的艺术家不断汇集;在他们的研究和碰撞中,艺术发展的新趋势逐渐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艺术展览的品质也在不断提高。1667年,第一届王家学院绘画雕塑展在王宫举行。1751年以后,巴黎美术学院沙龙【在此,“沙龙”一词专指汇集了某个领域的新作品和新创作的展览,例如绘画展、汽车展、园艺展等】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都获得巨大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和对艺术充满好奇的人:1863年,巴黎举办了一次“落选作品沙龙”,展出了曾被巴黎美术学院沙龙官方评委会拒之门外的4000多部作品,莫奈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就是其中之一。1874年,“印象派”画展成功举行。1880年,卡纳瓦莱博物馆(即巴黎历史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进入20世纪,巴黎的各类展览与日俱增,从高级时装、家庭和办公室内装饰、城市公用设施,到摄影、电影、古物收藏,无所不有,充分显示了艺术本身的巨大发展;1925年举办的装饰艺术展接待了约1600万参观者。
19世纪,巴黎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表演”和“展示”场所,即大型商场。1829年以来,巴黎先后有三个大型商场陆续开业,即1852年的便宜居商场、1856年的市政厅商场(最早被称为拿破仑商场)和1870年的撒马利亚商场。在这里,所有商品都明码标价,整齐地摆放在多层货架上;顾客可以自由出入商场,也可以在货架之间自由穿梭,浏览,完全不必担心有售货员如影相随、推销商品。所有这一切赋予这些大型商场独特的“巴黎气息”,使得逛商场像过节一样自由轻松。在巴黎,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些自由深入到巴黎的风气之中,成为巴黎节日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舞台、到演出大厅、再到城市,公众相互观望,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渐渐地,庆典活动和节日氛围在城市中无处不在,形式多样,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可以投身其中:与此同时,传统的室内演出也没有被人遗忘。17世纪,剧院名符其实地成为巴黎的娱乐场所,人们亲临剧院“既是为了看戏,也是为了演戏”,从而把剧院变成了表现自我的社会场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加尼埃歌剧院,包厢的设计既朝向舞台,又面向观众,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观众的地位日趋重要,可能成为观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随着观众人数的增加,演出厅的面积不断扩大,新的剧院建设层出不穷。建于1860—1862年的夏特莱剧院可容纳3600位观众,对面的夏特莱音乐厅有1500个座位;1913年建成的香榭丽舍剧院更是在建筑构造(使用混凝土)、设计理念(剧院由三个演出大厅组成)和区位布局(位于传统的戏剧演出街区之外)等三个方面富有创新。
1977年,被称为“美丽乡镇”的蓬皮杜中心对公众开放。这是一个囊括现代艺术博物馆、图书馆、音像馆等在内的多功能文化中心,是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要求下,为了广吸引民众参与文化生活而修建的。在最初设计时,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被要求设计一座“平易近人”的建筑,以吸引那些不会自觉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人;同样是为了吸引民众,蓬皮杜中心一直营业至晚间22点。从民众的使用情况看,蓬皮杜中心是非常成功的;自落成至今,这里每天接待近2万名参观者(与卢浮宫的接待水平大体相当)。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蓬皮杜中心的室外广场及其周边环境富有浓郁的节日氛围,由于整个广场呈台地状由高而低向建筑物倾斜,建筑本身成为广场的陪衬,特别是建筑立面上逐级抬高的室外金属楼梯。在这里,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人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1980年代,“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宏伟工程”同样是对民众文化庆典活动的重要引导。例如,巴士底歌剧院被设计为流行歌剧的演出场所;拉维莱特公园以及其中的工业与科学城、拥有6300个座位的“顶点”演出大厅、大市场、音乐城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整套的文化娱乐设施,为庆典融入文化、民众参与庆典创造了条件。其中某些工程通过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城市,或者通过将城市引入建筑室内,把庆典活动的节日氛围再次引入城市。针对前者,拉德方斯的大拱门即是最佳例证;在无论是建筑物上的窗户,还是建筑室外的台阶、电梯,都面向巨大的步行平台,通过隐喻或现实的手法,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城市。针对后者,奥赛美术馆(1986)可为例证:建筑师利用原火车站台,在建筑室内创造出街道、广场等城市空间,两侧则布置传统式的展室。
体育活动的发展同样可以说明观众人数增加、类型增多、庆典活动形式多样以及观众直接参与表演等趋势。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巴黎,体育竞赛为人数众多、积极参与的观众带来一次欢庆的机会。1894年,巴黎举办了第一届法国足球锦标赛。1998年1月28日,法兰西体育场见证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这个体育场位于巴黎以北,是为举办世界杯足球赛而专门修建的,可同时容纳8万观众观看比赛,或者10万观众观看文艺演出。除此之外,巴黎还有其他许多体育活动场所,包括可容纳5万观众的王子公园体育场,既可举办体育活动(拳击、足球、自行车等),又可进行文艺演出(歌剧、古典或现代音乐会等),可容纳3500~17000名观众的贝尔西体育馆。在现在的体育比赛中,观众成为场景的重要组成要素,他们在欣赏比赛的同时,将整个活动演变成一场大型的群众庆祝活动:这在足球比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比赛过程中,现场的气氛与比赛本身同等重要;由于观众坐席是相向布局的,因此对面的观众似乎也在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竞赛。这样的活动赋予巴黎一种独特的力量,这不仅因为巴黎民众拥有独特的个性,也因为大型比赛往往吸引了来自法国各地的观众。比赛之时,嘈杂之声充斥着巴黎的大街小巷:即使是端坐在电视机前的巴黎人,也有着同样的热情。
从战争到和平,从沉默、觉醒到战斗、解放,面对外来侵略与内部限制,巴黎始终在为自由而欢庆
在巴黎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刻,特别是与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吻合时,庆典活动的作用至为重要。1848年11月19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颁布新宪法;为了欢庆这一伟大时刻,巴黎人涌向街头,到星形广场观看烟火。事实上,每当有事件发生时,巴黎民众的反应都会像漩涡一样席卷整个法国。面对外来的或者内在的压迫,正是他们首先吹响反抗的号角。1914—1918年间,巴黎陷入战乱,不断遭到轰炸。这个时期,巴黎实施定量配给制度,甚至有部分居民因惧怕战乱而逃离巴黎;到了冬天,条件变得更为严酷,食物匮乏、流行病肆虐。终于,在经过1561天的战争以后,交战各方于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定。11月17日巴黎人齐集香榭丽舍大街,庆祝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回归【这两个地区属于法国领土,但在1871年曾被划归德国】。1919年7月14日法国国庆,300万人观看了法国和盟国士兵的阅兵式,欢庆法国的胜利。
1919—1939年,因战争而被搁置的艺术创作、技术创新和构想在巴黎迅速发展起来,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各类演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这其中不乏因钟情于巴黎的街道和堤岸而积极参与的外国人的贡献。针对这个时期的巴黎,海明威曾写道,“巴黎本身就是一场庆典”;莫里斯则写道,“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期就像是永无止境的7月14日”。戏剧、电影、音乐领域的新作层出不穷;咖啡馆的露天平台再次成为诗人、画家、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热烈讨论的场所,人们在这里讨论、聆听、观察和被观察,兴奋地沉浸在巴黎的沸腾生活之中。
对巴黎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另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在1940—1944年被占期间,巴黎遭受了羞辱和分割;入侵者无处不在,而巴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传到巴黎。就在盟军部队向巴黎挺进的同时,巴黎的抵抗组织发起了罢工运动,使铁路、邮政和警察陷于瘫痪。8月19日巴黎人发动起义,占领了公共建筑,设置了路障。8月24日,当勒克莱尔(Leclerc)率领的部队进入巴黎时,巴黎人已经部分解放了自己的城市。8月25日,德国人宣布投降,同一天,戴高乐将军返回巴黎,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得到,在某些时刻,痛苦的生活已成为过去……”第二天,当他抵达凯旋门时,巴黎已是一片欢腾。
庆典与历史相联,历史强化了记忆。人们对某座城市及其民众的共同记忆深深地铭刻在城市的每块石头上,每个街名中以及城市的传统和节庆之中。
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成为民众走上街头共同欢庆的日子。在巴黎,除了观看香榭丽舍大街的阅兵式,还可以欣赏烟火,参加在不同街区举行的群众舞会。有些活动则更为壮观。例如,1980年7月14日,200万人在拉德方斯参加了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演唱会;19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香丽舍大街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罗马时期,庆典和演出活动常常发生在达官贵人的私人宅邸、剧院或者圆形剧场。中世纪时期,艺术和演出活动展现的是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从16世纪开始,非宗教题材的艺术和演出活动迅速发展,逐步建立起自己特定的演出场所。所有这些庆典和演出的场景都在历史中延续下来,在今天的巴黎和谐共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黎的教堂日渐增多,而教堂里的宗教活动却不断变化:尽管今天的宗教活动通常比以往更加虔诚,但它不再像过去那样规律和普遍,越来越丧失社会性而蜕变成个人的行为。与此同时,教堂却激发了全新的、高质量的艺术和庆典创作。一方面,宗教活动的形式趋于多样化:宗教聚会和庆典不仅发生在教堂里,也发生在普通的世俗场所,例如演出厅、会议厅、体育场或者展览厅。另一方面,教堂的使用功能趋于多样化:人们不仅可以在教堂参加宗教活动,还可以聆听音乐会、观看戏剧演出、参与其他活动。
巴黎保留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同时又不断创造新的空间场所。建于18世纪的奥德翁剧院、王宫剧院和圣马丁门剧院至今仍在,并且仍在作为剧院使用,定期上演古典或现代剧目,由于历史悠久,它们在巴黎享有很高声望。在过去若干世纪里,巴黎的演出场所不断增多并呈多样化发展,众多演出大厅既可容纳数量巨大的观众,又可接纳各种形式的演出,最近一个世纪,某些场地还逐步发展成为专门上演优秀剧目的场所(例如贝尔西和巴士底歌剧院专门用于歌剧演出)。与此相应,巴黎的庆典和演出场景在形式上亦有所改变。例如,19世纪以后,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歌剧,而轻歌剧作为歌剧的姊妹,在同一场演出里融合了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等不同演出形式,其中的歌曲和音乐喜剧较传统歌剧能够为更多的民众所接受,因此轻歌剧及其特定的演出场所(夏特莱剧院,或称戏剧歌剧院)很快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就像此后出现的歌曲一样,它们在城市的街工地和其他普通场所被各种各样的人群广为传唱,十分盛行。新技术的发展促成了上述变化的出现,上述变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相关技术研究和工艺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以城市为背景,在规模宏大的场景里进行演出。利用光学和声学技术,这些宏伟的“声音和光线”将整座城市变成一个神奇的舞台,对此可以巴黎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为例。
在巴黎,歌曲的地位不可替代。从街道到咖啡馆,从小酒馆到音乐厅,埃迪特·皮亚夫(Edith Piaf)、莱奥·费雷(Léo Ferré)等歌唱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扩大歌唱艺术的观众面,确立歌唱表演的特定场所。在今天的巴黎,人们依然喜欢在饮酒之时聆听一首歌曲:年轻人则喜欢在数不胜数的所谓“夜总会”里,伴随着钟情的乐曲翩然起舞。尽管这些场所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英美音乐,但在周五或周六结伴前往小酌一杯,依然是巴黎人非常独特的习惯。
各种新型演出场所(电影、歌唱、体育……)的出现加之音响技术(麦克和声音放大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对相关建筑的规划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巴黎民众的行为特点却保持了长久的延续性,即直接参与演出,成为场景的组成要素。他们在场景中回应、抨击、喝倒彩,或是赞同、或是反对,直至最终主司整个空间:他们不是被排除在场景之外,而是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巴黎的景致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更是一场节日庆典。
此外,那些最初被精英阶层所独享的活动也趋于大众化;通过参观大规模的世界博览会,广大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大型展览的鉴赏力。在20世纪,巴黎的各种展览获得长足发展,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成为真正的大众节庆;在巴黎的凡尔赛门地区,每年都会举办汽车、农业、图书、教育、家居艺术等不同内容的展览,其日程安排甚至已经形成了规律。其中某些展览非常独特,因此深得巴黎人的喜爱;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农业展上,每次都会展出来自法国不同地方的漂亮奶牛、各种动物和挑选出来的最好产品,包括猪肉、奶酪、葡萄酒……外省的民众也可以借机来到巴黎。
除上述庆典活动以外,长久以来,还有许多传统节日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既是家庭团聚的重要时刻,又是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的组成部分,为人们在一起自娱自乐、享受集体生活创造了条件。圣诞之际,人们总是为巴黎披上节日盛装,大街小巷灯光明亮、色彩斑:尤其在香丽舍大街上,金树银花更为壮观。众多商家挖空心思,店面橱窗竞相争艳,到处洋溢着孩提梦想的色彩;每到夜晚,大人小孩都会徜徉在大商场的橱窗前,观赏其中的自动木偶表演:各式各样的长毛玩具熊在为圣诞节忙碌着,有的在厨房里准备圣诞蛋糕,有的在装饰圣诞树,有的在布置桌子和烟囱;旁边,圣诞老人在往靴子里放着彩纸包裹的圣诞礼物,小鸭子在游戏玩耍,玩具娃娃们在讲述着童话故事。人们前往市政厅、巴黎圣母院和街区教堂,膜拜耶稣诞生的马槽。尽管如今的圣诞节日带有些许商业气息【圣诞节期间是重要的销售季节】,但节日气氛依然独特并且令人期盼。通常,圣诞的节日气氛从12月初即已开始,在度过了元旦和国王节,共同分享国王饼之后才算告一段落;这种节日氛围因为节日的短暂而独具韵味,并且不会在一年当中的其他时光里变得平淡。
最近以来,巴黎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节日庆典活动。例如1982年6月21日,巴黎举办了第一届音乐节,在此期间,巴黎的每个街区都举办了大大小小的音乐会,既有专业团体的演出,也有业余爱好者的演出。广场上、花园里、咖啡馆、教堂前,甚至人行道上,在可能的地方,都有音乐家和歌唱家在为巴黎人免费献艺。这次音乐节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巴黎都会举行同样的音乐活动。今年,巴黎又出现了另一个全新的节日庆典活动,即邻里聚餐节。在节日的当天晚上,同一栋楼里的居民带着食物在楼下的街道上聚集,与邻居们共进晚餐:凡是聚餐的地方,车辆都要绕行。
长期以来,巴黎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节日内涵的理解,节日庆典也成为巴黎生活艺术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篇文章的寥寥数语就认为,巴黎人的生活条件总是非常理想,文章中涉及到的事物发展没有碰到任何问题。事实上在20世纪,巴黎经历了一场“节日庆典的危机”,在本质上则是日常生活质量的危机。1970年代,随着机动车逐渐占据城市空间,巴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空气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建筑物外饰面质量下降,几乎无法忍受的噪音污染,严重的交通堵塞;所有这一切不仅降低了居民生活的舒适程度,也降低了工作效率。从1980年代开始,为了使巴黎重新成为适于生活的城市,巴黎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一方面大力改善交通和停车条件,减少私人汽车的数量;另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公共交通的结构调整,提高没有小汽车的城市生活的效率和质量。终于,公共空间重新回归行人,节日氛围重新回归街道,巴黎重新成为一场欢快的节日庆典。无论在巴黎逗留一天或数日,还是天天生活在巴黎,人们都可以体会到巴黎生活的丰富多彩。节日庆典美化了巴黎,丰富了巴黎的生活,使生活富有韵律,使空间富有色彩:就像在昨日生活的树根和枝干上,不断添加今日生活的枝叶。
过去、现在和将来,节日庆典在巴黎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它使巴黎的人口成为当地的居民,使途经巴黎的过客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为当地的居民,因而得以体验巴黎生活的氛围和真谛。节日庆典把巴黎变成一座适宜居住的城市。当然,这并非巴黎的专利;巴黎的成功经验同样可以在别的城市复制、调整和变换。人们在某地定居,就是要与所在的城市、街区和空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既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也存在于建立在独特逻辑关系基础上的交流网络之中;此处所谓的逻辑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功能逻辑和理性逻辑,而是与人或事,与庄严的规定,与空间的用途以及其中的活动密切相关,它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参加节日庆典并非生活之必需,但节日庆典以一种慷慨的姿态丰富了生活中的关联。一个城市的精神和灵魂存在于节日庆典之中。正是这个灵魂,这种集体的氛围才是“居住”的最终结果;它把居民及其居住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帮助每个居民面对生存的困难。归根结底,我们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奥古斯汀·贝克(Augustin Berque)在《控制城市》(La maitrise de la ville)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即:什么是适宜于生活的美丽城市?为谁、出于什么原因、通过什么方式来建设适宜于生活的美丽城市?这也正是城市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UPI
本文原载于《国际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p79-84
作者:西尔维·拉格纳(Sylvie Ragueneau),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规划师、研究员
译者:刘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副研究员(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聘教授、副院长;《城市规划(英文版)》执行主编;《国际城市规划》编委)
刘永恒,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巴黎精细化城市规划管理下的城市风貌传承
大巴黎地区——漫长历史中的四个时刻
法国历史街区再生的过渡使用模式研究——兼论对我国城市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启示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佳篇回顾 | 巴黎是一场节日庆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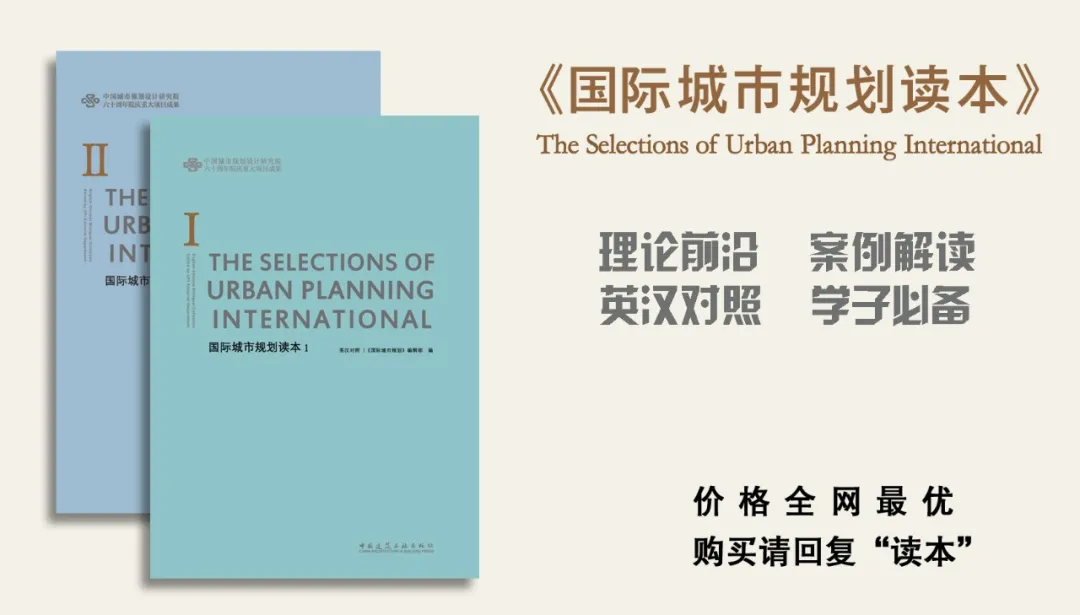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