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2023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如今,智慧城市被赋予“科技”和“进步”的光环,令人不由自主地信服并欣然向往。然而这种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否在盲目崇拜技术的过程中忘记了技术本应服务于人的目的?
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技术反客为主,从服务人类的工具变成支配人类的力量。这种异化现象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各种智能系统被盲目部署,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技术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它们是否符合社会整体利益[1]?
纵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总是先有明确的目标或待解决的问题,然后才去寻找或发明相应的工具。然而,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这一逻辑似乎完全颠倒了。很多时候,智慧城市部署不是针对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而是运用智慧工具去寻找甚至“发明”问题。陷入技术主导怪圈的智慧城市,将各种先进技术生硬地塞入城市肌体,然后再去寻找它们可能适用的场景,这种“拿工具找问题”的做法,不仅本末倒置,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正如西方谚语所说:“如果你有一个锤子,你看见的每件东西都像钉子”,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技术与社会需求脱节[1]。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标准化信息被视为决策的基础,但这些所谓的“标准”信息往往存在严重缺陷。问卷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垃圾进来,垃圾出去”的数据收集与处理困境,已经凸显了技术主导思维的局限性。当受访者因为不了解情况而随意给出答案时,当受访者的回答与其实际行为完全不符时,调研所获得的其实都是“垃圾数据”。但可怕的是,决策者往往将此类数据奉为圭臬,对其结构性缺陷选择视而不见。这种对技术的盲目信任,难免有些掩耳盗铃或自欺欺人,其结果可能会使城市治理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难以真正服务于市民需求。
两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或可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其一,连锁餐厅的电话调查中,受访者因为不了解价格而被迫随意给出答案;其二,城市规划的问卷调查中,独居老人给社区内小超市的重要性作出的高分评价与其实际生活方式完全矛盾——她平时甚至只去大超市购物,小超市对她来说似乎可有可无[1]。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标准化问卷所收集的信息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的决策必然存在误导和偏差,自然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可见,当我们过度依赖技术时,实际上是在放弃人类最宝贵的特质——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拥有多少先进技术,而在于如何运用这些技术来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当技术成为主导力量时,人类的价值观、道德判断和社会需求很容易被边缘化,而城市治理中最核心的要素——人的因素,恰恰是最不能被技术所替代的[1]。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时刻警惕技术异化的风险,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的原则。智慧城市建设,理应以人类的生存与延续为最高准则,聚焦全体人民的幸福与尊严[1],而不是技术的复杂与炫目。
[1] 梁鹤年. 智慧城市(三):治理层[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3(Z3): 42-45.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三):亚里士多德的“变”[J]. 城市规划, 2012, 36(9): 59-69, 90.

王冬银
2022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社会论坛上,梁鹤年先生发表了题为“智能社会与协同治理”的演讲,提到了智能机器的产生原意是模仿人的智能,以提升人的体力、智力、感知能力——智能机器通过不断模仿学习、信息数据处理和形成决策执行,服务城市治理[1]。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是“人在城里是为了生活,他留在城里是为要生活得更好”[2],那么什么是“好”?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得到提升和发挥自己的条件和机会,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有获得感,就是“好”。笔者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智能机器的使用,也应是追求这个目标。
智能机器是机器,其独特之处是“有学习能力”,信息输入运转后可以模仿人的思维,处理接受的指令和任务。但是如果深入反思就会发现,实质上最初这些智能机器的发明不是为了城市治理,而是将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从商业价值角度将智能机器“包装”成城市治理工具,再“卖”给城市治理者用于城市治理。无论出发点是否源于对市民需求和城市治理的考虑,我们首先要对城市治理有正确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考察时所指出的,“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作为人类聚集地和文明象征,一座城市的品格和魅力不仅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景观风物,更在于它能否让人们感受到尊重和温暖,能否提供逐梦筑梦的条件和可能[3]。城市治理不是处理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与市民的关系,而是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取所需时产生的矛盾与纠纷,在考虑整个城市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和协调各类问题。运用智能机器管理或治理城市,也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衡量可适性和有效性——智慧机器能否协助政府在考虑城市整体的延续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市民之间的纷争。此外,要设计出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智能机器,绝不能以普适代替实际中的特定情况。可喜的是,部分当代城市治理已经初有成效地运用了智能成果,不少城市形成了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电子政务和城市信息安全系统、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基础数据库、多方位电子商务系统等智能框架。
笔者特别想到一个话题。今年年初,中国推出了人工智能软件DeepSeek,它以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软件Chat-GPT的5%的算力成本,获得了与后者比肩的能力。其实,开发DeepSeek的幻方量化是一家靠炒股赚钱的金融公司,开发DeepSeek只是其副业。正是不图钱的出发点和特殊性,DeepSeek直接在全球开源,其“代码卖飞送全球”的做法震惊了全球,尤其是美国。类似于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很有可能创造未来、改变未来。一个智能工具的初衷不在赚钱图利,却能在信息采集、交流、发布与共享等功能上与城市市民产生极大共鸣,对于助推城市治理精准发力和靶向施策是极其有帮助的。然而,目前智能机器还不能完全度量和掌握人的真实意图和心思,且设备终会衰退,情况也会迅速变化,因此,城市治理目光不能过于集中和依赖于智能机器,而应回归到实实在在的城市运行数据,有效运用其智能收集存储分类大数据的优势,以有效辅助城市治理决策。
[1] 梁鹤年. 智慧城市(三):治理层[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3(Z3): 42-45.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209-232.
[3] 赵雅娇.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N]. 人民日报, 2025-03-09.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工具主义 VS. 人本主义
李媛
本篇是梁先生讨论智慧城市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与第一篇《地下层》聚焦智能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等物质空间的关系,第二篇《地面层》聚焦智能技术与人类感知及活动的关系相比,本篇探讨了更深层次的管理或治理问题,即“应该”如何应用智慧技术服务社会行为。
人的行为千差万别难以标准化,而城市治理需要标准化难以“一人一策”,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往往是城市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过于强调智慧技术的工具属性或标准化的治理手段,容易出现先追求“智慧”工具再找应用场景即“拿工具去找问题”的问题;过于强调个体需求的差异,容易导致低效沟通、社会群体分裂等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是,智慧工具最初并不是为了城市治理而发明的,而是为了研究人的行为特征而发明的,比如利用大数据研究人的消费行为特征从而促进消费。换言之,智慧工具不是“目的”,而是旨在促进人类活动本身的“工具”。因此,城市治理不是市民与政府之间的事,而是政府解决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取所需时产生的矛盾和纷争,基于整体利益协调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尽所能时所需的互补和互助[1]。
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城市更新智能场景营造的本质很有启发。比如: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需要应对小区停车资源紧张的难题,智慧平台既能实时更新剩余车位信息,也可监管车辆占道或无序停放问题,是个有用且有效的工具;再如:社区事务小程序既需要为居民协商议事搭建平台,也需要为高效公平决策提供规则保障,缓解“搭便车”等集体行动难题。
因此,智慧城市的起点是认识人的需求和行为特征,而智慧技术或工具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数据搜集、分析、设计、监察和反馈能力,尤其是应对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换句话说,人本主义的智慧城市应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以智慧工具应用为手段,以更好地认识市民的典型需求及其之间的矛盾,从而提高市民和谐互动的积极性。UPI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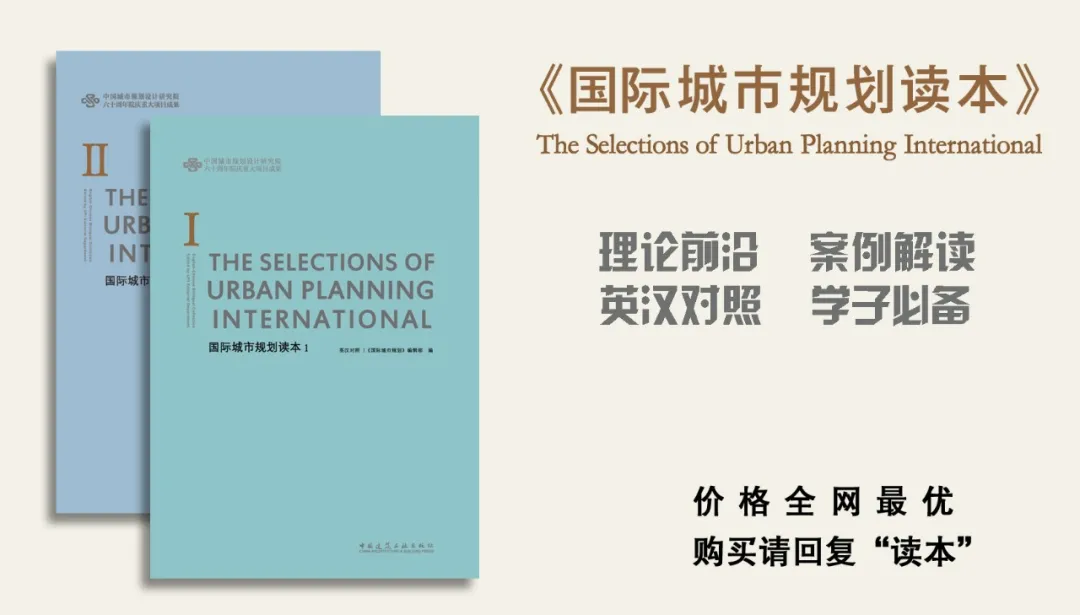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32)解读《智慧城市(三):治理层》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