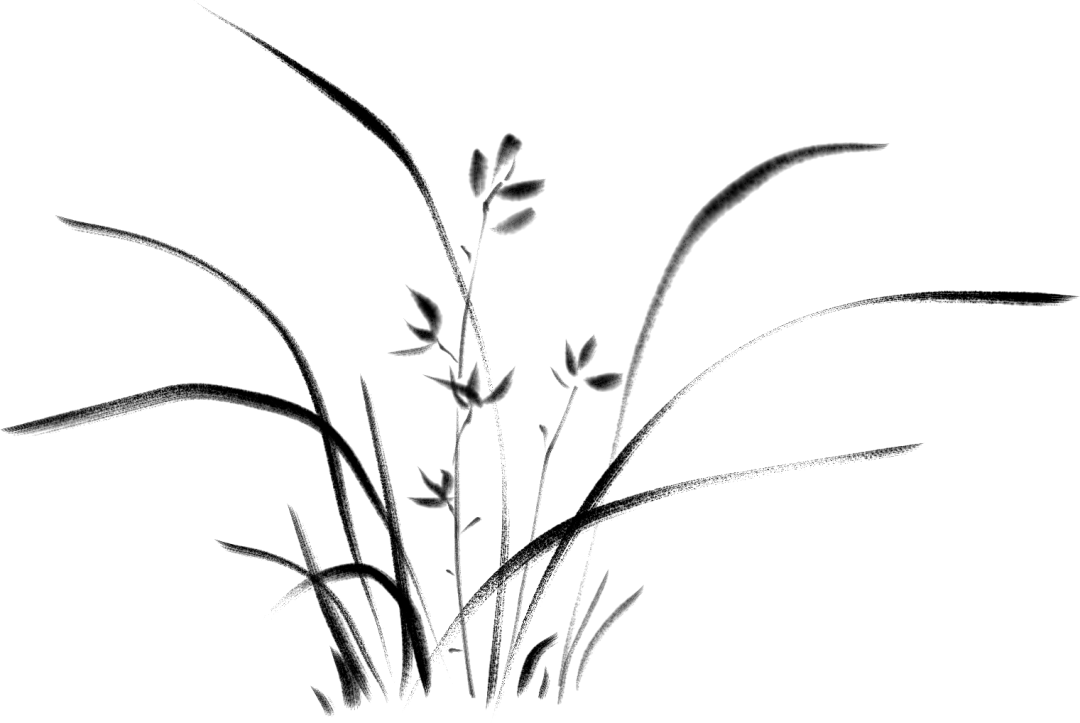
2025年4月21日上午9点,上海音乐学院第十二届“大音讲堂”——由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带来的《中华民族建筑的谱系认知与遗产传承》学术讲座,于汾阳路校区图书馆楼学术厅举行。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中心与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联合主办,上海音乐学院冷门绝学团队“中国少数民族濒危唱法数据集成、知识谱系与创造性转化”、国社科艺术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器乐艺术研究》提供学术支持,音乐艺术研究院、音乐学系、科研处协办,同济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多位专家及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共同参与。

图1 讲座合影
主持人冯磊副院长在开场致辞中代表学校对常青院士及到场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提到,此次讲座是建筑与音乐学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的跨界对话,希望本次讲座能够成为建筑与音乐在中华民族自主知识谱系和文化遗产方面共识、共建、共创的“上海经验”的开端,产生“美美与共”的对话与碰撞。

图2 冯磊副院长致辞
常青院士在开场白中援引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1999年墨西哥宪章的定义解析“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概念,将其分为建筑遗产、聚落遗产与景观遗产三类。“建筑遗产”涵盖文物建筑与历史建筑,这两类在中国台湾均被纳入“文化资产”;“聚落遗产”是集群概念的建成遗产,强调城乡聚落的整体文化特征;“景观遗产”则体现人地关系与互动,如“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概念。他特别指出,建成遗产需关注“实体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共生,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涵与互动关系。
讲座首先以中华民族、民系的汉语官话区、方言区,和少数民族的语族、语支区为背景,对其地域风土建筑谱系作了系统梳理和划分;
其次,以等降水量线为主要线索,讨论了历史上长城的文明分野、抵挡马队、机动运兵和护卫商道等营造用途,分析了游牧与农耕、北方与南方各族风土建筑谱系的特征要素,如帐幕穹庐、土木平顶、拱券穹窿、木构坡顶等类型及其交融衍化形态,绘出的相应谱系分布图谱,均体现“因地制宜,因材施用”的营造智慧;
再次,对宋《营造法式》木构建筑“材有八等”与古典音律间的类比关系,以及悬垂状举折屋顶与游牧民族帐幕的互涵关系进行说明,并剖析了汉化畲族赣匠-样式雷家族对清代皇家建筑的重要影响。
最后,常青谈及中华民族建筑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再生途径,特举西藏日喀则桑珠孜宗宫复原再生工程设计为例,讨论了藏族由碉房衍生的宗山宫堡构成特征,以及毁后重建中废墟保存,形体恢复及空间重塑的适应性再生过程。他并举新疆龟兹群众艺术博物馆工程为例,该设计提炼前伊斯兰化时期的佛寺穹顶元素,规避宗教敏感性,以多元融合手法表达异质文化基因的交融。这些都使建筑谱系的“边界”始终处于流动与重构中,包括伴随佛教东来的西域文化对汉地影响,如印度摩羯鱼(鸱尾)与彩画退晕法、希腊-印度式梭柱与须弥座、中亚琉璃瓦工艺。

图3 常青院士发言
总之,常青院士认为建成遗产保护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记录与精准测绘,系统还原地域民族建筑的聚落格局、匠作传统及仪式场景的内在价值关联,构建各族风土建筑的完整价值谱系。在此基础上,“适应性再生”成为关键路径——既要尊重遗产的物质真实性,又需探索功能活化的可能性,并整合结构加固、环境控制等传统与现代技术。此外,他特别指出,遗产的永续生命力离不开社会参与,需建立社区协同机制,让居民成为保护与活化的主体,尽力避免“标本化”保护导致文化断层。在结语中,他还提出了定期举办“中华民族建筑日”的倡议。
讲座结束后,在教学楼贵宾室举行了圆桌讨论,由徐欣研究员主持,常青院士、同济大学王红军副教授、潘玥副教授、李璟昱老师、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伍维曦教授、孙月副教授、张玄副教授、吴洁副教授、邢媛博士、王翩博士、复旦大学张梦翰研究员、四川音乐学院刘雯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魏育鲲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亚副教授、广西艺术学院朱腾蛟副教授等老师参与了讨论,围绕音乐与建筑的跨学科研究展开,聚焦音乐与建筑的谱系分类、认知与传承,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造等问题。

萧梅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入手,强调音乐与建筑在研究理念、视角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她指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常基于语系、语族、地理和历史等分类方式,如蒙古、突厥等语族划分,或黄土高原等地理分区,以及历史脉络下的谱系梳理。这些分类方式并存且相互重叠,反映了音乐与文化背景的深层关联。她特别提到少数民族濒危唱法的数字集成与知识谱系构建,需依托类型学基础,如藏羌的四度框架、壮侗的五度框架及苗瑶的三度框架等。她结合常青院士关于建筑认知的介绍,提出音乐与建筑在类型学上的相似性,建议联合探索“民族建筑音乐日”等创新形式,并在上海这一现当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汇点推动多民族文化案例研究。萧梅的发言奠定了跨学科合作的基调,强调音乐与建筑在谱系与文化传承上的潜在协同。

刘雯通过示范演唱,分享了她在多声部民歌研究及慕课转化中的经验。她聚焦侗族、藏羌、哈尼族等民歌的演唱特点,指出这些民歌常模仿自然声音,如侗族的五声部模拟鸟鸣、藏羌的波浪交替式模仿岷江水流、哈尼族的梯田式即兴呼应。她认为藏族民歌融合了羌族的波浪式与鸽子飞翔的声音,呈现“戈特曼”融合性,而苗瑶语族民歌则介于壮侗与壮缅语族风格之间,体现过渡特性。刘雯老师建议在慕课基础上进一步归纳理论,并探索建筑领域是否也有类似融合特质。她通过生动的演唱和案例分析,为会议注入了实践维度,引发了关于音乐与自然、建筑与环境的关联讨论。

徐欣回应了刘雯老师的发言,指出声音与视觉的转化是音乐研究的重要逻辑。她认为民间音乐常从视觉形态(如蒙古族山峰或哈尼族梯田)转化为音乐形式,而分析时需反向寻找声音形态的视觉工具,以理解自然生态与音乐形式的关系。她强调听觉与视觉艺术的相互转化特性,呼应了刘雯老师关于民歌自然模仿的观点。

伍维曦从音乐史视角探讨音乐与建筑的密切关系,指出音乐史受美术史和建筑史影响,许多术语如“文艺复兴”“巴洛克”直接源于视觉艺术。他以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经文歌为例,说明建筑比例与音乐节奏的关联,强调音乐虽为无形的声音,却在特定空间中发生,受空间制约。他认同萧梅老师关于传统音乐与建筑再生的共鸣,认为传统需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可不断诠释的活态文化。他特别提到常青老师关于日喀则建筑再生的案例,赞叹其展现建筑生命周期的生动性,并认为音乐与建筑研究有“打通隧道”的潜力。伍维曦老师的发言拓展了历史维度,强调空间与文化再生的共性,为跨学科合作提供了历史依据。

常青回应伍维曦的发言,高度认同音乐与建筑在谱系分类上的相似性,指出“风土”概念,认为音乐能反映地域的情感、性格与生存状态,如乐天或悲凉的集体性格。他以“风土”为核心,指出建筑与音乐均源于特定地域的风俗与感官体验(如视听触觉),强调音律可作为理解风土的起点。常青老师建议双方联手探索,尝试以音乐与建筑的谱系分类为基础,推动文化再造。

孙月从音乐美学与哲学视角,分享了她对音乐与建筑跨门类研究的兴趣。她指出,国外研究多从建筑角度探讨音乐,而国内反之较少,存在研究不对称。她提出从微观(装饰细节)、中观(形态结构)及宏观(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进行美学概括,并以舒曼第三交响曲《莱茵》为例,阐述复调手法与科隆大教堂建筑母题的类比性,指出音乐的音色扩展类似管风琴的丰富性。她还提到西方艺术研究中音乐调式(如多利亚调式)与建筑柱式的类比,强调巴洛克时期音乐与建筑装饰性的共通性。

王红军回应了孙月的发言,他认为音乐与建筑的关系不仅仅在于类比关联,也要强调空间作为连接两者的关键切入点。他以参观上音东方乐器博物馆时听到的丝弦琵琶声为例,指出其在小型厅堂中的现场感不同于户外音乐厅,反映了空间对音乐体验的塑造。他进一步分析侗族多声部清唱与山谷回声的关联,藏族洪亮声调与高原环境的对应,提出以物质性现场感为一个研究课题,探索音乐与建筑的深层联系。

萧梅补充了王红军的观点,分享了她对民族建筑与音乐空间关系的观察。她提到自己曾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同民族的建筑形态常为特定音乐文化提供空间,如藏族的“坡”型空间、回族的“窝”型空间。她还提到古戏台的声学设计,认为其空间结构能放大声音,甚至修复演员嗓子,类似西方教堂的歌唱效果。萧梅老师曾在考察山西古戏台时提出在此举办世界性歌唱比赛的设想,强调建筑空间与声音的互动,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
张梦翰认为他所研究的谱系并非是类型学的概念,而是从语言学与生物遗传学背景出发,提出以系统演化视角重构音乐与建筑的发展历史。他介绍了自己在汉藏语系起源研究中的经验,强调通过语言特征重构历史演化过程的可能性。他建议量化建筑、语言及音乐的类型特征,探索东亚及东南亚区域文化共演化的模式,回答这些特征是否具有共同发展范式。张梦翰老师特别提到建筑的类型特征是否可与语言、音乐特征结合,共同揭示区域文化的历史演化。

常青回应了张梦翰的思考,他认为文化量化是高难度挑战,因为文化不像自然对象可完全用因果律归纳。他指出,文化因地域差异而复杂,但张梦翰的数学背景可为量化提供模型支持。他提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认为可尝试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文化对象,并强调文化优先于技术。常青的回应平衡了科学与文化的张力,为跨学科合作的未来路径提供了启发。
潘玥受日本白川乡世界遗产保护的启发,提出将音乐(非物质遗产)与建筑(物质遗产)结合,增强民族文化魅力。她分享了白川乡通过全村修缮大屋顶、保留田间民歌演唱的保护模式,认为这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融合创造了沉浸式体验。她建议在上海举办“风土音乐日”,通过民乐演出或风土建筑装置,扩大民族文化的受众吸引力。

魏育鲲从技术、文化对于建筑的制约关系出发,指出了建筑的很多转向,跟文化和美学的转向并不必然是正相关,因为建筑有新技术的支持。同时她还举例说明音乐与建筑的不同,音乐的载体属性使其在地性更灵活,如在上海唱藏族歌曲可行,但在上海建布达拉宫不可行。最后她提出了疑问:在谱系研究中,技术与文化哪个是关键的制约要素,还是说两者一体?
常青回应强调文化是主导因素,以中国建筑的拱券未广泛发展的案例说明文化理念(如注重木构建筑)限制了技术应用。他指出,技术需与文化一致时才能突破,如西方中世纪尖券技术因哥特式文化需求而发展。他承认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尚未完全解开,但强调文化始终是第一推动力。

王翩从历史地理学视角,指出“风土”在音乐学、建筑学及文化地理学中的不同解释。他认为音乐学常将“风土”译为乡土冲突,建筑学强调地域性,而文化地理学视其为基于心理认知的空间。他提出以语言或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分类标准的局限性,认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角度看,需关注历史尺度上的文化融合与语言变迁。

常青回应王翩的思考,承认建筑的“风土”是动态变迁的,特别以明清以来人口流动(如大槐树传说)为例,说明文化随人迁徙而变化。他指出,地面建筑因迭代更新难以断代,研究重点在于保护标本式遗产并推动再生。常青老师强调“再生”是未来的核心,呼应了王翩老师关于文化融合的建议,并将讨论引向保护与创新的平衡。
综观整个圆桌会议的讨论,各位老师在音乐与建筑的谱系分类、空间关联及文化传承上碰撞出丰富火花。这将共同推动音乐与建筑研究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也为未来的跨界联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撰稿:彭小峰
图片:鄢杜玖坤
编辑:陈雨馨
审核:萧梅、徐欣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建筑遗产学刊):第十二届大音讲堂|常青院士《中华民族建筑的谱系认知与遗产传承》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