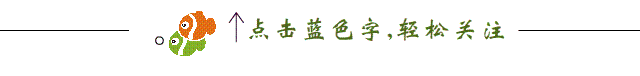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往年会期长了两天,是因为它套开了一个很“罕见”的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往年会期长了两天,是因为它套开了一个很“罕见”的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它召开的密度实在低的惊人,距离上一次召开已经是37年前了。
那个时候,会的名字跟现在有着两字之差,叫“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别小看了这两字之差,它折射出来的可是中央对于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恐怕这也是史上规格最高的城市工作会议了。
37年,光阴倏忽,何以重启城市工作会议?媒体纷纷对此做了解读,无非就是“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新闻通稿里的原话。
回溯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共召开过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分别是1962年、1963年和1978年。这三次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都有一定的“问题导向”,都是因为在城市建设中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才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和解决。(很显然,由此也可以推断出,此次会议的召开也是因为城市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早在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中共面临着管理城市的重任。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描绘出了新中国的蓝图。
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造城运动一触即发。
党媒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中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已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当时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处于薄弱的情况下,这样的提法并不过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切的城市生产都按照计划逐步推进。
1952年,国家开列了按照工业建设的比重分类建设城市的计划。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6月,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制度保障: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由工业建设的速度来决定。城市建设必须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工业建设的中心项目所在重点工业城市的建设。可以看出,当时的工业布局并没有倾向于中小城市和区县。
1955年9月,国家建委提出: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为了抑制消费,为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甚至毛泽东提出“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比较有利”的战备考量。
上世纪六十年代,称得上是一个“疯狂”的时期。
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工业建设盲目推进,各地工业区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兴建楼堂馆所,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 军事博物馆等“建国十大工程”均建于建国十周年前夕(1959年10月1日)。不少城市“放卫星”,纷纷提出要建设超大规模城市:盐城提出要搞成100万规模的大城市,株洲要扩容到80万……
这一远大图景的提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城市,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骤然增加,许多城市不切实际地扩大规模,城市规划严重走偏,城市进入无序、混乱发展状态。
1960年11月,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以此为肇事,新中国开始了“第一次逆城市化运动”。
1961年-1963年,近三年时间,全国减少城市25座,大量来自农村的“盲流”被遣返回原籍。
1966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城市化严重停滞。十年间,1700多万城镇青年下放边疆和农村,城市建设几乎停顿。城市规划方面的队伍全部解散,相关工作全部停止。

直到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城市的整顿工作”,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这里所谓的“大城市”,指的是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
会议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从1979年开始,所有省会城市和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不含三大直辖市),以及对外接待和旧城改造任务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百分之五,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要建设好城市,必须有科学的城市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市长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等。

这也意味着,城市规划的地位重新被修正和恢复。在这个时期,很多高校也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城市规划专业。如南京大学,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凭借雄厚的经济地理学基础,很快就在城市规划的教学、科研、实践等方面崭露头角。
1980年,国家公布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名单,这也标志着,以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式的建城模式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从这个时候开始,之后的30年里,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飞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只用了3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上百年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创造了“中国式奇迹”,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从1.7亿人增至7.5亿人。每年城镇新增人口21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
1983年,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式发展道路成为主流思潮,全国小城镇遍地开花,得到了飞速发展。
1984年,我国颁布实施《城市规划条例》。从1985年到1992年,建制镇从2851个猛增到14182个!
1990年,新的《城市规划法》出台,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方针。同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这种开发模式有悖于当时的发展趋势,一度受到极大争议。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各城市激进的城市化拉开帷幕,《城市规划法》几乎沦为空谈。

开发浦东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号召向上海学习
1998年10月,中央召开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小城镇战略”。
2000年10月,国家在编制十五规划时,城市化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2004年,“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城乡之间的二元差距越拉越大。三农问题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国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说法。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内涵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想象。
在相继推出“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圈、群时代。
不可忽视的是,在各地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诸多问题也一一暴露于人前。坍塌开裂的短命建筑、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奇奇怪怪的地标、贪大求洋的规划、逢雨必涝的“城市看海”……一股从上而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在全国上演,城市化脱离正常轨道,出现了“大跃进”。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转向借力于城市化自身的内生动力。一时间,这个圈、那个带风靡全国。它们不再强调行政区划概念,而是集中于经济概念和文化概念。
2008年,国家颁布实施《城乡规划法》,规划编制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基本形成,规划的法治地位基本确立,体系与队伍十分完备,然而具体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有的地方城市发展思路出现偏差,有的地方规划空间体系没有办法整合,有的地方规划沦落为政府主要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这一切已经不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没有理顺,顶层设计出了问题。
37年来,我们的城市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因为太快,所以很多问题都来不及消化,而现在我们将会把速度和质量“并轨”。可以想见,以后城市发展的核心,不再是单纯地扩张建设,而是纵向深入优化治理。
在这种思想和理念的指引下,以最高规格来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可谓恰逢其时。而新的城市工作会议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划工作也必将转型创新,走向变革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在争论,到底走大城市发展道路,还是走小城市城镇发展道路,我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前文中可以看,以前的方向和思路一直是城镇化派占上风,而此次会议名称由“城镇化”转为“城市”,这恐怕不止是概念的变化,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内涵和思路的纠偏。
经由公开资料综合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长按二维码,一键加关注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国际资讯 | [中东]阿曼塞拉莱滨水区重塑总体规划/卡塔尔公共交通总体规划(2025.5)-规划问道](https://weixin.caupdcloud.com/wp-content/uploads/2025/05/frc-69b1f46a51c00c56ea0c6452271abf56-220x9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