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Making of Polycentricity in China’s Planning Discourse: The Case of Tianjin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DOI: 10.1111/1468-2427.12876
作者:Weikai Wang,Ya Ping Wang,Keith Kintrea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多中心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对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其在中国规划理论和实践中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但是对其如何出现于城市总体规划中、内涵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化,又折射出怎样的权力关系,却鲜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天津在1986年、1999年、2006年和2016年编制的四次城市总体规划为例,分析了上述规划的时代背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迁、多中心意在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所采取的表现形式。1986年规划按照中央方针,提出以中心区和滨海区为核心的城镇等级体系,意在疏散人口;1999年规划意在加快自身经济增长,将中心区、滨海新区和八个城市组团共同构成中心城市,引导实现专业化分工;2006年规划进一步提升了滨海新区地位,并在发动基层政府的基础上,提出了11个新城增长极;2016年规划则在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突出了公共服务和商业等更多元素的多中心布局,并以网络化替代了等级化的概念。文章最后指出了多中心概念的工具化使用所蕴藏的开发风险。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Living in Social Housing? New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0, 35(4): 612347
作者:David Prentice, Rosanna Scutella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澳大利亚社会住房的目标人群指向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与私营租赁住房相比,社会住房被认为能在社会心理方面提供有益影响,并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其他方面的福利。但上述观点在美国以外的实证研究证据有限。与美国类似,澳大利亚实行二元住房租赁制度,但后者能提供更多的福利和全民医疗。这篇论文即以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统计匹配方法(statistical matching method)估算了社会住房对居民的就业、教育、健康、监禁和无家可归等一系列住房和非住房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社会住房能为居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安全网”,使他们不致于无家可归。然而,至少在短期内,社会住房的居民与未享受社会住房而又面临住房风险的个体在就业、教育、身心健康和被监禁方面拥有相似的结果。该研究揭示了简单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居所,而不考虑其他方面需求的住房政策很可能难以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这对国内保障房政策的优化完善具有一定参考。
Pulo Mas: Jakarta’s Failed Housing Experiment for the Masses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10.1080/02665433.2020.1746192
作者:Kemas Ridwan Kurniawan, ChristopherSilver, M. Nanda Widyarta, Elita Nuraeny
推荐:傅舒兰, 浙江大学建工学院。fushulan@zju.edu.cn
这篇最近上线的原创论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印尼雅加达在1960年代为解决城市大规模的平民住宅短缺问题而制定的郊区普罗马斯规划建设方案。论文在大致介绍印尼从荷兰独立后的政治变动到苏哈托新政建立,以及1960年代日益剧烈的平民住宅短缺问题后,将视野集中在具有代表性、革新性的普罗马斯项目上。从项目缘起、革新特征、制定人员的知识来源、变更走向、实施结果等方面,对该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结论来看,作为一项城市远郊住宅区的项目,普罗马斯引进了当时较新的绿带、人车分离等规划手法,是成功的住宅区规划和建设实践。但如果从项目制定的缘起来看,并没有能解决平民住宅问题而是转向成为中产阶级住宅,使得这项号称平民住宅的项目,实际上成了一项失败的实验。作为一篇研究非主流西方国家的论文,文章在背景铺垫展开以及细节剖析上精炼老道的写作手法,十分值得学习。
排版 | 徐嘟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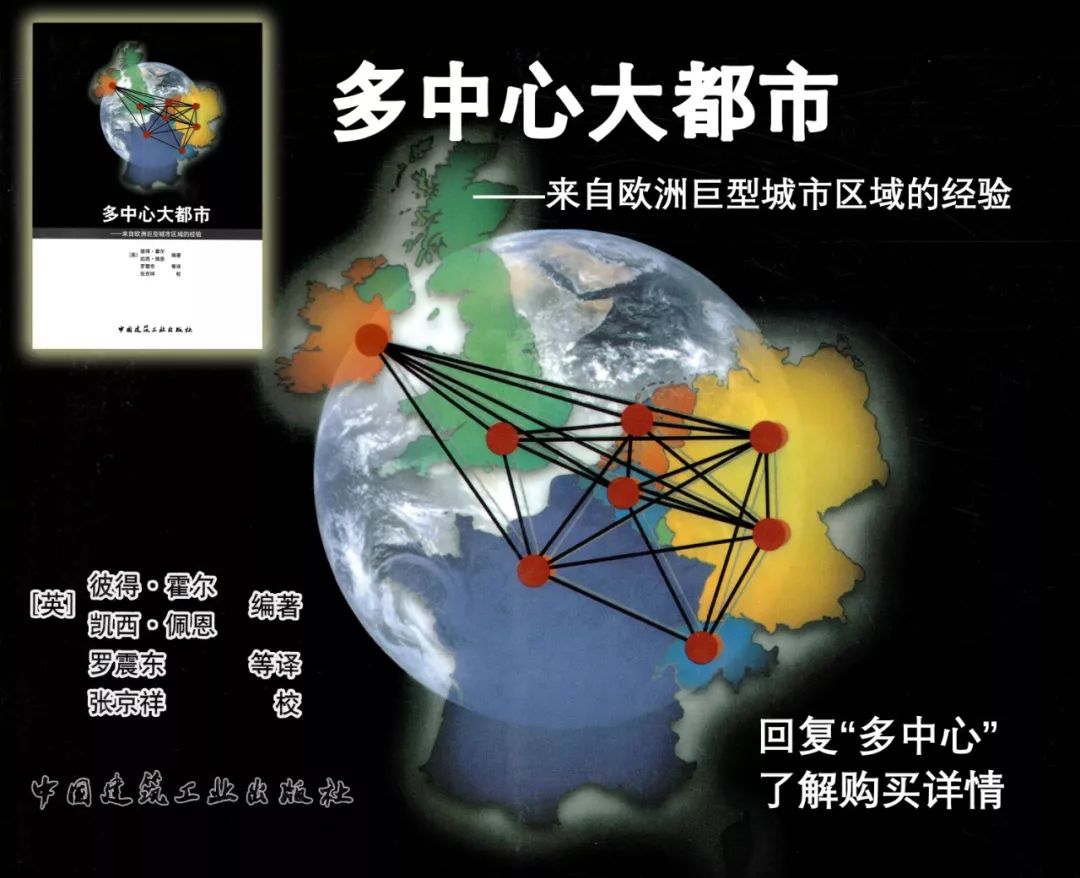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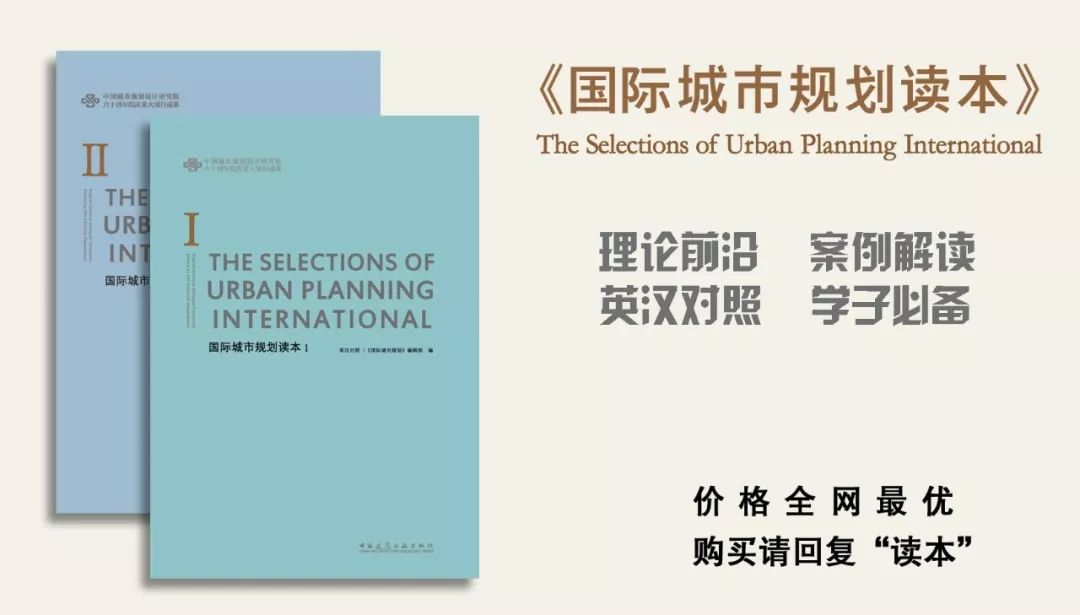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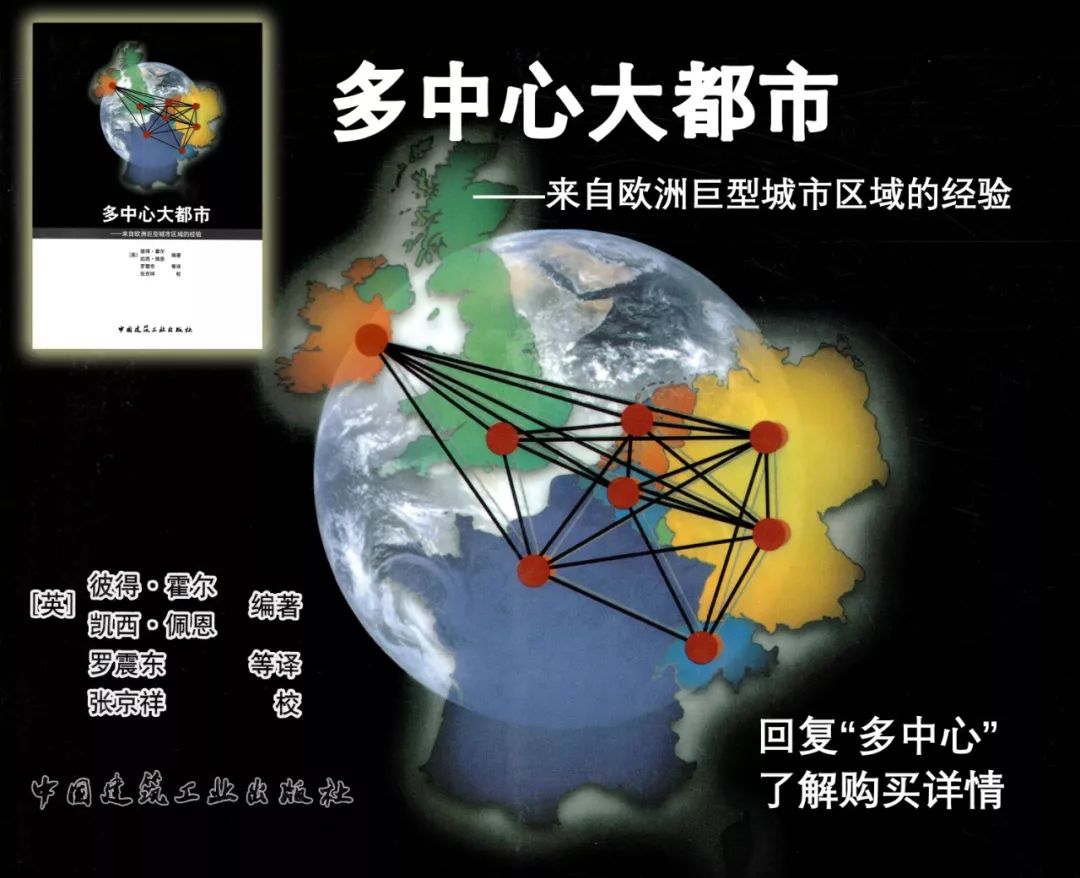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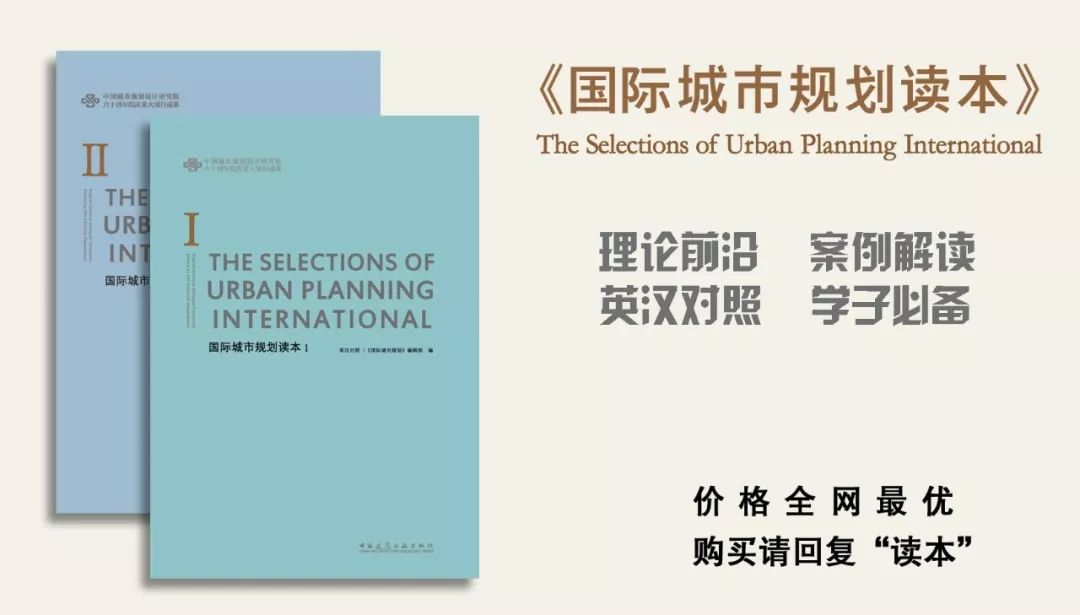
 第二期讲座课《技术发展与未来城市》 |《新城市科学》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二期讲座课《技术发展与未来城市》 |《新城市科学》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AI 大模型高级研修班》重磅来袭!涵盖八大主题,六大项目实战,四大行业应用丨城市数据派
《AI 大模型高级研修班》重磅来袭!涵盖八大主题,六大项目实战,四大行业应用丨城市数据派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加快赋能应用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加快赋能应用 第十章《基于多元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十章《基于多元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第二章《基于城市人工智能的城市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城市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2025春季学期MOOC上新啦!
第二章《基于城市人工智能的城市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城市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2025春季学期MOOC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