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所需要的城市——迈向以满足人类需求为导向的城市主义
The Cities We Need: Towards an Urbanism Guided by Human Needs Satisfaction
源自:Urban Studies, 2021,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11045571.
作者:Rodrigo Cardoso, Ali Sobhani, Evert Meijers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尽管目前城市研究学界对于城市空间如何回应物质和利益需要的研究已经相对充分,但以上研究多仅从经济或者技术视角评估城市,展望其发展前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作者提出从“满足人类需求”(human needs satisfaction)的角度进行补充。作者简要回顾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人类需求理论的探讨,认为在五个方面尚存争议:其一,对人类需求的确切含义尚未达成共识;其二,不同种类的人类需求是否存在着如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需求(五)层次论”;其三,如何定义人类需要的满足,应该基于主观判断还是客观描述;其四,人类需求的理论和实际政策应用之间存在脱节;其五,人类需求是普适性的,还是可能因时空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回应以上争议,作者在智利经济学家曼弗雷德·麦克斯-尼夫所提出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Human Scale Development)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由9种价值性需求(axiological need)及其20个维度与4种存在性类别(existential category)矩阵构成的人类需求研究框架。具体而言,价值性需求包括生存(subsistence)、安全防卫(protection)、情感(affection)、认知理解(understanding)、参与(participation)、闲适(leisure)、创造(creation)、认同(identity)和自由(freedom);存在性类别则包括存在(being)、持有(having)、行动(doing)和互动(interacting)。除了价值性需求中的生存,框架中的各种需求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化的划分,相反,在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同时性、互补性和权衡交易构成了基本特征。框架还对需求和满足物(satisfier)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作了明确区分:一方面承认人类需求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满足物可能随着背景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作者认为,这一框架通过厘清一系列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Local Border Reforms and Economic Activity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1): 81-102.
作者:Peter H. Egger, Marko Koethenbuerger, Gabriel Loumeau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一般来说,行政边界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很难被识别并量化分析。本文以德国市级边界调整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地方行政边界调整对空间经济活动分布的影响。1998—2013年,德国行政边界调整使得一些自治市被合并,导致其失去了行政中心的地位,而合并后的自治市又形成了新的、更大的行政中心。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地理编码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同时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边界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因果效应,避免了行政边界调整所致的缺乏下级行政单元行政数据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合并后城市的新行政中心显著增加了本地经济活动;被合并城市失去行政功能的城市中心,其经济活动减少;合并后城市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与被合并城市的经济损失之间呈正向关系。研究评估了这种影响机制,分析了新行政中心的位置、人口、本地活动和先前存在的公共服务等因素对这种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与行政中心的距离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这说明行政边界的变化导致了行政区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行政中心对于经济活动具有向心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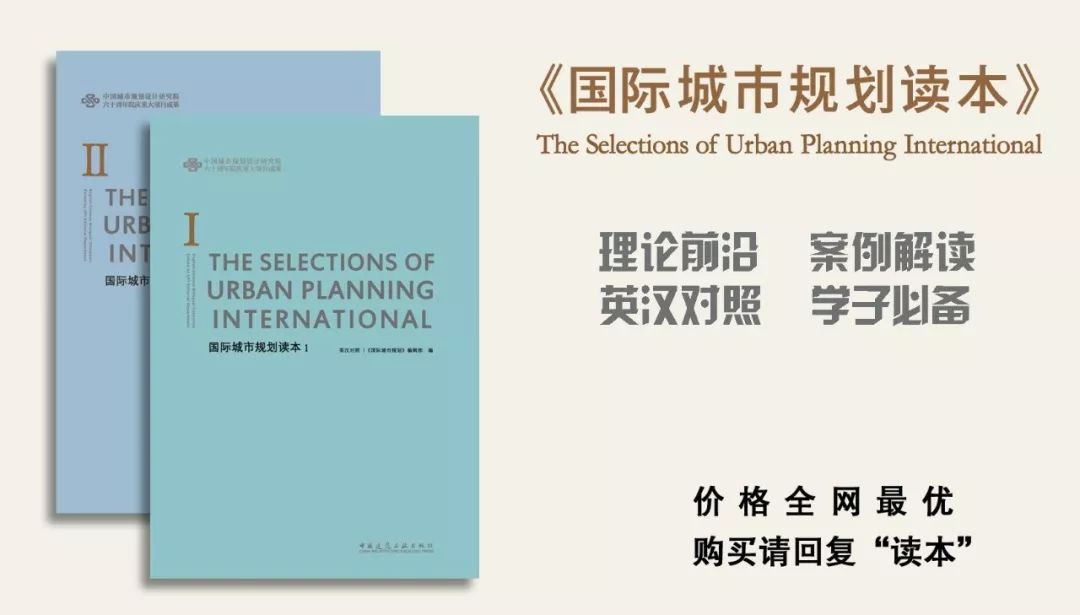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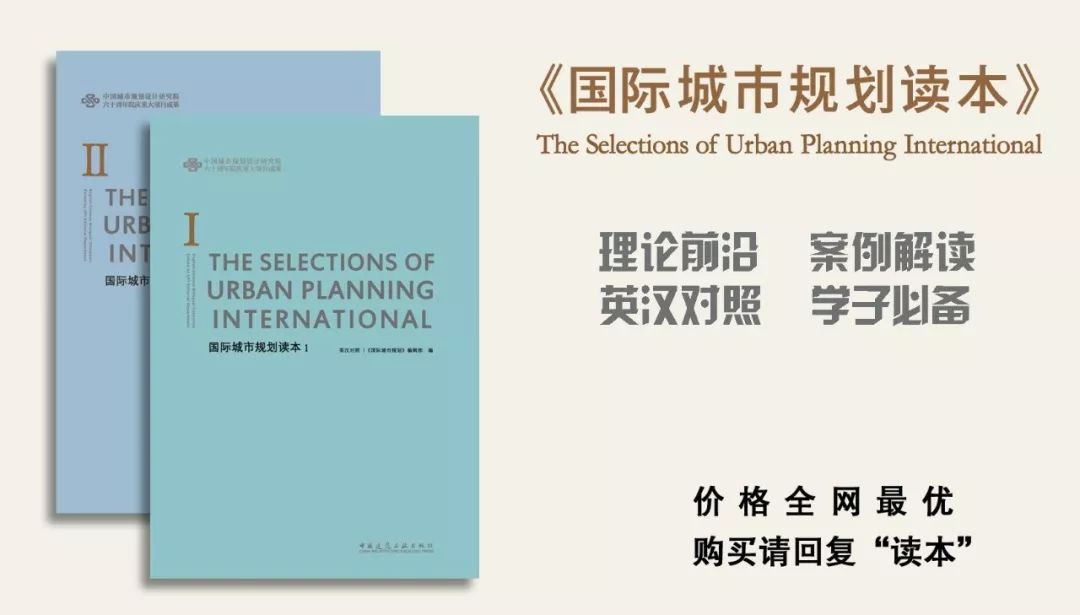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第二章《基于城市人工智能的城市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城市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2025春季学期MOOC上新啦!
第二章《基于城市人工智能的城市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城市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2025春季学期MOOC上新啦! 【报名倒计时2天】如何申报创新平台?以工程研究中心及博士后实践基地申报实践为例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2天】如何申报创新平台?以工程研究中心及博士后实践基地申报实践为例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2天】利用社区、公服POI数据对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2天】利用社区、公服POI数据对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省市级课题申报与结项实践及科技奖励申报实践经验分享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省市级课题申报与结项实践及科技奖励申报实践经验分享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社区生活圈现状评价:如何将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社区生活圈现状评价:如何将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