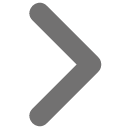在10月26日结束的“城市与我们:流动的公共”三联人文城市年度论坛中,电影研究者戴锦华、建筑师张永和、哲学家汪民安、城市规划专家李晓江、多媒体艺术家费俊、当代建筑及城市评论家周榕、人类学家项飙、音乐人小河8个不同领域的嘉宾,分别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和观察视角出发,带来了他们对于城市中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的思考。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聚焦城市社会变迁中“人”的显影。在他看来,“人”已然是我国当下最核心的话题。中国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人群逐渐呈现出更复杂、更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取向?怎么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元化的体验消费的场所?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于社会来讲越来越重要了。”李晓江觉得,这一点可能恰恰就是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价值所在。
以下是李晓江的演讲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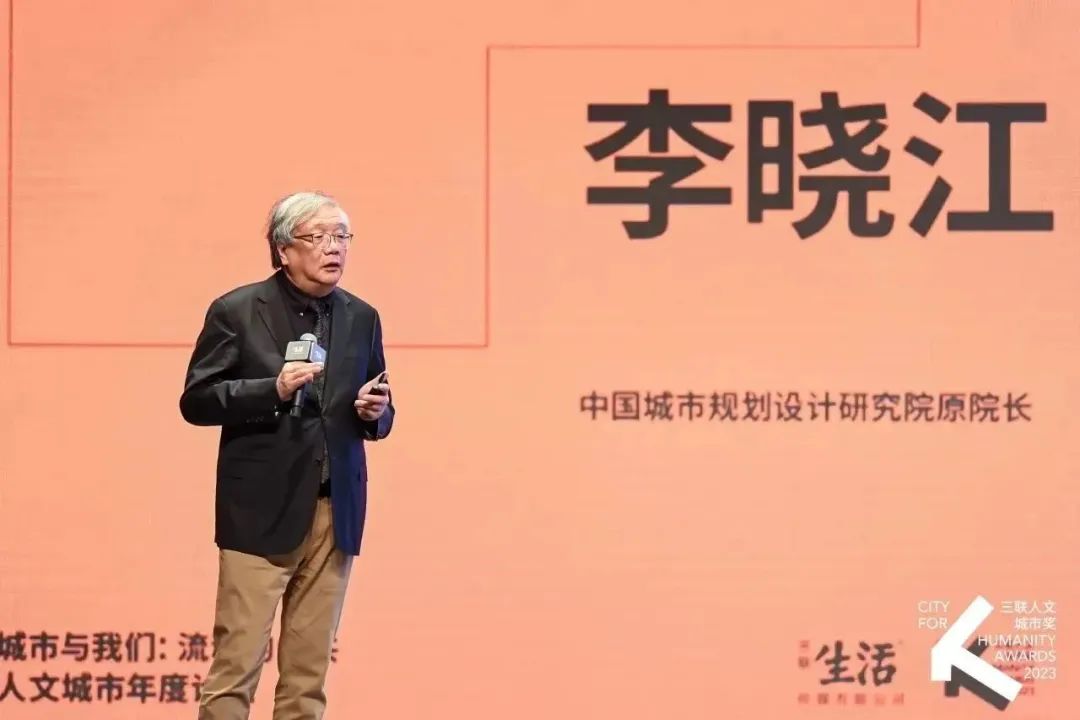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分享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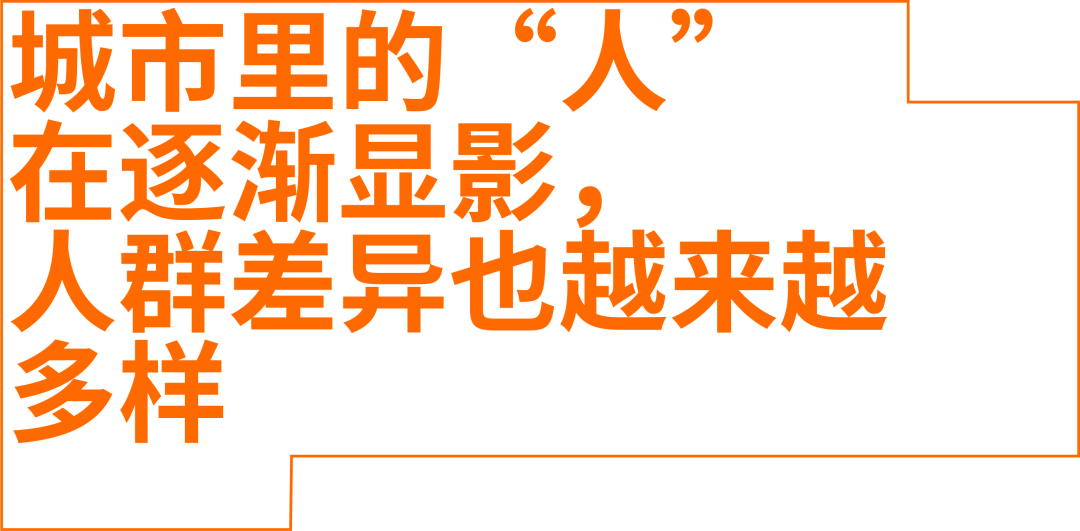
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叫“‘人’的显影”。我们玩过摄影的人都知道,显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我觉得这种过程恰恰能够拿来形容当下。中国经过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我们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渐变的、是逐渐清晰的,甚至到目前为止仍然还不够清晰,它还会显现出更复杂、更多样的人群差异。
所以我想,在讨论这样一个大话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怎么认识人。因为做了四十多年的规划,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做任何规划,我们是不是能把人的事情想明白?把人想明白,你所有的规划的理念、规划的思想和规划的具体的手法和方案才会是对的。
如果人的问题想不清楚,很可能很多努力最后会是无效的。因为我们的城市也好,空间也好,场所也好,是给人用的。

摄影:zhang kaiyv
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十九大重新描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用了一句话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人均GDP已经从200美元到了13,000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从一个极端贫困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中高收入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必然会、也有资格提出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天的年轻人去问问你们的父辈、你们的爷爷奶奶,在年轻的时候有美好生活的欲望吗?也许有,但只能做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反过来讲,当社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时,我觉得对所有的建筑师、规划师来讲,其实都肩负着同一个责任,它是给社会做供给的一方。我们给政府做规划、做设计,给开发商做设计,最后变成物质空间,成为一种社会供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需求方去想。第一,什么叫美好生活需要?第二,为什么会提出美好生活需要?第三,提出美好生活需要的是什么人?我想把这些事情想明白了,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

摄影:zhang kaiyv
建设部有一位领导,非常精准地把中国未来的发展用6个字表述了:“治病、跨阱、筑梦”:
第一是治病,治好我们的社会病,治好我们的城市病。
第二是跨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在GDP到达一定水平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我们能不能跨过陷阱实现我们的梦想?
首先我们要讨论“人”的显影过程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社会开始富起来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出现了富人、高收入人群,出现了中产阶级,但仍有大量的人沉淀在低收入甚至贫困的状态。但仅仅是社会的分野,经济的维度已经没法解释这个社会人群的复杂性了。
第二是社会视角,我们从社会视角看就会有角色和身份的差异,角色和身份的差异会影响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选择。到这一步是不是仍然不够?所以我觉得三联人文城市奖非常高的一个价值,实际上是在于进一步去细分价值观的差异。这一点实际上是媒体特别重视的一个维度,用价值观去区分人群,他们叫分众。但是这一点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理解太少了。对这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需求差异,我们的认识是严重不足的。

《故乡,别来无恙》剧照
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来讲,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有哪些特征?
第一,现在最明显的是,年轻人会选择生活的城市。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工作也好、读大学也好,其实他想的是未来在哪一座城市里面生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年前建立了成都分院,接纳了从北京总院、上海分院、深圳分院、重庆分院的很多年轻人。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组建的分院?他们都说,我们喜欢这座城市。
第二,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就业,由此带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的现象:双城居住,也就是周末的移动和回家。
第三,买房。
第四,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很多年轻人选择城市是在选择子女的教育。我经常说这一代年轻人,你们成长的过程是个“拼爹”的过程。你们一旦进入工作岗位,一旦开始考虑婚嫁的时候,是个“拼娃”的过程。好的学校、好的幼儿园可能是你们做很多决策的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小舍得》剧照
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新增的就业群体,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和父母一起生活。最近我们在深圳、上海的一些科技园区、科学城,发现年轻人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高达75%左右。我觉得在这背后,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孩子们对父母孝敬,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年轻家庭的生活离不开父母的帮助。
所以这些因素怎么在我们的规划、设计当中被给予充分的考虑,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人群细分以后必须要认真去思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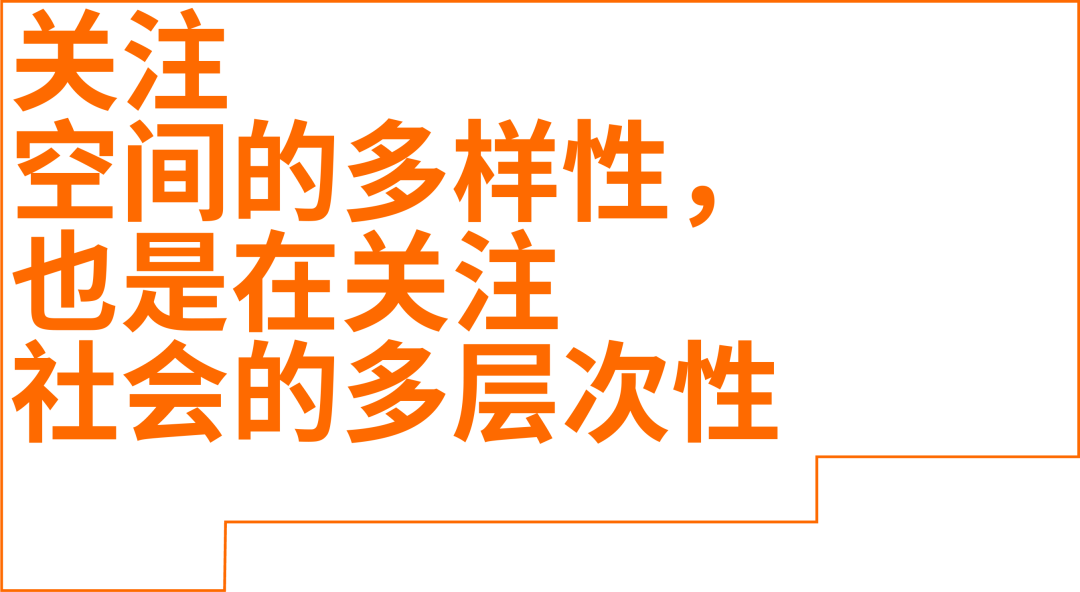
我觉得三联人文城市奖两届都非常关注空间的多样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其实也是在关注社会的多层次性。
我们需要关注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也有美好生活的需要,我经常说野百合也有春天。他们对居住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对经营和生存场所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公共服务、医疗健康这些服务怎么来获得?
讲到城市多样性的时候,我一直在呼吁要关注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空间。桥底下冒出来的空间很有趣,但绝不是富人喜欢的空间。反过来是低收入人群、流浪人群迫切需要的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包括交通的移动,我们怎么去满足它?
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当社会开始富裕起来,人群开始分化以后,很重要的一种需求出现了——精神和审美的需求。其实这也是三联人文城市奖举办的理由之一,如果仅仅讲功能,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不同维度的文化人士来参与。

摊贩在过街天桥通往桥下人行道的楼梯上摆摊
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这样的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当中,人们的文化消费、旅游度假、交往交流、私密独处、健康美容、各种满足好奇心的网红打卡……成了年轻人最典型的生活和消费方式。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消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纵向对比确实很了不起,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增加了50倍,让我们从一个贫困社会、温饱都没有解决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中高收入社会。但是在我们的经济结构当中,消费占比非常低,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或者说增长型政府的一种价值取向。
我们的消费在GDP当中的占比从来没有超过30%。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消费占比占60~80%。所以我们GDP是美国的1/6,但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只有美国的1/12,甚至1/14。

衣食住行的基础型消费在中国消费结构中占较大比重
来源:视觉中国
再看消费结构。美国的消费结构当中,衣食住行这些基础型的消费占比不到50%,但是在中国,我们和墨西哥差不多,80%还是在基础型的消费。
第一,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的演变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从温饱到追求质量,从追求质量到追求品牌,从追求品牌到追求奢侈品,这是一个产品消费的过程。但是产品消费不会无限增长,我们注意到产品消费转向了服务消费,各种各样的服务。再进一步变成了什么?体验消费。所以这样的一个消费链条,作为规划师也好,设计师也好,建筑师也好,我们要去理解它。
第二,我们的消费占比很低,意味着如果中国不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去的话,未来还有巨量的消费增长。

沉浸式线下空间的体验消费成为当下典型的消费方式
来源:视觉中国
另外我们讲交通,人的移动是生存的一种刚性需求。移动的过程受到成本的约束,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讨论空间、讨论场所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供给,一定要想什么样的人、会从哪里来,他能不能承受移动过程当中的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而且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的富裕,费用成本的敏感性在降低,时间成本的敏感性在上升。所以面对交通的提供和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提供,空间区位就显得特别重要。可能在做建筑单体的时候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规划师,你必须考虑它的空间特征。

30万北漂燕郊安家跨省上班
来源:视觉中国
由此我想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居民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四大资本的提升。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物质资本的提升。而人力资本的提升、社会资本的提升、自然资本的提升,这些也都和规划工作、设计工作密切相关。
人力资本的提升,怎么去关注各种人群的生存性需求和发展型需求?社会资本的提升,怎么去考虑不同人群之间公平的获得和空间的正义性?自然资本的提升,怎么去考虑绿色低碳的路径。
第二,除了空间以外,我们必须要考虑场所。怎么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元化的、体验消费的场所?这一点越来越重要了。

我记得上一届人文城市奖的时候,三联让我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人文城市奖的价值,我用了“空间正义、绿色低碳”。今天我想可能要转移到另外一个角度:多样化空间和场所的提供。
关于物质资本或者空间资源的配置,我觉得应当特别重视身份差异、价值观不同所产生的多元化、多类型的需求,通过空间配置手段去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尤其要关注中低收入人群赖以生存的非正规空间的供给。如何满足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尊严和需求?所以城市空间服务供给的正义性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
怎么为不同人群提供多元化的、体验消费的场所?这点越来越重要了。首先要考虑它的功能,各种人群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在哪个空间里面会去消费;然后考虑它的场景,也就是它的偏好,它的审美、它的文化诉求,应该怎么来回应;再次,区位必须可达,必须便利;价格也很重要,要可承受、可选择、可替代。
所以我们讲城市建筑、空间艺术、场所营造,实际上在当下社会当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我记得十几年前深港双年展,基本上是业界的自娱自乐,但如今深港双年展逐渐在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活动。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居民消费的需求来讲,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小众变成了大众,从专业变成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暂停营业的北京天堂超市酒吧
来源:视觉中国
我想再分享两个现象级的场所事件。北京天堂超市酒吧在疫情期间闻名全国,但也由此彻底消失。我觉得这是件很遗憾的事情。这个酒吧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时尚、网红、中低价格、无阶层和身份的差异,是一个符合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场所。我想起了一个英文单词,叫Affordable Luxury(可承受的奢侈品),其实中低收入人群也希望能够享受更加高档次的、甚至是奢侈品的消费。
在之前疫情流调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是从北京的怀柔,通过共享单车、长途公交、地铁,单程用了2个小时、双程用了4个小时去了天堂超市酒吧,在酒吧里逗留了4个小时。这样的人我们一眼就能看清楚,他属于低收入人群,是一个在交通或者移动当中对费用成本极其敏感、时间成本极其不敏感的人群。但是他去天堂超市酒吧是他的刚需,所以他付出的是时间代价。

曾经热闹非凡的中大布匹市场
来源:视觉中国
第二个现象是广州中大布匹市场。中大布匹市场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非正规空间。十几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做了一轮研究,前年我听说广州要搬迁中大布匹市场,我让我的学生又去做了一次论文。我觉得像这样一种极富多样性的产业生态,它实际上是广州整个服装业的总后台。服装业恰恰是广州的支柱产业,这些场所是广州的竞争力所在。
另外一件事情,说起来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去年长沙有个农民自建房倒塌了。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是城市也好,学校也好,严重漠视、忽略了我们大学生的消费需求。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大学附近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生活性服务业集群的聚集,为孩子们提供各种需求。但是我们的政府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的学校更不想掺和这个事,那么只有让农民来帮他解决,最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惨剧。到最后公布的54个死亡人员里面,一大半是在校大学生。所以,当这样的一种供给发生缺位,又会产生另外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思考它?

能够满足学生消费需求的湖南大学校园美食街
来源:视觉中国
城市空间和场所的价值与品质,在于它的包容性、开放性、烟火气、文艺范儿,世俗的、优雅的、本土的、国际的、文化传承的、时尚创新的都应该有。作为规划师,我们怎么用更加专业的方式去理解这种需求,为城市去提供多元化的场所和空间。尤其要关注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小众偏好者的需求的满足。所以规划师也好,媒体也好,关注城市的空间正义和场所多样,我想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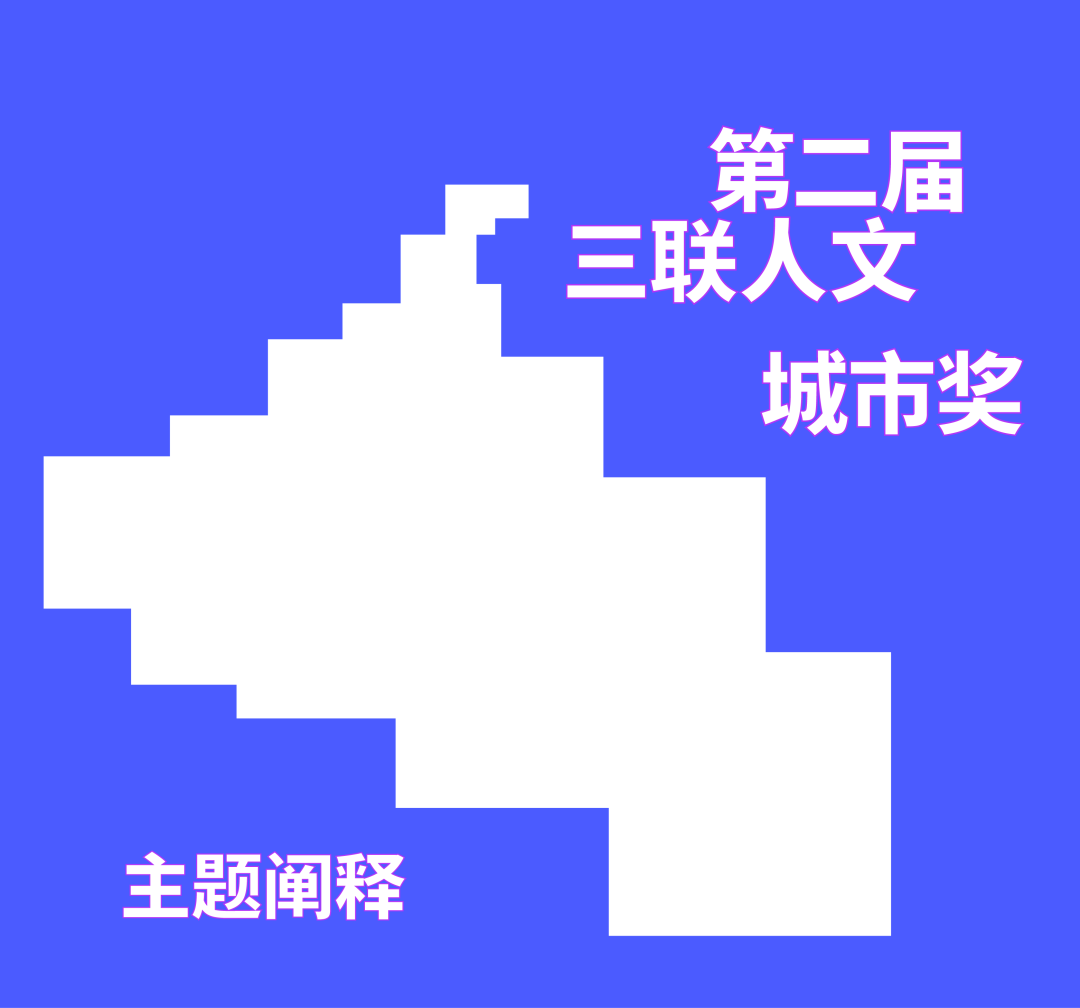
2023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以“流动的公共”为主题,希望在经历了个体感受和情感的变化后,我们能以更主动的观察和发问,在城市中创造出新的、具有能量的公共空间,在多重空间的交叠中发现具有存续性、生命力的公共领域,以此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李晓江:规划中到底有多少“人”的内涵?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规划中国):李晓江:城市里的“人”如何显影?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