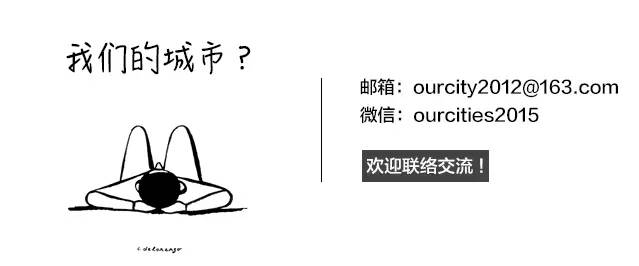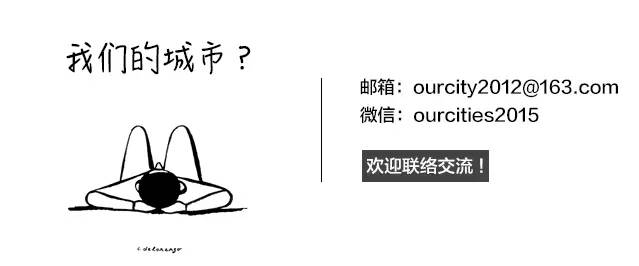2015-07-26
分类:乡土文化
阅读(92) 评论(0)
我从小生活在厦门郊区的小镇。厦门的市区在一个岛上,与台湾金门隔海相望,所以进城也就是进岛。直到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家才搬进市区,正式成为岛民,这已经是新世纪的事情。
上小学之前,小镇上还是一派城乡结合部的景象,我家住在老妈单位的宿舍,就在小镇的外围,楼下不远就是一片田地,上学放学可以不走镇里的石板路,而是踏着田埂抄近道。往东穿过那片田地,就是海边了。那时候进城不是什么快乐的体验,半小时的车程对晕车的我来说已经太长了,水泥路面、高楼大厦、车来车往,哪有田间水塘好玩,可以捉鱼摸虾,也可以偷农民伯伯的地瓜,当然,麦当劳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上小学之后,我就能切身感受到小镇的迅速城市化,东边的田地变成楼盘,海岸线也向外推进了许多,建起高档住宅区,只有西边的老区一仍旧貌。如今再回小镇上的旧家,回想起当时窗外的蛙声,简直恍如隔世。所以我特别喜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是我的故事没有那许多变化曲折,终点也不大可能是上海。
对于我们那儿的人来说,上海是很远的北方。本地人以前把外地人统称作“北仔”,不管来自广东还是东北,只要口音不同,就是“北仔”,似乎自己就是最南方的,这一话语中的自我定位和地理想象,是真自信还是外强中干,不得而知,只是现在几乎没人再用这种政治不正确的称谓,只遗留在一种传统小吃“北仔饼”的名字里,大约与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有关。所以上海对闽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强烈,这与长三角地区上海周边的情况不太一样。就在去年,我阴差阳错参加了一个扬州政府机构来上海办的招商贸洽会,领导致词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扬州虽然没有苏锡常的地理优势,但随着交通的发展,挤近上海的一小时都市圈也是指日可待,对双方只有利没有弊,言辞之间真有点急吼吼的,生怕被一小时都市圈给挡在外面。
后来我到扬州上大学,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很自然地拿扬州和厦门作对比。初到扬州的感觉是,扬州的街道真脏,普通话普及率真低,冬天真冷,阴天真多,但是东西真便宜,每天的伙食费只要7、8块钱,不过,城市的规模和节奏跟厦门还真像,都是小巧玲珑,都是慢性子,亲切得很。有时跟同是闽南人的室友聊起来,都觉得扬州有文化啊,理由并不是那些文化的遗迹,而是:连路边的报刊亭都有《读书》!在家乡,这简直不可想象。
接着又从扬州来到了上海。当然有诸多的不喜欢,它太大,常常让我心疼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它的水有奇怪的味道,不加点茶叶简直越喝越渴。当然也有诸多的喜欢,文化活动的丰富是家乡难以比肩的,更不用说家乡难以见到的打折书。
我对于生活环境一向迟钝,但从朝夕相处,到上了大学以后,半年才见一面,每次回家都得认几遍新开的路和改造的地段,也使我常常以一个外乡人的眼光看厦门。某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越来越像一个“大城市”,尽管报刊亭依然见不到《读书》和《天涯》的影子。高架建起来了,轻轨建起来了,通向岛外的大桥一座接着一座架起来了。坐车经过高架时往外看,真分不出跟上海有什么区别,轮渡也有点像外滩,当然,天是要蓝一些,树也要绿一些。大卖场、大超市、高档商城也随处可见,生活确实方便许多,许多商品也比过去便宜,除了房价。不过也开始堵车了。空气质量指数,从原来福建省九个地级市之首,下降到倒数第二。头顶的灿烂星空,那是再见了,内心的道德律令如何,不知道。
好多人都说厦门的性格是有点小富则安,但似乎并不逆来顺受,07年的PX(我们喜欢读作“劈叉”)事件,是我头一次对自己厦门居民的身份感到骄傲,无论最终的结果是由怎样不为人知的力量所推动和决定,我都一厢情愿地把它视为人民意志的胜利。作为一个有趣的对照的,就在市民们“散步”的终点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楼顶高屋建瓴地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大标语,据说,这用数百万人民币铸成的“为人民服务”,抗得住12级台风。
我也不知道,厦门最好的时候,是还没有到来,还是已经过去了。
城市与城市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的好坏,只凭个人经验当然不能作为评断的标准,我只是想起了一个太常见的被地缘因素所左右了的爱情故事。一对大学时代确定了关系的恋人,男生是闽南的,女生是浙江的,都是我的朋友,毕业以后,来到厦门打拼。也许海岛太小,容不下女生的梦想,男生呢,又觉得女生的梦想之地大而无当,谁都不愿妥协,女生终于只身离开海岛,去了首都,又展转来到上海,男生回了家乡,一个更安放不下女生梦想的城镇,但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鞋都。其中的种种原因细节,外人不得而知,这算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么?所谓爱情,在这种隔阂面前也无能为力。现在我仍然分别跟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之间的未来是越来越渺茫,通讯再发达,救不了人心的疏远。反正两个城市之间这种故事太多,无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