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分会、规划实施分会副主任委员
对“用途管制”似可从狭义和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前者对应于地块尺度和规划许可,后者则可扩展至对广域空间的功能定位。因而,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可谓是对偶关系;其中,全国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通过确定主体功能区和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而对大尺度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出安排,这可谓是宏观层面的用途管控;市级和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承接上位规划的主体功能区等控制要求,通过划定三区三线和规划分区等而制定中观层面的空间功能用途管制规则;市县级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则是在微观层面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用途管制看似仅为规划实务问题,但其背后有学理性问题,涉及价值判断和实证检验——需要规范和经验研究的支撑。例如,如何看待保有十多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以及是否需要控制特大超大城市的空间发展规模?再如,建设用地指标的行政分配是否导致或加剧了区域发展的差异?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发展要素和“土地财政”的认知。引出的问题是财富的源头是土地本身,还是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崛起?客观而言,建设用地供应要对应于实际需求,土地出让价格主要由市场需求决定;实体经济上不去,建设用地没有需求,房地产市场难免低迷;另一方面,能够进入市场交易和具有高价值地块,实际上只占城镇建设用地的小部分;市政设施用地、公共性公益性项目用地、产业类项目用地,或是行政划拨,或是低价出让。
除了上述讨论,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在规划实务或实践角度,还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用途管制的四组关系。
一是“自由裁量权限”与“羁束权限”的关系。建立“多规合一”的统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自上而下编制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行控制要素的“上下传导”,以及划定“三区三线”和确定规划分区等,既是为了改变国土空间管控“政出多门”和开发决策的随意性,也是为了克服地方规划朝令夕改和开发建设的盲目性。新规划体系的建立,无论在宏观还是在中微观层面均大幅减少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限,相应增加了决策和许可过程中的羁束权限。
二是“实体性控制”与“程序性控制”的关系。中央的决策既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也要加强“监督实施”。这包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从而为各类用途管制提供实体性控制依据;同时也要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并形成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从而在程序性控制方面为用途管制提供保障。
三是“许可制”与“清单制”的关系。就微观层面的用途管制方法而言,我国目前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其特点是详细规划本身并不赋予土地使用权益人或建设单位开发建设的权利,但规划行政许可要符合详细规划的刚性控制条件,同时亦可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并可综合权衡各方因素。“清单制”(或称赋权制)是西方区划法(zoning by-law)体系下的主要用途管制方法,即各类用地上的“许可发展”(不需要审批)、“禁止发展”和“需要审批的发展”均在规划文本中明示。其特点是行政透明、权利明确;但规划编制要详尽和准确,并要基于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
四是“建设控制”与“使用控制”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的用途管制是对土地使用的全周期管制。对城市规划管理而言,目前较为重视建设阶段的用途管制;即通过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建设用地的功能和建筑形态施以严格管理。但对建成以后使用阶段的建筑功能改变、形态调整等的管控则普遍不够重视,违法建设和扰民现象屡有发生。实践表明,城市的高品质有赖于高水平的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同时亦离不开全周期的用途管制机制。
2024年第1期 年会学术对话栏目
延展阅读(点击标题阅读)
-
我国土地发展权与规划控制的关系初探
-
城市规划中的“通勤”概念辨析及“通勤阈值”界定探讨
-
国家级开发区的尺度演化与元治理思考——以上海张江高新区为例
-
论《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视域、法律秩序与体系衔接
-
城市规划中的“耦合研究”溯源及误区辨析

空间规划基础理论大讨论:用途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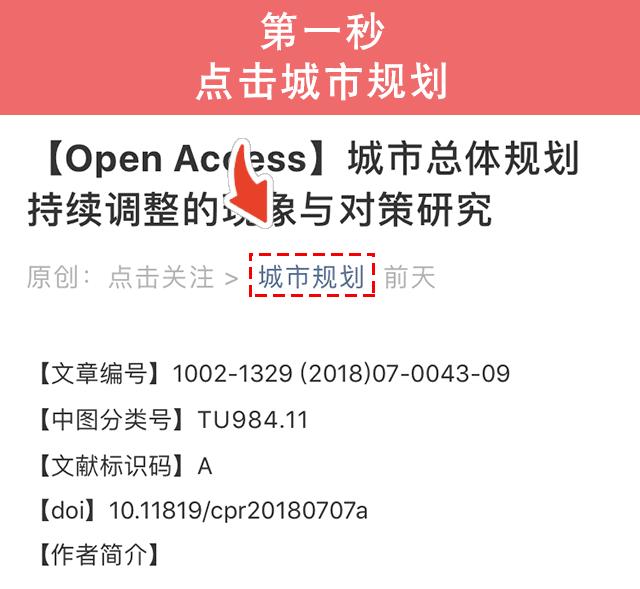
官方投稿网址:http://www.planning.com.cn

关注、分享、在看与点赞,让我体验一下吧~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学术分享】关于用途管制的若干思考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