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驾驶台上,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队员阮飞和金鑫淼时隔近3个月再度见面,高兴地彼此问候:“回来了?你没瘦啊。”“回来了!你也没瘦啊。”
自第一次中山站卸货时一别,见习船长兼机动驾驶员阮飞一直随船开展工作,而金鑫淼作为昆仑站(泰山站)站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极内陆的冰原上作业。如今,金鑫淼圆满完成内陆考察任务,登船再见老朋友。
 内陆队凯旋。付全有 摄
在南极考察中,昆仑站(泰山站)队和格罗夫山队两支队伍要挺进环境更为艰苦的南极内陆开展多项科研工作。由于一起出征、一起凯旋,大家习惯把两支队伍统称为内陆队。2024年12月16日,内陆队25名勇士分别乘坐10辆雪地车出征。“今年我们在距中山站约450公里处分成两路,8个人去格罗夫山,我们17个人前往昆仑站,分头执行科考任务。”金鑫淼介绍,“完成既定任务后,我们两支队伍按约定时间在泰山站汇合,一起返回中山站。”
昆仑站(泰山站)队主要有三方面任务:一是从中山站到昆仑站一路开展冰雪环境调查;二是在昆仑站开展多维度天文观监测研究;三是开展空间物理和空间碎片观测。由于南极内陆是高原,又非常寒冷,每年的现场作业窗口只有夏季短短两个月时间,出发后的两周时间里,队员们得风雪无阻地赶路——更早抵达昆仑站,就能为在站的科考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
“挺进内陆,有经验的机械师团队非常重要。在内陆,没有车辆寸步难行。”金鑫淼说。对此,考察队为昆仑站(泰山站)队和格罗夫山队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机械师。王荣辉就是其中一员。
“我今年是第七次参加南极科考,主要负责内陆队机械车辆的操作、维修和保养,备品备件的管理,以及处理车辆行驶中遇到的紧急情况。”王荣辉说。南极内陆天气恶劣、路途颠簸,车辆负重前行,难免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对今年的一个棘手问题印象深刻。“我们行驶到距中山站约830公里的位置时,6号卡特车靠左边一个轮子的7个螺栓突然断裂了,这个轮子有12个螺栓,突然断了7个。”他说,“如果再行驶的话,整个轮子有可能会掉出来。这辆车还拖着将近50多吨的货物,都是要运上昆仑站使用的科研物资。这个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我当时压力很大。”王荣辉说。
“当时大家正开着车,对讲机里传来队员沈守明的声音——怎么好像听见了鸟叫声?有经验的机械师特别关注声音。”金鑫淼说。内陆深处几乎看不到鸟类,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带着这个疑问,全队停车检查,发现鸟叫般的异响来自6号车。
“我们下午3时左右发现问题,直接就地扎营了。没有配件,车又必须修到能正常行车的程度,我们就一起想应急的办法……先把断的螺栓取出来,再从另外的车辆上拆找可替换的螺栓。螺栓的扭矩非常大,将近700多牛,当时海拔有3000多米,取螺栓的时候又冷、又耗体力。这时整个团队不分科研和后勤了,全部一起上,两人一组轮流取螺栓。”王荣辉说。这样的接力维修进行了8个小时,终于把难题解决了。在“老南极”看来,车在内陆出现故障很常见,修好就行。
“那辆车拉着大量的科研物资,修好后,我们试着开了几天,没再出问题,可以正常运行了,我心里才放下一些。”队员陈超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昆仑站天文场地能源设备的运行维护、安装,以及天文望远镜的维护。
内陆队凯旋。付全有 摄
在南极考察中,昆仑站(泰山站)队和格罗夫山队两支队伍要挺进环境更为艰苦的南极内陆开展多项科研工作。由于一起出征、一起凯旋,大家习惯把两支队伍统称为内陆队。2024年12月16日,内陆队25名勇士分别乘坐10辆雪地车出征。“今年我们在距中山站约450公里处分成两路,8个人去格罗夫山,我们17个人前往昆仑站,分头执行科考任务。”金鑫淼介绍,“完成既定任务后,我们两支队伍按约定时间在泰山站汇合,一起返回中山站。”
昆仑站(泰山站)队主要有三方面任务:一是从中山站到昆仑站一路开展冰雪环境调查;二是在昆仑站开展多维度天文观监测研究;三是开展空间物理和空间碎片观测。由于南极内陆是高原,又非常寒冷,每年的现场作业窗口只有夏季短短两个月时间,出发后的两周时间里,队员们得风雪无阻地赶路——更早抵达昆仑站,就能为在站的科考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
“挺进内陆,有经验的机械师团队非常重要。在内陆,没有车辆寸步难行。”金鑫淼说。对此,考察队为昆仑站(泰山站)队和格罗夫山队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机械师。王荣辉就是其中一员。
“我今年是第七次参加南极科考,主要负责内陆队机械车辆的操作、维修和保养,备品备件的管理,以及处理车辆行驶中遇到的紧急情况。”王荣辉说。南极内陆天气恶劣、路途颠簸,车辆负重前行,难免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对今年的一个棘手问题印象深刻。“我们行驶到距中山站约830公里的位置时,6号卡特车靠左边一个轮子的7个螺栓突然断裂了,这个轮子有12个螺栓,突然断了7个。”他说,“如果再行驶的话,整个轮子有可能会掉出来。这辆车还拖着将近50多吨的货物,都是要运上昆仑站使用的科研物资。这个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我当时压力很大。”王荣辉说。
“当时大家正开着车,对讲机里传来队员沈守明的声音——怎么好像听见了鸟叫声?有经验的机械师特别关注声音。”金鑫淼说。内陆深处几乎看不到鸟类,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带着这个疑问,全队停车检查,发现鸟叫般的异响来自6号车。
“我们下午3时左右发现问题,直接就地扎营了。没有配件,车又必须修到能正常行车的程度,我们就一起想应急的办法……先把断的螺栓取出来,再从另外的车辆上拆找可替换的螺栓。螺栓的扭矩非常大,将近700多牛,当时海拔有3000多米,取螺栓的时候又冷、又耗体力。这时整个团队不分科研和后勤了,全部一起上,两人一组轮流取螺栓。”王荣辉说。这样的接力维修进行了8个小时,终于把难题解决了。在“老南极”看来,车在内陆出现故障很常见,修好就行。
“那辆车拉着大量的科研物资,修好后,我们试着开了几天,没再出问题,可以正常运行了,我心里才放下一些。”队员陈超说。他的主要任务是昆仑站天文场地能源设备的运行维护、安装,以及天文望远镜的维护。
 昆仑站队员维修AST3-2望远镜。纪拓 摄
昆仑站队员维修AST3-2望远镜。纪拓 摄
“负责能源设备和天文望远镜的运行、安装、维护,压力大不大?”我问陈超。
“会有压力,紧张,在内陆出发基地时就开始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上面那些设备是什么状况,不知道到时拿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或者能不能拿到数据,不知道自己带的东西够不够,万一是哪一块儿坏了,配件没有,就很难受。这种心理压力持续到了走的那一天。到走的那天就放下了,反正能干的都干了。”对科研任务“时时放心不下”的陈超,在昆仑站每天平均工作13个小时。他说:“来一次不容易,在昆仑站上一共只有18天的时间,很紧张,一定尽量把设备仪器都搞好。我基本上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左右,反正天都亮着,但是马斌有一天晚上干到凌晨两点。”
“那天正好是走之前的一天,‘惊魂24小时’。”队员马斌感叹,“任务基本完成了,我最后稍微整理一下舱里的网线,不同的计算机插在不同的交换机上。我发现有一个计算机的网口坏了,就换网线,换着换着发现是这个计算机不行了。”
马斌来自中山大学,主要负责昆仑站天文观测条件研究,有两台设备安装在一座8米高的铁塔上。“一台计算机接一台望远镜,铁塔上两台设备的计算机是装在一起的,要把其中一个坏的主机拆下来,换上新的。换完发现另外一台计算机的系统盘坏了,再回去重新做系统盘换上,其间还新出现一些小的故障和问题,那天从下午弄到凌晨2点多,睡了一会又忙了一上午。我安慰自己,走之前发现了问题,比走之后它才坏要好很多。”
经历“惊魂24小时”后,马斌期待着回国查看昆仑站上仪器设备观测的数据:铁塔上的昆仑视宁度望远镜、南极红外双筒望远镜等已正常开展自动化观测了。昆仑视宁度望远镜是证实冰穹A地区有地面上最佳大气视宁度条件的“功臣”,现在正在持续进行长期监测。南极红外双筒望远镜利用昆仑站大气极为干燥的特点,首次从水汽吸收波段观测星空,期待发现大气中有水汽的星星。
“在南极内陆工作中,科研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有些设备可能在国内运行得挺好,但到了极低温环境下,又经过长途运输,一路颠簸,它就会出现问题。”已经参与5次南极内陆考察的格罗夫山队队员曾应根说。
格罗夫山队队员王猛也深有感触:“我们带的装备,对这个极寒天气的预估不足,比如带的发电机来了就启动不了。还有,没来南极之前,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个可控震源仪器的支撑雪橇,但到南极后发现这个雪橇在雪地上压根儿很难拖动。我们设计的雪橇的橇腿太短了,一往前走,里边全部是雪,导致震动部分受阻,且难以前行。”
“这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都能通过队友的共同努力很好地解决。”作为经验丰富的机械师,曾应根对南极现场工作遇到的突发情况很淡定。
“我们大家一起商量,把设备直接放在现成的油囊雪橇上,很好地解决了问题,效率反而变得更高了。”王猛说。这次考察,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冰下湖开展主动源地震勘探工作,为来年冰下湖的钻探选址提供技术支撑。“这次的结果非常好,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极冰下湖进行这种主动源地震勘探,但是由于我们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再加上这个勘探手段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验证,产生了大量的数据。目前,这些数据已经带回国内开始进行深入处理分析。”他说。
王猛今年第一次参加南极考察,最直观的感受是“南极真的非常冷”。“我们在冰下湖地区的时候,每天晚上8点温度计就不工作了,因为温度计只能显示到零下40摄氏度,温度再降也看不出示数来了。在外边站超过一分钟以后,凡是裸露的地方全部都结冰。”
与昆仑站夏季没什么风、多晴天的天气相比,格罗夫山和冰下湖地区常年刮大风。“前期的气象资料表明,在冰下湖工作区域,这里一旦出现坏天气,这个坏天气就会持续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真正留给我们干活的时间,当时预计只有7~10天,科研节奏非常紧凑。”王猛说。在此情况下,只要有好天气,格罗夫山队队员们就一天24小时连续作业。
“有一次早上起来就做任务,那天格罗夫山的天气窗口不好,飞机没法降落运送人员和设备,只能第二天改降落到泰山站。做完科研任务已经是下午,我们就立即从格罗夫山开车赶去泰山站,170多公里开了十几个小时,抵达后马上平整雪面跑道,为飞机降落做准备,当天下午接到人员和设备后就执行科研任务……那次30多个小时没睡觉,一路开车一路跑都没停。当时4个人开两辆车,累了就轮流休息,赶在窗口期把科研任务完成了。”曾应根说。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那是非常渺小的,它随便刮个风、吹个雪你都受不了。”曾应根感慨。如此艰辛的环境,为什么还来了这么多次?他回答:“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在这么一片纯洁的大陆上,有这么一帮非常优秀的队友,共同去完成很多挑战、很多任务。很多时候,你不会感觉自己一个人在干活。比如我在修车,那风吹得很冷,队友帮不上忙,但是他们在旁边帮你挡风,心里感觉一下子就不那么冷了。”
队员挖雪当水用。马斌 摄
“南极最吸引我的地方除了独一无二的风景之外,还有在这边认识的很多人,感觉进内陆队就像多了20多个家人一样。我是这个队伍里面年龄最小的,一直被关怀被照顾,就是像家人一样。”昆仑站(泰山站)队的李纯青说,“比如队长金鑫淼、机械师姜华,一路上帮助了我很多,队友们都很可靠。在我布设CCR棱镜阵列的时候,需要前后跨越大概几百米插杆子,然后左右各跨越几百米插杆子。基本上是我走到哪,金队就开着车跟着我到哪,很体贴。”
“有一天去布设CCR棱镜阵列,纯青把手指冻伤了,我开的雪地车就在旁边,让他冷了随时上车。这小伙子感觉冻了没提出来,还咬牙坚持把活干完,认真嘛。”金鑫淼说,“纯青一个人肩负着好几项任务。我们晚上8点扎营,他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干活干到12点多。我们能协助的都协助了,但是像在电脑上设置参数、整理数据那些,别人帮不了。”
“布设CCR棱镜阵列需要在外面操作一个类似手机的仪器,我如果戴了手套的话没办法操作。当时又是在昆仑站,零下30多摄氏度,又有点风,在外面干了两个多小时后回去有一只手指就没有知觉了。”李纯青不好意思地说。
 队员展示钻取的冰芯。金鑫淼 摄
队员展示钻取的冰芯。金鑫淼 摄
2025年2月11日,内陆队凯旋。回望那58天的内陆科考时光,队员们告诉我,内陆很冷,开车很累,工作压力很大。然而,南极很美,与伙伴们一起并肩拼搏、为国科考,很充实、很温馨、很光荣。
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特派记者:曹悦妮
文字编辑:戴路
新媒体编辑:刘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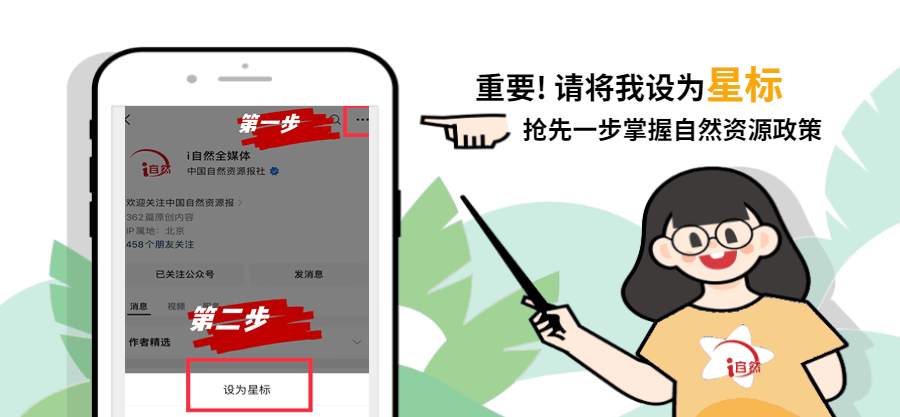

转载请在醒目位置标注来源:i自然全媒体
i自然投稿邮箱:mnrnews@163.com
电话:010-6804761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i自然全媒体):南极内陆科考趣事多

 内陆队凯旋。付全有 摄
内陆队凯旋。付全有 摄 昆仑站队员维修AST3-2望远镜。纪拓 摄
昆仑站队员维修AST3-2望远镜。纪拓 摄

 队员展示钻取的冰芯。金鑫淼 摄
队员展示钻取的冰芯。金鑫淼 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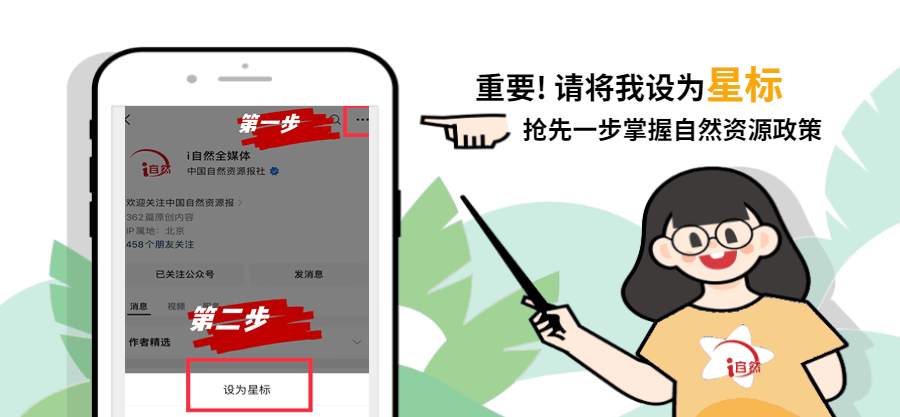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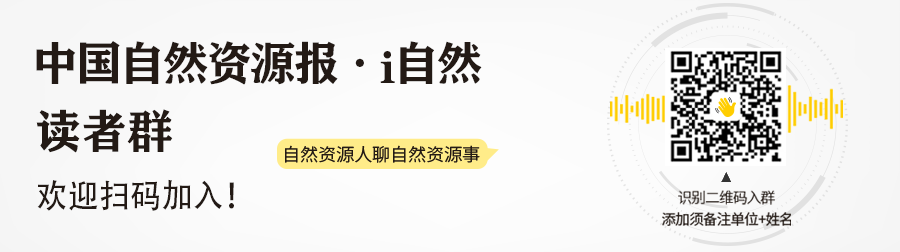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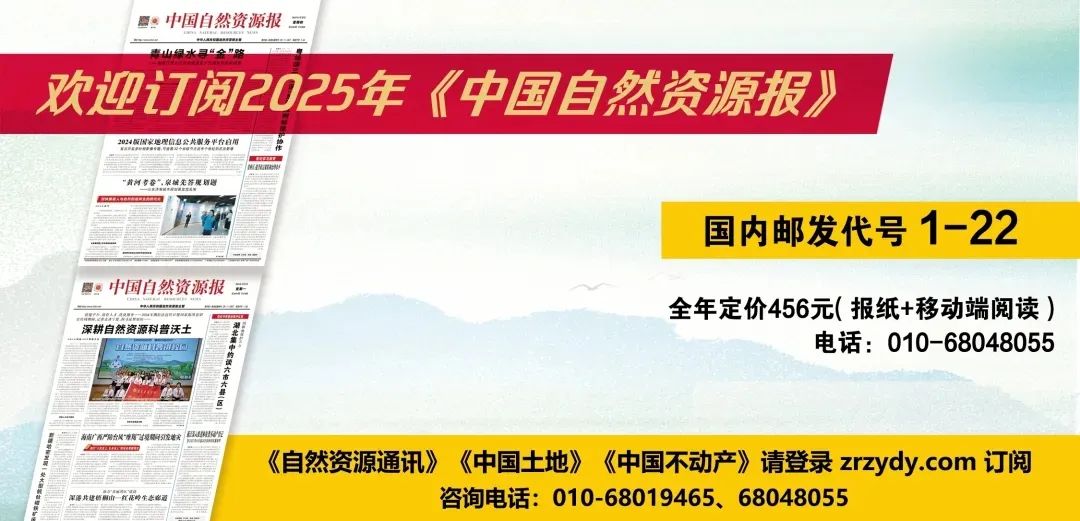



 内陆队凯旋。付全有 摄
内陆队凯旋。付全有 摄 昆仑站队员维修AST3-2望远镜。纪拓 摄
昆仑站队员维修AST3-2望远镜。纪拓 摄

 队员展示钻取的冰芯。金鑫淼 摄
队员展示钻取的冰芯。金鑫淼 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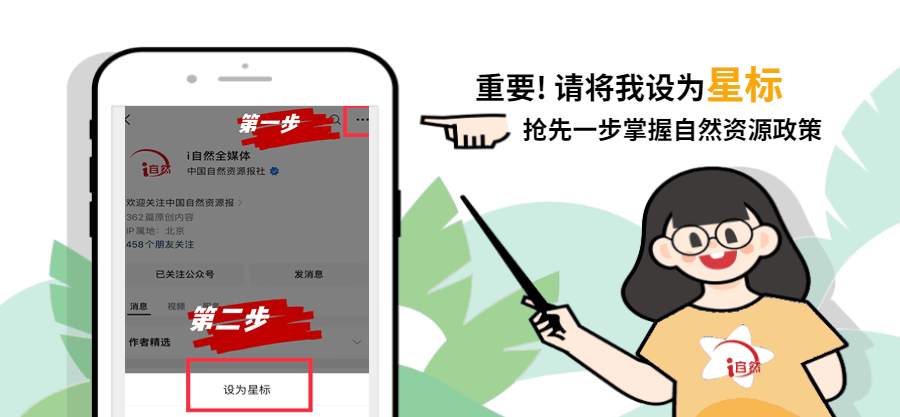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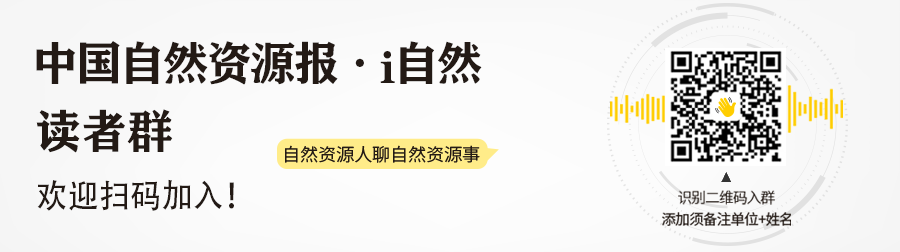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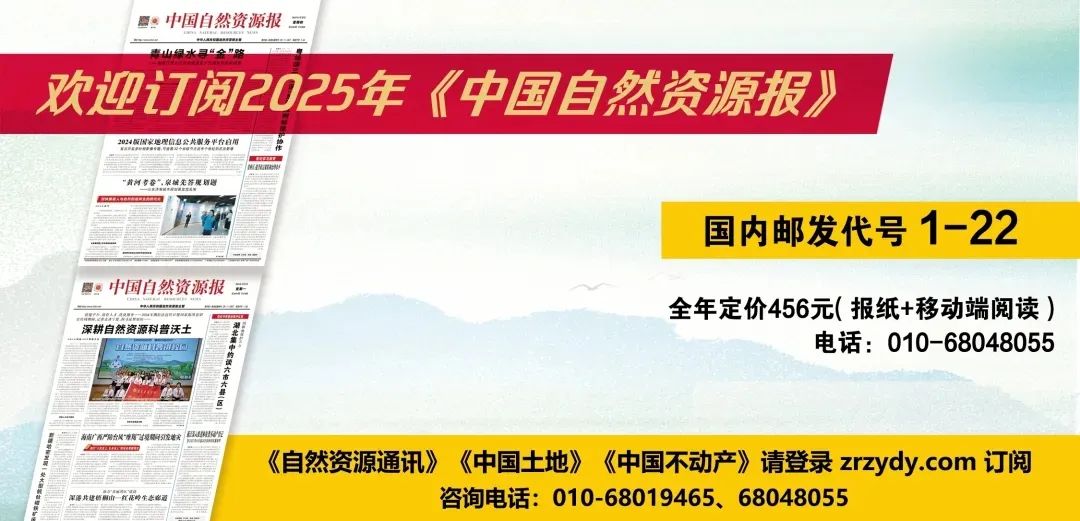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第九章《基于手机数据的城市空间研究》|《大数据与城市规划》2025春季学期 MOOC 上新啦!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如何搞定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审?从论文、专利、标准、课题、报奖、创新平台来看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今晚开课】社区生活圈评估预测模拟方法与实践丨城市数据派 第二章《基于城市人工智能的城市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城市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2025春季学期MOOC上新啦!
第二章《基于城市人工智能的城市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城市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2025春季学期MOOC上新啦! 【报名倒计时2天】如何申报创新平台?以工程研究中心及博士后实践基地申报实践为例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2天】如何申报创新平台?以工程研究中心及博士后实践基地申报实践为例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2天】利用社区、公服POI数据对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2天】利用社区、公服POI数据对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省市级课题申报与结项实践及科技奖励申报实践经验分享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省市级课题申报与结项实践及科技奖励申报实践经验分享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社区生活圈现状评价:如何将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
【报名倒计时3天】社区生活圈现状评价:如何将住区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分类?丨城市数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