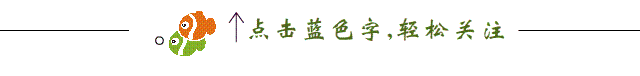
解决雾霾离不开花钱。假设国家突然把治理全国性的雾霾现象摆到甚至高于经济发展的地位,投入GDP的三成以上,相信连绵的蓝天白云指日可待。显然如此高额成本是不经济的,贫穷和动乱的危害甚于雾霾。那么界限在哪里?
这种算总数的表述背后包夹诸多方面的因素,最终产生的结果可能令所有方都不满意。比如,综合考虑河北钢铁产业的就业支柱地位和北京、天津居民的健康损耗两项因素,合理的界限可能在于有限关停张家口的高炉,并打击唐山的黑钢厂。措施很难彻底,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不均衡。所以后果肯定两不讨好:河北继续出血补贴京畿地区的环境,但首都居民发现PM2.5 的指标值仅仅从500下降到350. 经济上的最优解并不一定对应着政治上的最恰点。
更现实的情况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河北省委将代表本地区利益与中央细细推敲每一项限制性措施的力度,争取将省内综合治理难度降低。而北京地区的利益代表们从相反的角度出发,通过中央官员的感同身受、国内外重大会议的蓝天要求、城市中产阶级的互联网集体诉苦等渠道提取反击力量,推动其他地区的协调治理。政治博弈的结果可能是短期“APEC蓝”+中长期雾霾绵延结合。
所以,年初红遍网络的柴静《苍穹之下》中,解决方案中为人所诟病较多的一点就是“避重就轻”。纪录片在详细分析后给的出路是大家减少私车出行、举报身边污染源等“细枝末节”;而对于如何从政治决策中处理能源结构、环保地位、央地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则毫不涉及。
然而,从长远看,政府的决策绩效有赖于政府-公民双向互动,而不是政府自己的攻守转换。互联网公开传播的纪录片很难穷尽这里面的可能性,能够给出开头就算不错。“细枝末节”的引申,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新型政治决策过程。
既然是自下而上,那么区分清楚不同人对于雾霾的成本感知就是第一位的。柴静由于女儿的健康原因奋起而战,恐怕不是当场补贴五万块钱能让她满意的。上班族带着3M口罩坐地铁去公司,要求的补偿恐怕至少要比口罩和空气净化器价格要高。火电与供暖企业如果能够自己主导定价,愿意为高排放支付的罚款不可能高于全部利润。让河南农民放弃田地秸秆燃烧的费用,得在来年补偿性化肥开销和长期土壤板结成本的总和以上。吸雾霾的和制造雾霾的,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价格。过了这条线,行为就会发生变化。
自下而上的难点在于如何组织集体行动,促成切切实实的改变。市场是一个好机制。比如,已经实施的企业排污权试点机制中,所有公司购买排放废气的指标,交钱给环保部,作为治理基金。如果指标用不完,可以卖给不够用的企业,价格自己商量。等大家你来我往地把这个价格琢磨明白了,基本上就能看出来环保部放出的这一批指标是不是整体够使:太少则价格太高,太多则价格太低——与股票类似。市场通过价格形成有效指引后,反过来让所有企业要求环保部下一批指标发行中合理调节数量和价格。
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是交易达成的根本。就好像如果一只股票所有人一律看涨,那么也就没有了卖家。捍卫清洁空气权的城市中产阶级是一拨人,代表皖北秸秆焚烧权的农民是另一拨人,前者显然比后者个体力量大,组织资源多。如果只有都市白领发出声音,那么皖北农民可能就要吃亏。目前基本情况也就是如此。在政府和市场都缺位的情况下,农民自发成立NGO来保障权益的做法,就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
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后,最终来到政治决策过程面前。这时候的对决具有清晰的特征,避免了“自上而下”决策中所特有的各说各话。双方的事实都清楚,彼此也认可,分歧就在于价格。石家庄和天津的市民诉求为华北农民和重工业领袖所充分感知,反之亦然。建立在充分沟通基础上的决策,即便是两不讨好,一般也很难造成社会分裂。
雾霾本身的存在,显示了此前政治、经济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裂痕,牵扯到的是社会治理有机体的全部,因此难以通过个别部委或者少数阶层的独立行动来解决。对于能源、产业和经济地理结构调整这样的重大任务,如果不能够有效集结力量进行对抗,那么“哭大声”的永远是体制内拥有话语权的那帮人。经济学的作用在于指明集体行动的渠道和方向,边界在于政治裁决。但如果经济的问题掰扯差不多了,政治的问题也就好办了。
齐岳,《北京青年报》《北青观察》长期供稿人,曾译著多本知名财经类著作
本文刊登于我院合办杂志《凤凰品城市》2016年1月刊。
-
JUP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jupchina),如有任何需要请通过后台留言或者发送邮件至caoxc@jupchina.com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