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2期
从图像的重影看跨文化艺术史
(下)
李 军
3. 《跨文化的艺术史:论图像及其重影》一书及其构成
该书的写作,孕育于笔者前一部著作完成的过程中,可谓深深投下了自身学术生涯的身影。
2014年底,在《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提到,该书的写作不仅整整持续了十年,而且在写作的后期,自己的学术兴趣已“愈来愈从本(该)书关心的博物馆与艺术史的相关问题,转向欧亚大陆间东西方艺术的跨文化、跨媒介联系”;这也意味着作者逐渐从上一本书的写作,转向本书内容的写作。这一过程同样持续了十年。
跨越东西: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
第一编“跨越东西: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包含了同一主题的七章,集中探讨13-16世纪欧亚大陆两端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艺术交流。所谓“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是该书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的新概念,意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还是一个在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是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共同创造了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艺复兴。本编的研究为论证这一主题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作为该书的开端,第一章在书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本是作者于2002年起研究西方艺术史的案例之一,是作者2008年发表的一篇长文《历史与空间——瓦萨里艺术史模式之来源与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教堂的一种空间布局》中的部分内容。它所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故事:以中世纪晚期西方教会与方济各修会的冲突为背景,透过对意大利阿西西方济各会教堂的空间、方位、图像程序的细腻解读,揭示出教堂之所以朝东和东墙图像配置的秘密,即对方济各会内部所盛行的激进观念,在图像层面上进行了隐匿的表达。
从第二章开始,该书的论调有了重大的改变。针对同一个对象,它试图开始讲述一个与前一个故事迥然不同的故事,一个与真实的东方息息相关的故事。它把图像与空间的关系,放置在同时代欧亚大陆更为宏阔的语境——蒙元帝国所开创的世界性文化交往和互动网络——之中,从而发现,具体的建筑空间和图像配置犹如壮丽的纪念碑,它们以最敏感的方式,随时随地铭记着遥远世界发生的回音。例如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西班牙礼拜堂中的图像配置,即讲述了多明我会在向东方传教中的自我期许和历史使命。最后还揭示,甚至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最大的骄傲——布鲁内奈斯基的穹顶,同样镶嵌在与东方(波斯与中国)深刻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往的语境之中。
长期以来,主流地图学界把地图制作看作是以数学和定量方式“再现”客观地理的一个“科学”过程,这一理路近来日益遭到当代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正如“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的含义在文化研究那里已经由“表征”代替,意为它“不是单纯的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一种文化建构”。这种“文化建构”在地图学上不仅能够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和“地图(绘制)中那些主观性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呈现为一个有关知识生成、传递和演变的客观历程。
第三、四章以13至16世纪的世界体系为背景,聚焦于十幅(四幅中国、六幅西方)现存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地图。一方面揭示它们之间种种隐秘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更借助于艺术史方式,追踪这十幅世界地图在制作层面上,其图形形式之间所呈现的一个加减乘除、辗转流变的跨文化过程。
第五、六和七章是围绕着同一主题的一组研究。它们从方法论上质疑了西方主流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存在的两个根深蒂固的成见,指出其一方面过于强调图像的政治寓意而忽视了图像表象的自身逻辑,另一方面则始终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把文艺复兴解读为西方古典的复兴。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意大利锡耶纳画派代表人物安布罗乔·洛伦采蒂的主要作品《好政府的寓言》进行了全新的研究,通过揭示出它与中国南宋楼璹《耕织图》及其元代摹本在具体细节和构图上的全面联系(第五章),用大量细腻微观的相关图像分析(第六章),并围绕着丝绸生产、贸易和图像表象的复杂实践,把它还原在蒙元时期欧亚大陆的广阔背景下,进而讲述一个闻所未闻的关于文艺复兴的故事,一个丝绸之路上由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参与创造的跨文化文艺复兴的故事(第七章)。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该书第一编通过横跨欧亚大陆的大量图像、图形和图式乃至技术的研究,证明流俗之见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丝绸之路”与“文艺复兴”之间,那些界限分明的畛域并不成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丝绸之路”与“文艺复兴”之间十分频繁的交流互动、前后相依和彼此共存。“东方”与“西方”就像两个地平线上矗立的巨人,随着日出与日落,在彼此身上都投下自己的影子,以及影子的影子。
跨越媒介:诗与画的竞争
第二编的五章以“跨越媒介:诗与画的竞争”为题,则将探讨跨文化艺术史中的另一个层面。所谓“媒介”,传统上一般理解为艺术作品的物质载体。其相关西文表述有“Medium”(媒材)、“Matter”(质料)、“Material”(物质)或“Materiality”(物质性)等等。从古希腊肇始的西方思想史,通常会把“形式”与“材质”对立起来。如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四因”说,其第一、第二因即“形式因”和“质料因”,二者之间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艺术创造,则往往被理解为是艺术家将“形式”(Form)赋予“质料”(Matter)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媒介”不是仅仅具备被否定的、负面的存在,就是迹近透明,成为观念或内容的传声筒。但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古典符号学揭示了每一个符号先天拥有的二重性:它在指涉他者的同时,也反过来指涉了自己。“媒介”亦然。每一种艺术“媒介”在表述艺术“形式”的同时,也表述了它自己。
换句话说,当某种“形式”从一种“媒介”向另一种“媒介”转移时(例如某书法家的书丹被刻工刻在碑石上),其“形式”会在与新“媒介”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意义(碑文的“金石味”)。这种新意义的产生并非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艺术家(或工匠)的主体性(“艺术意志”)与新“媒介”的物质性(“艺术潜质”)相互磨合与调适的结果。这种新意义还会在进一步的“媒介”转换中辗转流变,甚至回馈给原先的“媒介”,创造出一种新的流行风格(如书法中“碑学”)。从表面上看,艺术“形式”在一次又一次的“媒介”转换中,犹如影子生产影子,创造出一层又一层的重影。但每一层重影并不虚无,而是具有物质性的存在。一方面是新“媒介”的物质性为新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潜质与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艺术意志”为这种潜质与可能性之实现,提供了非此不可的能动性保障。二者之结合,即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媒介竞争”——实为实现于“媒介”层面上的“艺术意志”的竞争——的现象。
笔者曾在《可视的艺术史》一书中,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概括为“跨媒介艺术史的研究”。鉴于“媒介”之间的差别和转换仍然是一种物质文化的现象,故笔者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艺术史的新诉求属于“跨文化艺术史”的范畴。
第八章试图探讨“诗”与“画”之间的媒介竞争。它以释读一张宋画(传乔仲常《后赤壁赋》)为鹄的,通过分析画面中由分段题写的赋文(诗)与九个场景(画)之间所构成的张力结构,试图还原画作者在使画面的视觉意蕴与原赋文的诗意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构造与意匠经营。
第九、十两章同样着眼于诗歌与艺术的关系。但这次聚焦的对象,是建筑师梁思成在林徽因影响下产生的建筑史新观念(从“古典主义”转向“结构理性主义”)之非建筑、非建筑史起源(第九章);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契机,是一种“诗性的逻辑”在林徽因那儿的生成与生效,发生于在她深受诗人徐志摩影响而成为一名诗人、随即后者戏剧性地猝然离世之后的时刻……因而,与流俗之见大相径庭的是,笔者认为,与其是建筑或建筑学专业领域的事实,毋宁更是与建筑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诗歌和文学的胜缘及其跨媒介的转换生成,才是理解林、梁于1930至1932年间建筑史观念发生重要变革的一把钥匙(第十章)。这种“跨媒介艺术史研究”的诉求,更充分地体现于本编的最后两章。
第十一、十二两章通过穿越沈从文的文学、绘画和学术三方面的跨媒介文化实践,试图对作家沈从文的“转业”之谜,提供一种基于图像阐释、文本细读和历史考证的新阐释和新论证。沈从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喻成是一次针对“工具重造”的运动,他本人在工具方面的变革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一变革以沈从文在1934年用彩色蜡笔作画为标志,伴随着人生中的婚外恋情、文学创作中的色彩实验、战后政治评论中的审美乌托邦,中间贯穿着一条“图像转向”的红线,并最终导致沈从文晚年向“形象历史学家”的转型。这一“图像转向”和一个堪称“艺术家”的沈从文,将成为理解前期“作家”沈从文和晚期“学人”沈从文的桥梁。而其中透露的内在逻辑历程,存在着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纷争的哲学深度和意蕴。
探寻方法: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
与前两编的个案研究不同,该书的最后一编是对于艺术史方法论的探讨。该书所理解的艺术史方法论,与其说属于思想史范畴,毋宁更属于艺术史研究者的实践范畴。对艺术史研究者而言,前辈和同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经验,同样构成了艺术史学本身的重影。但该书并不想因此而陷入抽象的理论思辨。《可视的艺术史》一书的主旨在于,博物馆及其展览陈列是一部空间化的“可视的艺术史”;而在该书中,对艺术史的思考首先表现为对“可视的艺术史”即展览的思考。
开始的两章围绕着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至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开。该展览已于2018年1月23日-5月7日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由笔者担任主策展人。展览本身在学界和博物馆专业领域同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在于,展览在中国首次尝试了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展览陈列、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最近二十年来,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开创了现代文明新纪元的传统观念,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新研究的挑战。第十三章主要介绍了该次展览的新理念,即展览如何基于对丝绸之路和文艺复兴的新阐释,以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学者独立策展的方式,向全球48家博物馆征集了250余件(套)文物和艺术品;如何通过呈现极为丰富和充分的证据链条,以构成全球学术界反思文艺复兴和丝绸之路的新思潮中最新的一波浪潮,标志着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一次华丽亮相。同时也以实物证据的形态,与该书第一编的案例研究形成了呼应之势。
第十四章则进一步探讨了艺术展览的研究与策划等问题。如果说展览是一部“可视的艺术史”,那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展就是一部“可视的跨文化艺术史”。从研究层面,以丝绸为例,区别于“全球艺术史”或“比较主义”的思路,这部“跨文化艺术史”提出了应该把中国丝绸的传播史和中国丝绸在当地的影响史结合起来的新视野,尤其提倡研究东方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装饰图案是怎样逐渐改变了意大利丝绸的制作和审美,并对文艺复兴发生影响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国艺术史和西方艺术史就可以先天地重合在一起;它们并不是截然断开的,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策展层面,提倡同时设计内容和形式。即一方面在内容上增强展览的故事性和体验性;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则借鉴了中世纪抄本插图的方式,努力使档案文献视觉化、图像化,做了一系列中国展览史上鲜见的尝试。
第十五、十六两章则属于同时代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研究。前一章依托西方哥特式教堂研究史上五次范式转换的历史与逻辑过程,对于法国艺术史家罗兰·雷希特以“作为视觉体系的大教堂”为着眼点的“视觉-物质文化”维度,进行了具体的评述。后一章则通过阐述另一位法国艺术史家阿拉斯的艺术史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为了与艺术作品的微妙性质相适应,细节和眼睛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一章借助艺术史家郑岩、汪悦进合著的《庵上坊》(20)一书,探讨了“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史”的可能性。这种“艺术史”以“艺”、“术”、“史”作为三项指标,是一部围绕着艺术作品(“遗物”或“遗迹”)而展开的“遗物或遗迹之学”;是一部适应艺术作品之“微妙”性质的“微妙之学”;是一部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所有“技术”的“方技之学”——一句话,一部“有限的总体史”。即一部涉及到人类同时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全部领域(从材料、工具、工艺到观念、宗教与信仰;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同时又聚焦于物质形态之艺术作品的生产、流通、接受和传承的具体历史。
至于该编的标题,它来源于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一段话,笔者认为它既符合该编的意旨,故征引在这里:
在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极隐秘和难以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和喜欢。
2018.4.14
本文为李军即将出版的新书《跨文化的艺术史:论图像及其重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的导论。
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6至1997、2002至2004年、2011至2012年和2013年,分别在巴黎国际艺术城、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哈佛大学本部和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从事文化遗产和跨文化、跨媒介艺术史研究。2014年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已出版专著《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希腊艺术与希腊精神》《“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身份与性别》;译著《拉斐尔的异象灵见》《宗教艺术论》等;即将出版新著《跨文化的艺术史:论图像及其重影》。策划大型国际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及“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
相关链接:
理解中世纪大教堂的五个瞬间:《信仰与观看:中世纪大教堂的艺术》译序(上)
理解中世纪大教堂的五个瞬间:《信仰与观看:中世纪大教堂的艺术》译序(下)
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一)
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二)
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三)
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四)
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与楼璹《耕织图》再研究(五)
美术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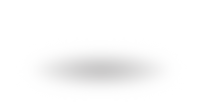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