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梦的具现,
有时是美梦有时是噩梦;
城市是真实的人生,
不论你爱亦或不爱;
城影之间,掌一盏灯。
——《城影之间》序
作者:黄璐(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众终究是抵不过娱乐与鸡汤的梗。第89届奥斯卡少了死撑的小李子的励志故事之后,明显后劲不足。若不是颁错奖这一史上第一大乌龙,怕只会是更少人关注到本届的最佳影片《月光男孩》。

一部黑人影片,不管影评人如何盛赞它为21世纪的“黑人电影”、“后种族电影”,对于多数国人而言,共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2015 年,在《NeuroImage》上刊登了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所论证的那样——该校科学家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在中国大学生观看亚洲人和白种人脸部图像时对他们大脑进行了扫描。相比于看到白种人的痛苦的表情,亚洲学生对亚洲人痛苦表情的同情反应更强烈。种族间的共情缺口问题可是有神经学依据的。
撇去种族问题不谈,对自我的认同以及对他者的共情,其实,影片里一直都有。在影片里,自由城(Liberty City)少年Chiron来自单身家庭,母亲吸毒,他遭遇校园霸凌,他与同性初尝禁果,最后,自己也成为了一名毒枭。Chiron在“死基佬”的问题里迷茫,在“小不点”的问题里迷茫,在母亲吸毒的问题里迷茫,在毒枭的世界里的迷茫……从小到大,沉默寡言的他反复被人追问“你是谁?”。幸好,他偶遇到胡安担当起了类似父亲的角色,这个满身腱子肉的大毒枭告诉Chiron“月光下的黑人看起来是蓝色的”,他对着他说“总有一天你要决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别让其他人给你做这个决定了。”

《月光男孩》是剧作家塔瑞尔·麦卡尼Tarell Alvin McCraney(他的舞台剧本原名《月光下黑男孩看起来是蓝色的》)的童年经验。采访里,他说,“我在 2003 年的夏天写下初稿。当时我的母亲刚刚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我希望写下自己在迈阿密成长的一种诗性叙述。”

这种诗性的叙述里,没有底层生活的苦大仇深,也没有脸谱化的黑人模式,有的就是细腻而个人的成长叙事,有血有肉、有迷茫有脆弱、有无奈也有温情的充满张力的故事。虽然,如果你非要标签化它们的话,“贫民”、“校园霸凌”、“同性恋”、“毒枭”……每个词都具有炸裂传媒眼球的能量,但是,影片偏偏不从这些“十万+”角度出发,有种族但无歧视,有同性恋但无性向歧视,只是安静地刻画一个人的人生。
凑巧的是,在看《月光男孩》的时候,正好在看涂子沛的《大数据》,开篇就是奥巴马的励志故事。书中说,奥巴马一直在迷茫中长大,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了解美国文化,作为一名黑人,他似乎又不属于那个群体。”又说,奥巴马“刚上大学时无所事事,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甚至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谁都知道,这个迷茫的故事有一个happy ending:他开创了历史,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而成功的原因在于,公共生活。“没有别人为他提供的帮助,他走不到今天,但没有他自己试图去帮助别人,为社区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更不可能知道人生的方向。”

如果不是看到塔瑞尔·麦卡尼Tarell Alvin McCraney的专访,根本不会相信,这部影片的言外之意竟然与奥巴马的故事如出一辙。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Chiron” 被心理学家荣格视为“受伤的治愈者”,塔瑞尔·麦卡尼Tarell Alvin McCraney说,“(Chiron)部分是无法疗愈的,他的工作是寻找办法治愈别人。我认为这很重要,在理解男性特征,尤其是黑人群体的男性特征时,我们记得的是受过的伤害、别人如何冷漠无情,而不是自己也有能力宽厚待人。我虽然很不喜欢集体的场合,但内心依然保有着希望帮助别人的一面。很多时候,我会感到心灰意冷,但只要我可以尽量帮助更多的人,我的任务就达成了。”
影片内外,迷茫的出口都在更广阔的公共的城市社会,正如,“巨婴”们需要在公共事务中唤醒自己,正如,抑郁患者需要在公共接触中治愈自己一样。城市里的每个微小的自我,都在从受伤者到受伤的治愈者这条路上慢慢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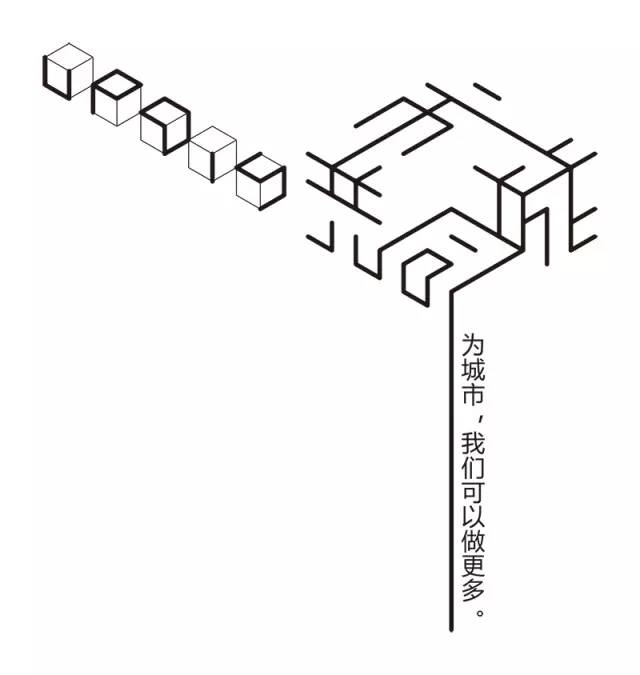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