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现实和世界历史被如此泾渭分明地描述时,人们的内心总是得到更多的慰藉,生起更多的同仇敌忾和选择的决然。然而,邱园却在说着另一个版本的更加眼花缭乱的全球化故事。这是一个搅拌着科学、审美、自然、金钱、权力乃至暴力的故事,更是一个全民参与、充斥着描述归类、价值重估和审美判断的故事。
一直想要写写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不是因为它世界闻名,而是无法忘记它带给我的特殊震撼。
一度我怀疑这震撼是因为没做功课,光听说茶花开得艳,便兴冲冲买了票去看,以至于对这座皇家园林的历史,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不过,等到回来查阅网页,便发现震撼和偷懒无关。这座皇家植物园,在中文里被雅致地称为“邱园”。各大旅游网站和驴友日记对它的介绍,也颇为一律。从1759年奥格斯汀公主的一所私人植物园,发展扩建成如今规模宏大的皇家植物园,人们毫不掩饰对其悠久历史和丰富馆藏的夸赞。而所有的赞美之词,都以一段中规中矩的邱园历史为前提。比如,百度百科中的这一段:“早在1772年,植物园的管理者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收集植物,并开始了植物在经济、科学和欣赏领域的研究。甚至已经有使者到达中国香港、台湾、福建、广西、云南、京津地区采集。”

▲ 绿盒子:邱园植物及真菌收藏

▲ 阅览室
于是,反而我有些庆幸自己的懒惰。倘若事先读到这些夸赞之词,一入邱园,便容易先入为主,情不自禁地以人类自居,抒发起对植物的赞叹来。毕竟,在如此平和的植物收集史中,除了做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类”之外,别无选择。可倘若没有这样的描述打底,如我这般一头撞进邱园,所见所闻又会如何呢?
毫无疑问,邱园极美。它的美,有一部分和伦敦各大公园一致,舒朗的天空,开阔的景致,明丽的色调,悠闲得仿佛主人一般的水鸟,和那一股扑面而来的貌似疏于打理的荒野之气。可以说,这些是伦敦各类公园都有的基本特点。就此而言,作为当年世界工业革命的核心城市,伦敦在城市内部保留和维护自然的能力,既超过了早早开发的古代城市,也优于那些在后发道路上疲于奔命的现代城市,尽管这样的保护,往往成为伦敦人抱怨当下住房危机的一大由头。不过,倘若只是如此,邱园是无法给人以震撼的。因为这样的自然之美,只是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加上英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占得先机后特有的“余裕”使然。

▲ 伦敦海德公园与城市建筑群

▲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也许你会说,邱园的美,最直白的表现,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奇异植物济济一堂、其乐融融的样子吧。这个解释自然不错。可现如今,哪个大城市没有自己的植物园,哪家植物园又缺少收揽珍奇的实力和便利。更何况,对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来说,一切远方的事务,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所在。仅是收集罗列世界奇珍,让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地接受游客检阅,恐怕已经很难构成令人震撼的美感。
也因为这样,在邱园的我,越走越疑惑。邱园如此之美,可对我这样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它究竟美在哪里,以至于让人有一种久违的震撼之感?直到走进邱园内的玛丽安诺斯画廊(Marianne North Gallery),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震撼,方才具体起来。
那时画廊里正在举办英国女植物绘画家Margaret Mee(1909-1988)的画展。据介绍,47岁之后的她,先后组织了13次深入亚马逊河流域的勘探,记录和绘制那里的珍奇植物。由她发现和命名的植物,便有九种之多。而在画廊的尽头,更有一个不大的房间,上下两层,装修得并不奢华。一色原木的墙壁上,挤满了另一位英国女画家Marianne North(1830-1890)的近千幅油画。一眼望去,油画的挂放,似乎没有规律可言,一幅紧挨着一幅,铺得满眼都是。在下端的护墙板上,密密麻麻地刻写着每幅油画的信息。即便有二楼透进的温暖阳光,如此数量繁多、色彩艳丽的油画,肃穆地挂满了四壁,依旧凭空生出一种令人压抑的美感。再定睛看时,油画的主题,大都以当地的动植物为主,间或有风景人物。而在每面墙的上方,则标示着画中各色植物景致的地理位置:东印度、日本、新加坡、爪哇、澳洲、牙买加、南非……。

▲ Margaret Mee亚马逊勘探日记
正是在这个房间,在美艳油画的包围中,我突然意识到邱园的震撼,既不在于景致,也不因为齐全,而是在伦敦西北角的这个小小空间中,如此生动地浓缩和保存了当年大英帝国在整个全球扩张和殖民的过程中,由各色普通英国人——植物猎手、商人、管理者、画家、冒险家——参与的那一场搜集、观察、定义、审美乃至穷尽这个星球上所有自然之物的空前运动。事到如今,日不落帝国早已成为历史,但这场充满了野心,自以为代表全人类穷尽全球的运动,却在邱园活生生的植物和如此艳丽的绘本中存活下来。以至于运动中的巨大与细微,暴力和审美之间的张力,依旧生机勃勃,震撼人心。如果说,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帝国主义是貌似越来越遥远的血腥暴力的话,那么,在邱园留存的便是它依旧鲜活的明丽和美艳。这也就难怪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在写鸦片战争三部曲时,会把邱园、植物学家以及侵入中国内地,非法收集茶花,视为理解鸦片战争的重要线索,和当时由印度商人居中的鸦片贸易并置,细细描摹。
几个月后,英国公投,结果是令人大跌眼镜的脱欧。一时之间,英国人显得格外小气,整个伦敦也顿显萧条和颓唐。不知为何,在这样的时刻,想到了明丽的邱园。压迫与被压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与被任意驱使的小人物,官僚和百姓,富人和穷人,当现实和世界历史被如此泾渭分明地描述时,人们的内心总是得到更多的慰藉,生起更多的同仇敌忾和选择的决然。然而,邱园却在说着另一个版本的更加眼花缭乱的全球化故事。这是一个搅拌着科学、审美、自然、金钱、权力乃至暴力的故事,更是一个全民参与、充斥着描述归类、价值重估和审美判断的故事。
至此,当英国人最终放弃了令人自傲的欧洲梦,美国人退守到事关“伟大”的自保之中,曾经被帝国主义收编规制的星球,正在开始一场新的更加纷乱的全民运动。只是,当大英帝国的全民运动,最终留下的是孕育于血腥殖民史中的邱园时,今天这一场全民运动,会把人类推向何处,又企图在未来留下这个时代什么样的记号呢?也许,在这些问题面前,既没有比邱园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活化石,也没有比邱园更直接的对当前世界文明走向的质询和挑战。
■ 原文刊于2017年3月30日《文汇报 · 笔会》,原题”撞入邱园”,内容有删节,此为完整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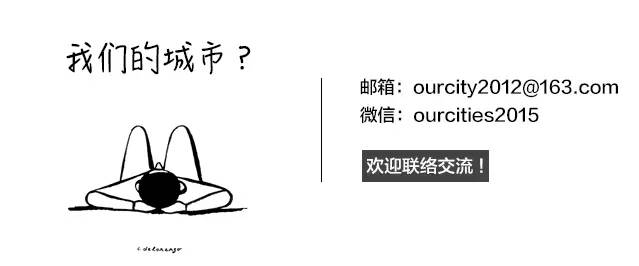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