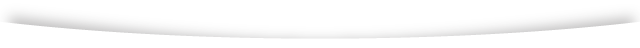
《世界建筑》2017年第8期
价值、阐释与真实:
五龙庙环境整治项目思考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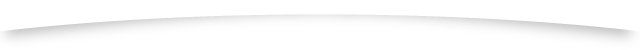
摘要:五龙庙环境整治的热议凸显了人们对于建筑遗产保护与其存在环境的关注,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见解。而本文则试图从“历史环境概念及其历史价值辨析”“五龙庙身份定位及社会价值实现”“建筑本体阐释尺度辨析”“历史语境真实性解读”4个方面重新审视产生争议的原因。
关键词:环境,历史价值,社会价值,阐释,真实性
山西芮城五龙庙(又称:广仁王庙) ①② 环境整治项目近期引起文保圈内学者的关注,并导致各方对于建筑本体及其环境保护方式的热烈讨论。持支持态度的学者们认为:环境的整治促使一度失落的宗教场所重新回归乡民的日常生活,并为之提供了一处难得的公共空间;曾经破败的庙宇吸引更多游客到来的同时,也增加了五龙庙的旅游收入;而更有意义的是利用社会资源介入遗产保护的尝试也取得了成功。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强调:周边环境的整治使得正殿这座唐代遗构及对面清代戏楼的“完整性”受到了破坏,从而割裂了建筑本体与存在环境的深层关系,但关于具体应如何操作却并未给出更多建议。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设计者王辉的方案可以接受,只是不应选择五龙庙这样稀有的唐代建筑作为改造对象。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五龙庙的争议,王辉曾撰文回应,并从“原真性”“存在感”与“主题性” ③ 方面予以说明。 1 而产生争议的原因,王辉则认为是“编码者”与“解码者”的身份差异所致。 1(111) 在五龙庙的环境整治项目中,王辉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编码者”,其背后隐含的是一位“建筑师”的自我定位;而将考古学者定义为“解码者”,则暗示了这一职业对于历史真相的求索。“编码者”或“解码者”本身并无褒贬之意,更多的是潜在地决定了二者在面对同一事物时的不同态度,是身份的不同导致了五龙庙环境整治理念的差异。但笔者认为这仅是部分原因,并非争议的根源所在。其深层原因恐怕要归于“相异的出发点”以及“将其视为何物”的判断,最终才让各方产生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因此,笔者拟结合国内与国际现行相关保护文件的相关内容,从以下4个方面对五龙庙的环境整治进行分析,以期厘清争议根源所在。
1. 历史环境的概念及其价值的辨析
要厘清五龙庙主体建筑与新建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环境”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前主席德国古迹保护专家米歇尔·佩赛特(Michael Petzet)曾将历史建筑的“环境”定义为:“(按文物古迹的状况)对附近或较远的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整个范围。” 2 我国2000年版的《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总则”第二条中指出:“保护是指为保存文物古迹实物遗存及其历史环境进行的全部活动”。 3(4) 其中“历史”与“环境”被组合使用,英文版中与之相应的词汇是“historic setting”,但并未对其进行具体释义。而“环境”在中英词汇表中与“setting”相应,其英文字面意思被理解为“environment”,参照的中文注释则是:“人文环境/景观、自然环境/景观、历史景观”。 3(46) 至2015年《准则》修订,新版中“历史环境”一词再次被沿用,其中第9条“不改变原状”中指出:(不改变原状)意昧着真实、完整地保护文物古迹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有效地保护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环境,并通过保护延续相关的文化传统。 4(9) “环境”一词的英文对照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就新旧两版《准则》来看,“环境”一词的概念均兼顾了物质性与文化性,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发展演变过程,特别体现在与“历史”相结合的用法上。然而,“历史环境”(historic setting)一词我们却很难在公开发布的国际文物古迹保护文献与官方话语之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表述。在西方语境中对于“历史环境”的理解其实更加接近于“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或“文化环境”(cultural environment)的概念,但就其内涵来说,则与《准则》中的表述并无二致。保护的内容既涵盖了文物建筑周边区域内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活动,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同时还涉及到它在历史变迁中的演变过程,以及在当下城市或乡村空间结构中的作用等。因此,如果要对“历史环境”进行综合评价,那么就需要从以上方面进行多重维度的考量。

图1/从五龙泉眺望戏楼(摄影:张建军,2012年8月)
那么五龙庙的“环境”状况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文献资料以及改造前的历次考察中有所了解:历史上的五龙庙应为合院形制,正殿墙上的两通唐碑记载了部分建庙初期的信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所立《广仁王龙泉记》石碑记录了县令于公凿引龙泉之水灌溉农田之事,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所立《龙泉记》则记载了五龙庙的扩建修葺始末,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除清乾隆时期重修五龙庙记事碑刻外则未有详细记载。近代的五龙庙由正殿、戏台、厢房组成(1950年代塌毁),四周围墙,东南角辟有小门。另据乡民介绍,解放后五龙庙一度作为学校使用,庭院也曾辟为菜地。至修复前,庭院荒芜,杂草丛生。戏楼右侧的三眼窑洞濒临崩塌,高阜之下的五龙泉更是早已干涸,已然沦为乡民日常生活垃圾的倾倒场(图1)。加上近年周边民房的加建与增高对五龙庙的存在空间形成挤压,从而导致这一宗教场所失去了往日的神圣与庄严(图2)。

图2/周边民宅(摄影:张建军,2016年6月)
通过上述分析,五龙庙的环境是否如部分学者所说可以进行历史复原呢?如果依据新版《准则》第9条阐释中“去除后代修缮中无保留价值的部分,恢复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状态;对于能够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历史环境要予以恢复” 4(14) 的建议是可以恢复的。但综合环境整治前的实际状况来看五龙庙并不具备恢复历史环境所需的条件,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除正殿与对面的戏台外,其他建筑物都已消失,而外部围墙则为近代村民自发砌筑,即便在考古发掘后也没有找到原墙址的确切位置。加之五龙庙本身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荒芜秽迹的现状环境也不属于五龙庙的原初状态。而在无确证资料下的臆测式重建则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历史环境重建一说无从谈起。此外,建筑及其环境自建成之日起就处于持续变化之中,有时功用也在不断调整,无论恢复至何时都无法完整表达其真实的历史状态。
那么五龙庙的环境整治是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质疑的“不符合文物保护原则”或者“损害到文物的历史价值”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照《准则》第30条对于“环境整治”描述:“对保护区划中有损景观的建筑进行调整、拆除或置换,清除可能引起灾害的杂物堆积,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古迹安全的生产及社会活动,防止环境污染对文物造成的损伤”。 4(9) 就此来看,五龙庙的环境整治工作并未违反上述条例规定,但这也并不表示五龙庙的环境整治工作就是完全合理的,我们有必要再参照一下国际宪章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其中,196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物古迹保护文件《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以下简称《威尼斯宪章》)的第6条明确指出:“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 5(53) 并在第7条中对此予以强调:“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脱离”。 5(53) 这一原则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以下简称《内罗毕建议》)中得到补充与拓展,其“总则”第3条指出:“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 5(93-94) 两部宪章均继承了将古代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的基本作用,同时注重古迹主体及其所在环境的整体性。就此来说,五龙庙环境的整治并不完全符合其要求。但《内罗毕建议》还有一项重要建议,那就是将“服务社区生活”作为遗产地的一项职责纳入其中,第7条指出:“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并使之适应于现代生活的需要”; 5(94) 第33条也指出:“保护和修复工作应与振兴活动齐头并进”。 5(98) 这说明对于建筑遗产的保护已经超越保存其历史价值的初级要求拓展到服务社区,以及如何有效地与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循环关系之上。因而,我们可以说环境整治后的五龙庙符合了《内罗毕建议》中提出的服务社区生活,以及振兴地方文化的倡议,而这也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之一。
2. 五龙庙身份定位及社会价值实现
五龙庙的身份定位与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并且直接反映了这座唐代遗构是否处于合理利用的状态,以及利用方式是否与历史价值相匹配,而这也是引起争议的症结之一。“周边农舍的无序翻建,倒逼五龙庙去产生一个更强大的气场,来抵制周边环境建设性的恶化” 1(110) 是王辉面对五龙庙惨淡景象时的反应。这不仅是一种“编码者”的自我身份定位,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显现。在严谨思考的基础上,五龙庙被重新赋予了清晰的功能设定:“将一个孤立古庙转换为一座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 1(110) 并通过3项具体策略来加以实现:“将美术和建筑两个课堂合一,能够放大芮城县的文化旅游特色;通过围绕五龙庙自身的木结构的信息延展;对于古建知识展示与阐释。 1(110) 尽管五龙庙最初是被作为博物馆来进行设计定位的,其目的是通过五龙庙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来吸引游客,并向其展示五龙庙的历史信息与建造知识。但从环境改造后的结果来看,其产生的社会价值甚至超出了当初的设想,环境整治达成预期目标(博物馆)的同时,还原了作为宗教场所的原始功能(庙宇)。五龙庙的场所氛围吸引了乡民的好奇心,从而使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到五龙庙的空间活动中。改造后的环境作为五龙庙与乡民之间的媒介,从物质与精神活动两方面再次激活了这所千年古庙的场所精神。
通过环境改造五龙庙的身份得以转变,但是否属于合理利用范围呢?按照《准则》所示,合理的利用可以促进文物建筑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活力,并为广大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是以不损害文物古迹的本体特征与历史价值为前提的。前文已述,五龙庙的环境整治并没有危及到主殿及戏楼的本体安全与历史价值构成,但在活化文物与服务民众方面却做到了最大化,并促成了一种地域传统与民间信仰的继承与发展。五龙庙所供之神为广仁王,目的是祈求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调雨顺。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信息社会的天气预报已经不再需要向这位神仙跪拜祈雨,然而广仁王却并没有因此而失业,朴实乡民又为他找到了新的工作,那就是“与民赐福”。 ③ 这其中既有节日性祭拜广仁王的传统因素,也有普通村民的精神生活诉求。这正是五龙庙在当下农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它为村民的精神需求再次提供了一方园地,而没有演变为表演性祈雨活动的道场。

图3/河北衡水宝云寺(摄影:郭龙;除古塔外,所有建筑物均为1980年代所建,其形制均仿自其他寺院。宝云寺塔在2006年6月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环境的改造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五龙庙身份的复杂化,以及空间情景上的戏剧化。对于乡民来说,五龙庙的作用是依旧是俗世性的,过去祈雨,现在祈福。他们并不介意五龙庙的复杂语义,反而乐享其成,在得到一处高质量的休闲场所的同时,还获得了一种地理上的优越感;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五龙庙是体验性的,他们既可以通过观赏建筑来怡情怀古,又可以浏览周边庭院了解古建知识;而对于古建研究者或者建筑保护的专业人士而言,五龙庙则是知识性的,其“价值”与“真实性”才是他们所关注的。这种情况在宗教文物保护案例中是常见现象,一座建筑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又是信仰的精神场地。但不同的是,大部分保护案例都选择了维护其现状,或者干脆恢复到了某种“历史状态”(这里暂且不论这些项目的重建是否合理,而是说建筑与环境在形式上具有统一性),从而没有在视觉上产生明显的冲突,而身份特征也更加单纯(图3)。

图4/村民广场(摄影:张建军,2016年6月)
环境整治改变了原有的空间氛围,五龙庙从荒芜落魄的景象一下转变为茶余饭后的闲话场,废墟与岁月产生的诗意被喜爱热闹的乡众所驱散。两种功能与两种人群在环境整治后的五龙庙悄然汇合,乡民的日常活动与节日祭祀,加上远足游客的到来为五龙庙注入了新的文化价值(图4)。在古庙新景的变换中,一幕幕戏剧性的场景不时上演:乡民一面虔诚地叩拜,一面欣然地收着门票;而游客在游览古庙之余也会在周边庭院中慢慢体味中国古建的精深。精神的迷信与建筑的科学毗邻而居,仅隔一墙。环境的现代与建筑的传统所形成的视觉对比,以及文化变迁带来的矛盾与冲突被“历史证言”还是“服务乡间”的争议所遮蔽,从而增加了五龙庙作为一个整体事物进行被解读时的困难。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此文最初源于笔者在微信群“C太太的客厅”中参与讨论于五龙庙环境整治项目时的部分感想,但因当时对这一项目没有全面了解,所以没有过多发表意见。后来不断听到同行在一直讨论此事,而2016年第7期的《世界建筑》杂志又刊登了王辉先生及其他专家的文章,在仔细阅读之后,笔者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因而整理成文。其中不乏个人推断与理解,但都基于此项目所呈现的事实与已发表文章的论述,偏颇与不足之处敬请指正。此外,《世界建筑》2016年第7期已经将五龙庙的设计过程及成果表达得非常全面,因而本文不再对其具体设计进行介绍,望读者自行查阅。
② 广仁王庙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城关镇龙泉村北端,坐北朝南的高阜之上。现存唐代道教正殿与清代戏台各一座,南北呈轴线排列。正殿内奉水神广仁王,故名“广仁王庙”。因五龙泉水从庙前涌出,又俗称其为“五龙庙”。五龙庙正殿为全国仅存4座唐代木构建筑之一,且在1965年就被山西省立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龙庙正殿及其对面的清代戏台在2015年得到专款并进行了加固与修复。
③ 关公巡城日也是五龙庙举行环境整治工程竣工日,乡民蜂拥而至,但已不为祈雨,而为祈福。一大早前来上香的大妈被《建筑创作》的记者问及有无上香拜庙的问题时回答:“拜啊,我一大早想来摆贡,但是因为有你们这个仪式,不让摆也不让上香”,并对阻拦产生了不悦。当问及:“那都求啥?还跟龙王求雨?”大妈则干脆地回答:“哎,啥都能求,心诚求啥都行。”参见:建筑创作.五龙庙前的乡土与精英. [EB/OL]. [2016-05-17].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16655121.html
参考文献:
1 王辉. 广仁王庙环境整治设计的理论性思考[J]. 世界建筑,2016(7).
2 米歇尔·佩赛特,歌德·马德尔. 古迹维护原则与实务[M]. 孙全文,张采欣 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53.
3 China ICOMOS.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Publication by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2.
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5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相关链接:
美术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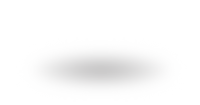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