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级暑假,我和朋友在校外城中村里各租了一间小房——房东家原来大概有个院子,东一间西一间搭了许多房子,形状都不规整。城中村挤挤挨挨都是这类临时搭建的建筑。朋友租的那间房,开门对着墙,靠墙放一张床,左手尽头是窗户,下面有一张桌子,剩下的空间就只容得下一个人进出。这间房虽然小,比起我租的那间没有窗户的房子,总还是要强些。朋友回家后,我就搬到了这里。
虽说有窗户,但窗外一块不大的空地,被三堵墙围成了三角形的天井,水泥地面上堆了些杂物。天井靠窗一头不通,另一头是一条窄巷——两堵墙之间约有十公分距离,大概是房东与邻居两家的界址。
夏天天气奇热,村子里通风不良,房间内闷塞可想而知,所以晚上是睡不好觉的。凌晨有几个小时天气略微凉些,朦朦胧胧将要入睡,还可以听到窗户外传来各种声响。那种响声无以名状,时有时无,既有屋顶乘凉的人轻言细语,也有街巷里的夜行人边走边摁打火机的声音,远处大路上车辆通过,天空里飞过一只鸟,只要有声音传入耳边,不论高低,总是显得遥远又清晰,听得人忽而烦躁,忽而感伤。
等到窗外声音变成一种有节奏的“噗噗”和“嗒嗒”声,四周已经亮了。又是炎热的一天。
我躺在席子上,一边流汗,一边想这声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准时,又这么顽皮。但头脑总是浑噩,好奇不能战胜身体的困乏。那到底是个谜。
有一天——不知道是睡得太晚,还是起得太早,“噗噗”和“嗒嗒”的声音传来时,我正坐在窗前,于是双手撑在桌子上,探头向窗外望了望,发现几只年幼的黄鼠狼正在一堆废弃木条上蹦来跳去。那些天我听到的,就是它们踩踏木条时发出来的声音。
已经多年没见过这种小动物了。我看了一会,它们觉察到窗边有人,也停下来看我。小黄鼠狼并不怕人,和我互相打量片刻,自顾在木条堆上玩去了。它们的母亲也在不远的地方,并不逃走,只是不错眼地盯着我。我识趣地退回去了。
我写信给朋友报告我的遭遇。第二天,它们仍然在窗外“噗噗”“嗒嗒”地跳个不休。
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再没有碰见过像这群黄鼠狼那样,对人类视而不见,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动物。
等我搬到上海中环住了几年,有时吃过晚饭去小区广场散步,春秋天傍晚总有一种暮霭沉沉的时刻,小区里的草木都笼罩在温暖而像有形体的空气之中,昆虫、鸟和蝙蝠在其中悄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猫走着走着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好像听见有人在呼唤它。我总觉得,小区的生态已经足够复杂,可以容纳更多的动物,只是看不见它们活动罢了。人让它们紧张。
我的儿子马可也听过2000年夏天那群黄鼠狼的故事。等他大了一些,在户外的时间变长了,有时等他玩够了,回家时天色已晚,偶尔有小动物先他一步冲过车道,朦胧中似乎是鼬科动物特有的体形。当我叫他看时,动物已经没入了麦冬草,不见了踪影。
自从那之后,他一直期待能遇上黄鼠狼。秋天暑气消褪后,我们在小区各处没有目的地兜来兜去。如果是晴天,傍晚碧蓝的天空很空旷,月亮上升到我们可以看到的高度之前,景色有些昏暗。分不清哪些是树枝,哪些是树影。
马可总在低着头寻找植物果实或者较早变黄的树叶,我在一旁帮他留意黑暗中匆忙驶过的电瓶车。在堆着落叶的草地和草地对面单元门前的垃圾桶边,一只小兽碌碌地来回逡巡着找东西吃。我捏捏马可的肩膀,嘴贴在他耳边,提醒他看黄鼠狼。

我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看它闻着、嗅着、翻找着,频繁地挪动四条短腿,长长的身体贴着垃圾桶的弧边,柔软地转向另一边。有时候它瞟我们一眼,但并不怎么用心。等马可往前走了一小步,黄鼠狼停下来,抬起脖子。它望望我们,从容地穿过小路,跳过一丛灌木,跑进了配电房边的杂物堆。
在第二年春天到来之前,我们经常在那一带遇上它。
它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经常在几块被道路分隔开的小绿地穿行。我想它大概会吃居民们放在树林里的猫粮。有时候它全速跑过车道,又像准备捕鸟的猫一样,匍匐着穿过草地,然后敏捷地攀上水泥台子,夹杂着黄色和棕色的毛泛出油光,就像一只拉长的老鼠。但它绝不像老鼠那样表现出惊惶。它闻闻这里,嗅嗅那里,眼睛的余光其实一直关注着周围的环境,尤其是人类的动作。
人们不像开始那样大惊小怪,而是装作没有看见它。好几次我刚刚伸手要摸出手机,它就抬起脖子,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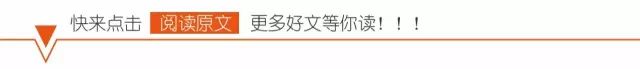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市政厅):小区史|黄鼠狼来了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