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9期】

农民安土重迁的情结源自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崇拜,即所谓的土地情结。而这种土地情结又源于中国固有的地理位置和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影响。中国是一个以内陆为主体的国家,三面连接陆地,一面临海。黄河、长江的中下游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 它的北边是难以逾越的大戈壁,西北方则是横亘万里的黄色大漠,交通受到严重的阻隔。其西南边更是世界上最为高大、最为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濒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浩瀚无边,古老的中国人是难以征服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特殊情感。在传统的中国农民眼中,“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 。土地是农民立身养命的“命根子”。
纵观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农民对土地的情结源远流长。曾有研究中国古文化的学者提出过这样一种假设:中国始祖之一的黄帝的“帝”有可能是土地的“地”,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常提及的“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即中国神话文学作品中的“地母”。黄帝被尊称为中华文明的始祖,或许是因为他是黄色土地的化身。因此,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中国人在很多方面与黄色的土地有关。生长在黄土高原的中华民族的先民,可谓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染的也是黄土。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面朝黄土、背靠青天,不停地向土地刨取食物。人们对二十四节气和春夏秋冬这样的季节变化非常敏感,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

旧时,在诸如郝堂这样的传统乡村,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没有了土地的家庭无法定居,家庭成员也缺乏安全感。在传统的中国乡村,一个家庭在当地的地位、荣誉和责任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家庭所拥有的土地的多寡。“一个人在乡村社会上的地位的高低与拥田的亩数常具有正比例关系。”(金耀基语)亦如海根所言,在任何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最高之身份即为依赖于土地而生之地位,土地之拥有变成一种深刻的情绪上重要的价值。同时,土地对农民来说有一个天然的归属感,他们对土地的稀罕有时甚至超越了对自己孩子的珍视,这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在传统的乡村,土地是家庭的重要支柱,是农民的命根子,正如杨懋春所言:“土地的数量表明了家庭对其过去和未来的责任的关心程度,以及他们奉行这些责任的虔诚程度。拥有土地也给了农民独立人格、精神鼓舞和自由的感觉。”这就是农民土地情结的实质所在,它的深刻内涵远远不只是一块外表形态上耕种庄稼的田地。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家庭的真正基础, 是农民及其家人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顾中国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对土地的抗争史。如果说 唐末黄巢的“均平”到宋王小波(李顺)、钟向(杨幺)的“今为汝等均之” “均贫富”, 只是一个抽象的均平思想,那么,到了明末的李自成和清末的洪秀全则提出了明确的均田地的要求。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而洪秀全更是提出“天下人田,天下人耕”的口号,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土地为天下人共有的口号,因此,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斗争彻底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及至现代以来,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毛泽东 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等,都顺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愿望,满足中国农民天然的土地情结。

当然,黑格尔曾说过,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在传统的中国农民眼里,土地就是命根子,是传家宝,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二十年前曾流传一则故事,说的是两位在十几岁就去东北流浪的七八十岁老人,几经周折在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处找到了他们的出生地,并在他们回家时各自从地里刨了一把黄土包在布兜里带回东北。也许外国人并不理解这两位老人的举动,但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所在。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一种特质,是对土地和故乡的一种眷念与离别的悲凉。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对土地的崇拜有中国人这样虔诚,他们把对土地的崇拜隆重而深刻地烙印在了它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差序格局”的社会,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人格构造。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的社会气中国特有的自然 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铸就了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道德价值体系 和文化人格心理。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伦理本位”下的“差序格局”是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孝、义、信是这一社会结构下的价值体系的核心思想。注重“面子”与“人情”则是从这一价值体系的核心思想中濡化出来的文化人格心理特质。
本文摘自
《郝堂茶人家》
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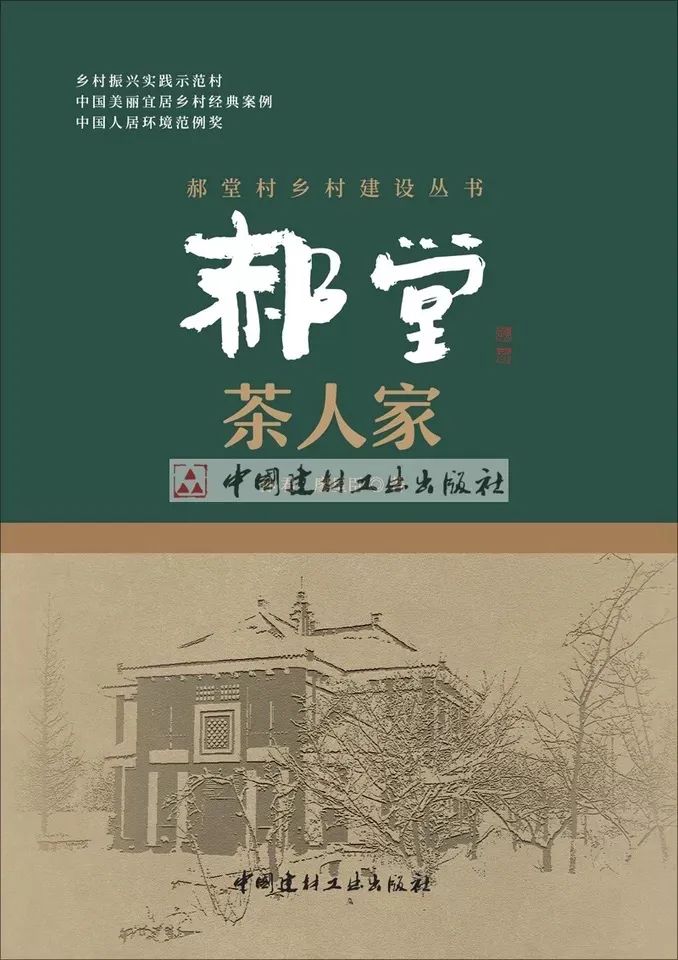
购书请通过网上正规渠道购买,或联系北京绿十字办公室进行订购。
联系电话:010-64429281。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京绿十字):农民的安土重迁情结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