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和外婆家都在老城内。今年过年回家,很意外地发现,奶奶家、外婆家所在的两个小区的“门房”(潮汕话,门卫的意思)突然都辞职不干了,都陷入了“失管”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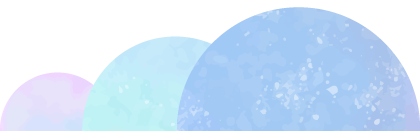
奶奶家所在的N小区位于城南,90年代末完工、01年交付,是有明确产权关系的物业。从建成到现在,仍然由本地开发商下属的物业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外婆家所在的Y小区位于城北,大概是在98年之前、房地产建设热潮那会建成的。建成没多久,开发商由于资金链问题就跑了路。平日里,小区的大事小事只能依靠这些没有房契的业主自己管理起来。
从建成年代看,两个小区都可以算作是老旧小区,楼龄基本都超过20年。随着这十年新区开发速度加快,外来开发商的楼盘在新区立起来了,老城区里边有能力的住户都往外置业。这些年小区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像住在N小区的叔叔婶婶家就腾退了房子,准备搬到新区,住进碧桂园的楼盘。
N小区和Y小区虽然一个有物业一个没物业,但原先都是有安保、实行封闭式管理的门禁小区。所谓安保,就是“门房”式的管理,这在老城区的小区内很常见,算不上是有保安,更谈不上什么物业。
N小区的物业公司雇佣了一对七十岁左右的老夫妇做门房。门房每个月向住户收取管理费,大概每户收个24~30块钱。期间提过几次涨价,住户们意见不小,所以也一直没涨上来。N小区不大,50户左右的规模,门房夫妇一个月能收到的管理费不多。另外再由N小区物业通过收取停车费补贴他们的工资,算下来也十分微薄。
最近两三年,随着N小区的人口流动性变大,人口构成日渐复杂化,外来租户占比大大提升,不配合交管理费的人越来越多,前天人还在屋里、后天已经人去楼空的情况也也来越常见。钱收不上来,日常管理难度也高了。门房二老年事已高,眼睛耳朵都有点不大灵光。本就力不从心的老伯老姆,干脆也就不干了。

Y小区
Y小区打一开始就没有物业公司。最早是靠小区里人脉广、有门路的住户物色合适的门房人选。门房也是六七十岁的老夫妇,能做的就是白天看个门、晚上落个锁,其他的管理等同于无。Y小区建筑密度高,空间虽小但住户不少。尽管跟N小区一样收着差不多的管理费,但Y小区没有物业的停车费用可供补贴。面临收费难、工资低的现实,Y小区的门房夫妇早早就收拾东西回乡下老家去了。

N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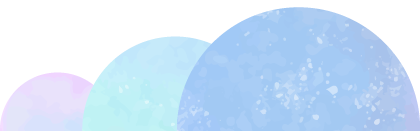
门房出走,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安全问题。晚上没有了门禁,两个小区的大门都形同虚设。摩托车失窃,放在楼下的快递也经常被偷。奶奶在家门口装上了监控,外婆也在寻思着装一个,住户的不安全感被放大了。原先有门房看着,住户们都不敢随便把电动车的电池带上楼,现在没人管了,安全意识薄弱的住户乐得方便;还有住户从家里往楼下拉了好长一条电线,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其次是停车问题。Y小区对停车不收费,但门房对住户的信息了如指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车主是不是住户、这车能不能放行。所以公共空间虽然不大,但摩托车、电单车的停放还是有秩序的。N小区有只对业主开放和收费的地下车库,地上的停车空间由门房管理,大车怎么停、小车怎么放都井井有条。而这次回家,就发现小区楼下的通道被占道的汽车停堵住了。听奶奶说,夜里附近小区也有车主过来乱停乱放。

占道汽车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公共区域的保洁。两个小区原本的门房都兼任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雨天过后扫扫积水,过年小孩子玩鞭炮的时候扫扫纸屑。门房走后,公共空间的卫生保洁工作也无人承担,外婆经常抱怨,Y小区门口的垃圾桶臭气熏天,很多住户把垃圾堆在桶外,一进门就好大一阵味道。
去年的时候,全市动员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安装燃气管道。有街道和社区的同志到N小区宣传,不少住户听了之后跃跃欲试。尤其是老人家,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搬不动煤气罐,所以特别希望能用上方便安全的气。但小区里的住户意见多难协调,成立自治组织去申报,又没有住户愿意出面组织,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门房出走之后,小区治理问题频发,物质环境不断衰败,直接体现在了房屋的贬值上。我小时候在N小区住的时间长,对N小区更加熟悉一点。这一年小区里出售房屋的业主还不少。邻居家的房产被抵押,70多平米的房子按市值赎回才花了20来万左右(这个价格和无房契的Y小区持平)。一个认识的阿姨也讲,她100多平米的房子,也只卖了40万左右,远远不够在新区置换一套新房的首付。
门房出走之后怎么办?成了这一年摆在小区住户面前最大的难题。有物业的N小区经营不善,雇佣不到新的门房;而没有物业的Y小区,住户们一谈到要出钱,都纷纷摆手。他们最担心的是其他业主、租户搭便车的行为,正如N小区提出成立业委会时候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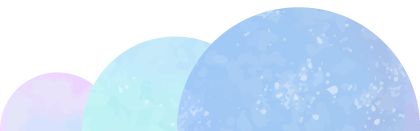
这两个小区会一直衰败下去吗?从目前的管理水平来看不容乐观,但我也看到了一些转机。
首先, 两个小区的住户已经通过自组织的方式解决了保洁问题。Y小区的公共空间本来就不大,两三个住在一二层、平日里空闲时间比较多的妇女自发地担任了清扫公共空间的职责。住在外婆对门的梅姨,是早些时候请来门房的业主之一,在小区里属于能“话事”、德高望重的。住户们现在将公共区域4个路灯电费交给梅姨,梅姨每年收取一次,帮住户统一代缴电费,也支付一些日常的保洁费用。
N小区的住户自发划分区域,形成片区负责的口头约定,每个楼栋前的公共卫生清洁由对应楼栋的退休干部、全职主妇负责,形成了默契、不成文的“楼长制”。燃气加装虽然最终作罢,但有住户跟社区建立起了联系,通过反映问题的形式,不久就把原先2个脏兮兮的大桶撤掉,换上了4个容量适中的分类垃圾桶,垃圾收集点周边的环境也改善了不少。

新增的分类垃圾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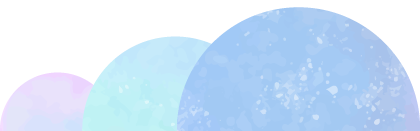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建设问题,更是社会治理问题。老旧小区的原住民大多是像奶奶、外婆这样年事已高的老人家,现在又越来越多地为外来务工人员租住,涉及到众多的使用权人。老旧小区是社会治理的显微镜,人际关系千丝万缕,矛盾关系无处不在。这次返乡的所见所闻让我直接体会到,小区使用权的破碎化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如何“赶走”了门房,导致了小区失管的困境,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
门房的出走暴露出老旧小区治理上的更多问题。缺保洁、没门禁、停车难、缺钱缺制度、没有愿意做事的人……老旧小区的问题看似很小,解决起来却不容易。这些事情既是与城市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也是城市规划建设中最最老大难的问题。
问题意识的觉醒,是社区居民形成共识的起点。从问题入手,通过大家商量确定老旧小区改造要什么、要做什么、有没有钱、找谁来做,通过协商的方式,形成对老旧小区改造内容、改造顺序和改造资金的安排。
处于产权过渡地带的公共空间和房前屋后,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空间载体。两个小区组织能力的快速成长,都是以解决公共空间的卫生保洁问题为抓手。老旧小区改造很多涉及半公共空间,介于私人和公共空间的过渡地带。问题的解决也应该从这些人们最关心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切入。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改造行动重构社会关系,通过理想的社会关系再建美好的生活空间。
在住户采取“自救”措施的经验中,也藏着奥尔森公共治理的智慧。一是缩小社区管理的幅度。比如N小区把小区分解到楼栋,实行楼长制,让楼栋里的居民能够通过行动实实在在地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变化,对于他们加入到公共事务的管理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二是动员社区的能人、有意愿的人。在美国,不少成功的社区议事会都是退役军人、退休老干部主导的。Y小区的妇女、N小区的退休干部也是使得小区组织起来的关键人物。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N小区的业主在燃气加装事件中建立了与所在社区和街道的联系,Y小区听说也已经纳入所在街道加装智能门禁的试点范围。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路径,不是照搬西方社区公众参与的模式。从原理来讲,中国的家国政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政治。老旧小区改造的关键,在于把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营造出来。一方面,人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事务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社区与家庭发生关系,将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公共服务下沉到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之中。
(现在每年回家的时间不长,来不及深入了解家乡的变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变化做一些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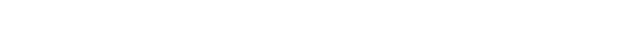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文责自负,与本公众号立场无关。
欢迎公众投稿,投稿邮箱RR_lab@163.com,
请注明微信投稿字样。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化研究):“门房”出走之后: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