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虽然已经追完几天了,但是这部电视剧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久久不能平息。起初看这个电视剧,完全是因为有刘奕君,想知道这个演老狐狸的专业户怎样在一部正剧里施展拳脚,没想到看完第一集,我就被深深吸引了,特别是黄文秀的演员杨蓉,高度还原了黄文秀本人的音容笑貌。在片头曲部分,黄文秀生前采蜜的照片和杨蓉演的黄文秀的照片衔接在一起,让人有强烈的代入感。看了这部剧,了解了黄文秀是个怎样的人,做了怎样的事,更是让人感动不已,更为她的牺牲扼腕叹息。
我强烈推荐读者去看这部剧。不过这篇文章不是影评,而是想谈一谈剧里的女性主义视角和其中折射出来的规划理论,以及对我们中国规划教育的启示。
《大山的女儿》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大山的女儿》用时下常用的一个标签形容,就是“大女主剧”:女主角不是男性的附丽,而是顶天立地、有个性、有担当、正直、勇敢、智慧的独立女性。黄文秀本人当然是这样的人。不过,这部剧除了对女主角的刻画,还塑造了一组当代中国女性的群像,讨论了女性所面临的一系列特定困难,以及以黄文秀为代表的党和政府组织——现代性的力量——如何在传统农村帮助女性应对这些困难。
剧一开始,韦其代的丈夫因车祸去世,韦因分割赔偿款与公公产生了争执。公公想多分一些给儿子修坟,同时把祖坟翻修;而韦其代希望为自己和孩子多争取一些生计钱。黄文秀和她的同事们根据民法的原则,巧妙地把钱打到韦其代的账上,为她争取到了应得的部分,同时也避免了媳妇和公公的冲突。这个苦命的寡妇后来再出场的时候,就是和公公争论承包地是否转包给种植大户种枇杷。她说服公公的底气是,她、亡夫和儿子三个人的承包权都在她手上,占全家承包面积的四分之三,她不同意转包,就没法转包。公公最多只能摔碗而去,没有其他办法。在中国农村,妇女权利工作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黄文秀为当地妇女所做的工作,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村基层组织为中国农村妇女所做的工作。
这部剧还包含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关切。比如家庭暴力问题——贫困户岑丽凌因为不知谁给她家捐赠了水泥,差点被在外打工回家的丈夫殴打;比如寡妇的婚恋自由问题——黄文秀帮助寡妇兰双应拒绝了前任第一书记的追求;再比如女人“干得好”还是“嫁得好”的经典问题——下乡参加社会实践的北师大学生和兰双应的女儿金凤展开了讨论:为什么即便是贫困户的女儿也不应当想着靠嫁个有钱人改变命运,因为附丽于他人的女性是没有独立自由可言的。还有镇里的“穆桂英”镇长于芒果,大着肚子还跑去现场解决旅游纠纷。虽然该角色设定为NPC【非玩家角色,此处意为配角】,但也是一位有着强烈个性的女性。剧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对残疾夫妇小美沙一家的刻画。小美沙哑而不聋,丈夫瞎了一只眼。他俩虽然日子艰难,但是独立、自强,在文秀书记帮助下,开办了村里的第一家快递点。导演把全剧仅有的两处对着镜头的独白给了小美沙一处,借她之口描绘普通村民看到的村里的变化。
当然,这部剧里的女性也并非一个个都是苦大仇深,也有一些“小女人”设定。比如刘奕君饰演的村支书农战山的爱人岑福玉,是全剧的温柔担当。在堂妹岑福爱的煽风点火下,岑福玉总觉得老公忙于工作是因为对黄文秀有他心,总是温柔地“点拨”老公,但真正接触了黄文秀之后,也被文秀书记帮助村民的一片真心感动了——尽管有点“小女人”,但她不是个拎不清的人。而岑福爱可能是全剧唯一一个稍带反面性质的女性,老公蒙昌龙是村民委副主任,也是枇杷种植大户。黄文秀来了以后,推动成立了烟草、禽畜、砂糖橘合作社,都按二八分成,八成利益给村民。而枇杷种植则按照五五分成,越来越多村民就不爱种枇杷了。岑福爱心疼老公,就到处煽风点火,劝村民不要加入其他合作社。随着剧情的发展她后来也理解了黄文秀,她夫妻俩是全剧的撒狗粮担当。
这部剧最体现编剧和导演女性主义视角的,是“强行”安排了一段关于性侵的讨论。黄文秀的大学同学在城里,被领导性侵,反手把领导打残,自己也留下了心理阴影。她和男朋友来村里搞慰问演出,黄文秀带他们看脱贫攻坚的情况,疗治了她心里的创伤。我想,这段戏其实和主干关系不大,可有可无。但也许,创作者是想告诉身居城里的女孩,不要一提到女性主义就只想到性侵,实际上女性主义关怀是存在于广阔天地间的,关于女性主义的思考和关切,真实地存在于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脱贫攻坚中的规划理论
如果不接触西方的规划理论,绝对联想不到脱贫攻坚和规划——特别是城市规划——有什么关系。记得我刚到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发现课程中有许多沟通谈判技巧和活动组织有关的训练。当时有些疑惑,规划需要这些吗?现在明白过来,先发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过程,物质空间大建设的阶段已经过去;在已经建成的社区里,针对人的工作成了规划工作的主流,动辄都要和居民商量着来。在北美,这样的城市规划就成了“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这里的“社区”,要理解为 community 的词根——commune,即在一定地域内长期生活的人的共同体。这种城市规划,已经不再是对物质空间的规划了,而是对人、人的共同体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引领。
当下,中国广大城市中推进的城市更新,也慢慢进入了这个阶段。而在中国语境下,脱贫攻坚实际上是最广泛、最深入,也是积累了最多本土经验的“社区规划”。在这其中,重要的不是物质空间设计,甚至也不是对权、钱等核心资源的动员,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规划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谈判和组织能力了。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剧中前任第一书记——县银行的钱经理——被轰走了,而刚毕业的小姑娘黄文秀却完成了脱贫任务?
于我而言,《大山的女儿》帮助我更好地思考规划理论。西方规划理论对于规划的经典定义——“在公共领域把科学和技术知识带到实践中的努力”(an attempt to relat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to actions)[1],涵盖了各种公共领域的规划,包括但不限于物质空间的规划。这个定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和黄文秀们从事的具体工作:我们的脱贫攻坚战不正是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知识帮助贫困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伟大实践吗?!黄文秀们这些扶贫干部,不正是将现代理念武装的头脑和贫困地区人民的实践紧密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取得全面脱贫的伟大胜利的吗?!
西方的规划理论,由于它追求公平公正的底色以及西方特有的在个体层面进行思考的面向,近些年来越来越强调关注女性、少数族裔、原住民和性少数者的视角,甚至扩展到“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原住民”这样的多重身份,“交织重叠不平等”(intersectionality)成为规划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议题。这种关注个体的倾向固然离不开西方走向“社区规划”、更多需要与个体打交道的大实践背景,但是,许多时候,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靠更多照顾弱势群体,甚至是搞“逆向歧视”就能够解决的。
《大山的女儿》发生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这是个壮族村落,以西方规划理论的视角看,剧中“社区”主体不仅是少数族裔,还是原住民,还是女性,绝对很 intersectionality了。然而,细细品味,这里脱贫的困难和解决方法同样适用于汉族地区,也不因贫困户是男是女而有差别。比如,砂糖橘不结果,不会因为贫困户个人的身份有所不同,高低都得像文秀书记一样去请种植专家来指导种植;再比如,枇杷种植收益分配低,是因为流通环节有既得利益群体。既然是“既得利益群体”,它的剥削不会因为种植户是女的就多一些,是男的就少一些,总归需要像文秀书记那样运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办法斗争掉。实现改变,重点不是落脚在多帮助谁,少帮助谁,而是怎么帮助这个社区整体:规划者、变革者们必须有信念,有爱心,有文化,懂科学,了解法律制度,同时又能扎根地方,接通地气的人。
我看了《大山的女儿》导演的专访,他讲最打动创作团队的是黄文秀的两点:一是好不容易从大山走到了北京,却毅然选择回来建设家乡;二是父亲有病,自己又是小女儿,一直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中煎熬。这两点固然打动人心,看重这两点,也体现了创作者的人文情怀。但是,黄文秀最打动我的,是她的真心:她是真心想帮助乡亲们脱贫,考虑的不是账面上的脱贫,而是不仅要脱贫,还要把百坭村建成“一个乐园”,用她的话说,“要真正地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听起来太理想主义了!然而,这不就是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吗?
黄文秀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认认真真工作的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黄文秀的认真是讲方法的。她本科学的是思想政治,研究生是哲学专业。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她的所学。村民开始对她敬而远之,她懂得“春风化雨”,学当地话,帮村民干活,获得村民的接纳。砂糖橘不结果,她不偏听偏信,坚持自己调查研究,先是问北京学农学的朋友砂糖橘的市场情况,又托人情找专家来村做技术指导。她也知道向当地干部和村民请教,摸清村情民情和当地人脉权力关系。村里的网红班小班帮着卖砂糖橘,碍于本地人的情分不好意思收提成,黄文秀却提出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指出这才是长久之计。可以说,黄文秀是兼有理想主义和专业精神两种宝贵品质的干部,这可能也是她在牺牲以前就已经小有名气的原因。这样的人,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又红又专”。
现在,我国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未来反贫困的斗争,将更多在城市这个新战场上。最近走在街上发现,实体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许多店铺关门歇业。北京西郊一个集体土地上的购物中心,原先两层的分割摊位全部关张。城镇居民的生计受经济波动影响更直接,未来二十年,城镇社区的老龄化、人口减少、社区凋敝等问题势必将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我们能否保持千千万万城镇社区的欣欣向荣,在城市复制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现在,许多规划人发现规划专业吸引力不如以前,思考规划教育向何处去。其实,我想中国规划教育可以在上述这些方面多多发力,为“社区规划”输送懂城市的专业人才。
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以黄文秀为榜样的。她不会“社恐”,甚至有点“社牛”,懂得如何与普通人、陌生人打交道。她了解城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会算经济账;她有“政治头脑”,能够看懂一个地方的权力关系;她熟稔法律法规,懂得充分利用政策;她还有一定的空间思维和设计灵感,能够“螺蛳壳里做道场”。规划教育除了发扬既有的规划设计优势,还要在人际交往、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这些知识上发力,才能培育出符合未来需求的规划者。更重要的是,还要鼓励、引导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把他人、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我知道,这样设想规划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了,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最后,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也纪念黄文秀牺牲三周年: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937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而题的词】
参考文献
[1] FRIEDMANN J.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90, 27(5): 93-114.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
读懂“土地财政”,玩转城市更新
“资产负债表不想奋斗”是个问题吗?
老电影《“特快”列车》中的规划理论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海外行思 | 《大山的女儿》中的女性主义和规划理论——兼谈中国规划教育的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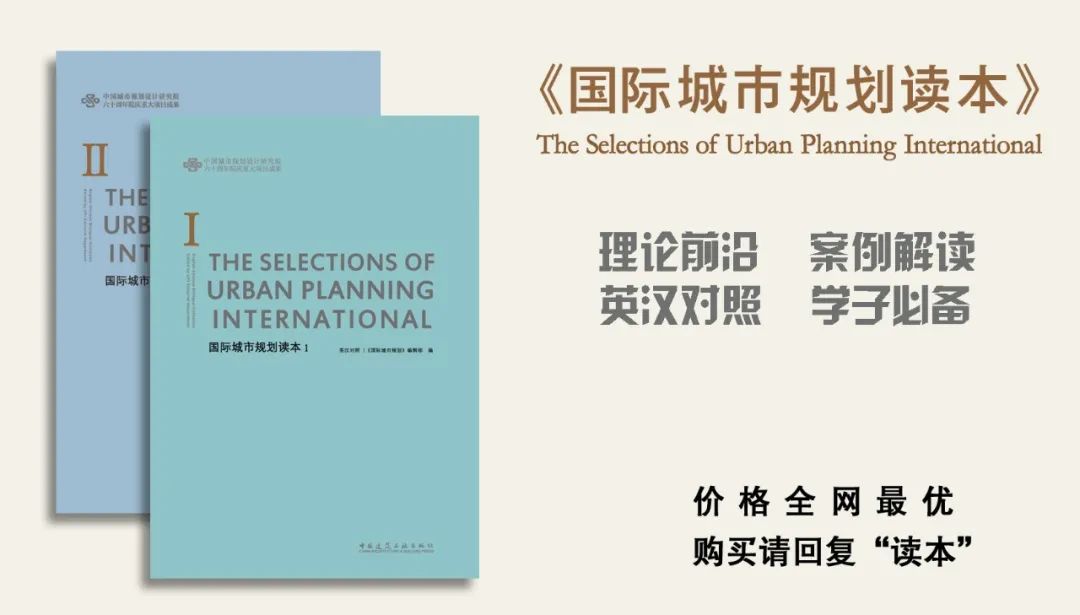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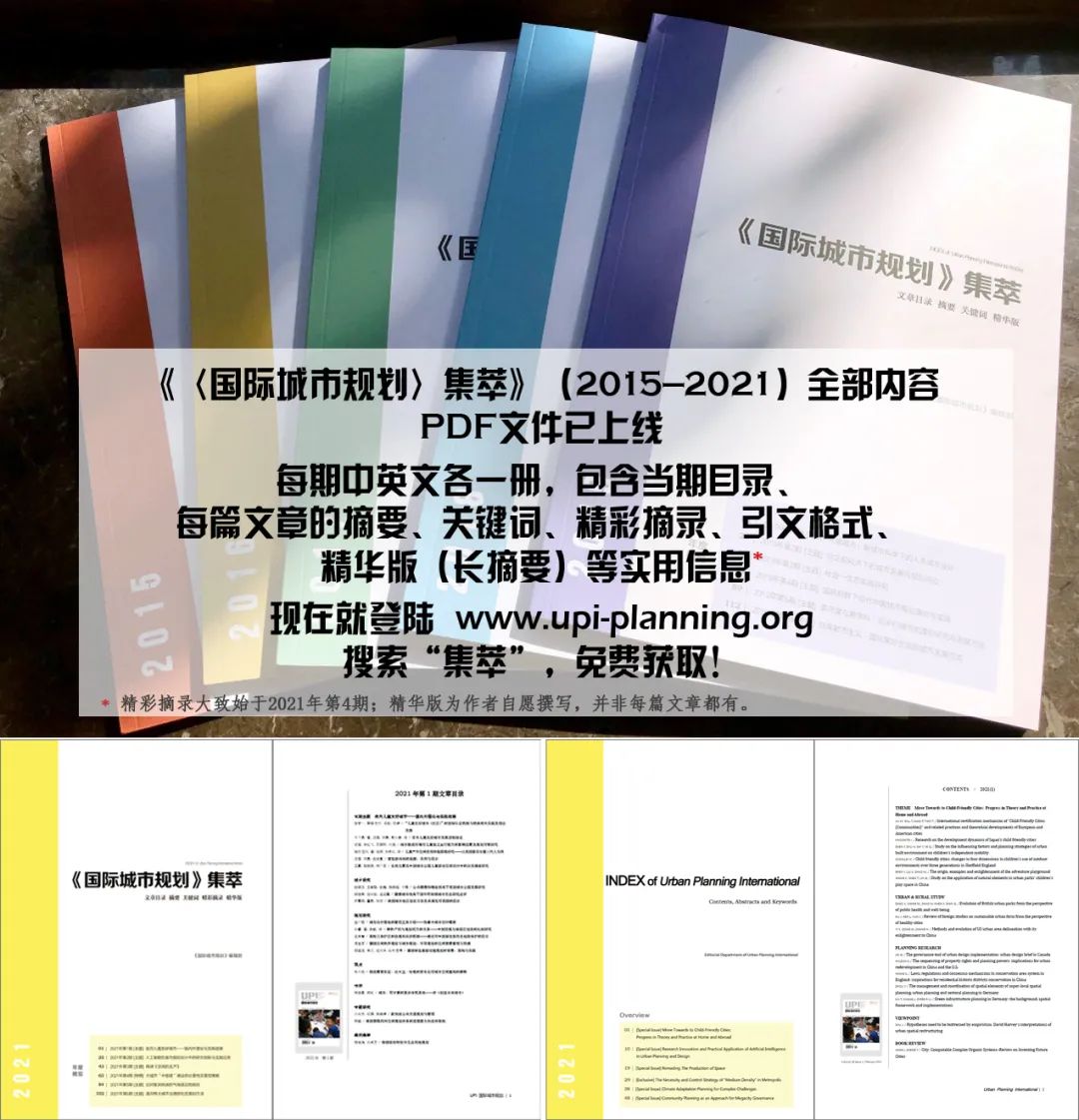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