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石板房村是位于北京房山区佛子庄乡一个普通的村落,村域面积非常大。一条十几公里的河道贯穿南北,周围是绵延百十里的高山。与全国许多村庄类似,这个曾经二三百人的村子,如今常住人口只有七十多人,冬季则更少,而且基本都是老人。
2017年5月底,北京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作为市农工委邀请的社会组织之一,参与到协助第一书记扶贫减贫的工作尝试中来;8月初,石板房村社区文化志愿服务项目获得2017年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资助,此后,协会招募选拔11位志愿者先后三次前往村里开展调研和社区文化活动。
志愿者们对三次走访调研的素材进行整理,形成了文本《石板房村村情概述及人物略记》和视频短片《守望石板房》,我们将会分期选编《石板房村村情概述及人物略记》中的部分章节。
今天,我们推出陈景纯和史秀荣两位老人。
陈景纯和史秀荣夫妇家位于石板房村一队的一个山坡上,过去是村里小学的所在地。两棵高高的柏树从背后拥抱这个屋子,而院门口的核桃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陈景纯和史秀荣夫妇现在的家
史秀荣回忆起小时候上学的情景:“那时我带着我弟弟上课,他坐在我旁边。我在河沟里捡一块像粉笔一样的划石,就拿着划石写字。就在这个地方。”过去村民曾自发组织过戏班子,给乡里乡亲唱河北梆子,戏台子也曾搭在这里。
而那些早已为岁月之河冲刷殆尽的遗迹,仍化作记忆,鲜活地存在于老人们的心里。
陈景纯和史秀荣都生于1945年。那一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烧杀抢掠,陈爸爸带着全家搬到了离村一公里的连湖沟。他们住的草房只有七八平米,房子很矮,站在土炕上都穿不了衣服。陈景纯就出生在这里。
当时,一家人靠父亲种地、放羊糊口。狼经常出现,有时一两只,有时一群,大家就点燃火把、敲锣来把狼赶走。
1949年全国解放,他们把家安回到离村50米的山坡,建起一间十平米大、两米高的小草屋。一直到1954年,家里才盖了三间石板房。祖母非常高兴,不停地背着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陈景纯玩。那时祖母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身体很好,去世时是96岁高龄。

志愿者造访时,陈景纯老人家新打的核桃
史秀荣的父亲和大爷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相依为命,自力更生撑起了整个家。
史秀荣的爷爷去得早,大爷13岁、父亲8岁时就跟着大爷爷、二爷爷一起生活,大爷负责放一百多只大羊,父亲则赶一群小羊。早年春节讲究烤柏树火,父亲大年三十去砍柏树,直到爷爷叔叔们饭都吃完了才回来。冬天很冷,他刷碗时看见手流血了,才发现手指已经被砍下半截。他把水泼到门口,水结了冰,把二奶奶滑倒了。二爷爷就惩罚父亲,不让他吃饭。

史秀荣老人和志愿者们一起干活聊天
大爷一气之下带着父亲离开,在爷爷生前的一块地上盖了两间茅草房。两兄弟白手起家,一点一点把日子过得红火了起来。土地改革的时候,史秀荣家被定为中农,大爷挨批斗,一位叫赵喜的贫农还为他们说了话:“他们从小就没有父亲,那点粮食和地都是他们哥俩一点一点地干的。”
那时,史秀荣的大爷被关在现在水库上面的小屋里,谁也不敢给大爷送饭,除了史秀荣的母亲。母亲性格开朗率直,她说:“我们家又没剥削过人,凭什么不让吃饭哪?”
谈起这段往事,史秀荣不免苦笑着自嘲:“其实我们家的人都不笨,就是被‘成分’给坑了。我父亲和大爷特别能干、能吃苦,把我们下一代‘坑’了。”
1954年,九岁的陈景纯开始上小学。四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大的二十来岁,小的八九岁,老师总是讲完一二年级再讲三四年级。陈景纯头脑灵活,爱思考,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有时老师还会让他答高年级的试题。就这样,他上满了四年小学,成绩是上等。
当时的老师刘景唐教学很负责,他让学生听课时看着他第二个扣子,这样注意力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陈景纯毕业那年,刘老师被调去集中学习,离开了村子,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一位军营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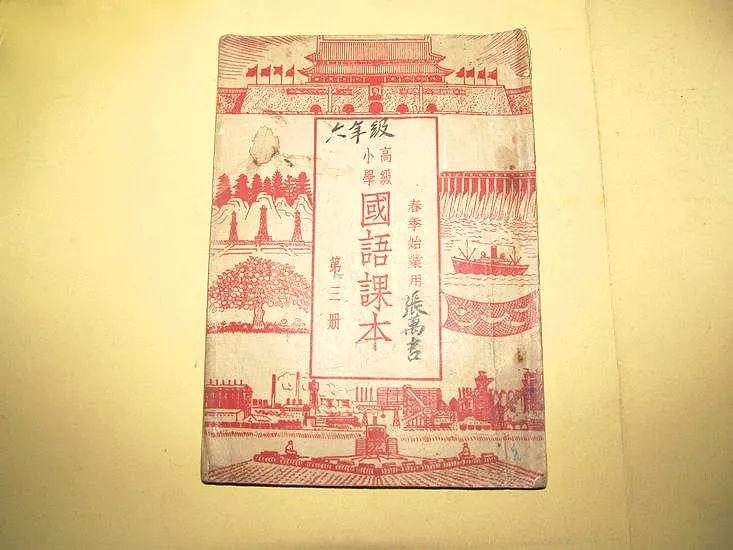
五十年代的老课本
1958年8月,陈景纯与同村的陈兴荣、陈庆方等人一起去15里外的长操村高小继续读五六年级。史秀荣为了照顾弟弟史正元没有再去上学,对此,夫妻俩至今仍感到遗憾。
到长操后,陈景纯先是在大舅家住了半年,和表弟们睡在一个大炕上。后来学校给男生们找了两间房,少年们正值好玩的年纪,把房子住得又脏又乱。冬天,天寒地冻,他们不想走到茅房,一出门口就撒尿,没过多久那里就拔地而起一座小小的冰山。夏天,大家一起到河里游泳,陈景纯练会了狗刨、甩泳、被称为“扎猛子”的潜泳;孩子们还管跳水叫“跳冰棍”。中午去河里游泳会被老师批评甚至罚站,于是他们从河里出来就跑着去上学,一出汗,老师检查就划不出白印,也就发现不了他们的秘密了。
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大家都吃大锅饭,学校也不例外,陈景纯很喜欢吃食堂的锅尕。全民大炼钢铁,学生们也要帮着背矿石、拉风箱。陈景纯还记得,当时高小的校长叫连文续。校长和刚分配来的“校花”老师马文花走到了一起,“听说文革时连校长被批斗时,马文花还陪绑着。”
高小毕业后,陈景纯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化工局焦化厂技工学校。在那里学完两年基础课、一年专业课后,他们将被安排去北京焦化厂当工人。
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学生们的定量是男同学每月29斤、女同学每月27斤,根本不够吃。有的同学会偷改粮票,把二十几号改为十几号提前用,但这样月底就没的吃了。有的女老师看学生可怜,偶尔接济二两粮票,学生就能度过难捱的一天。
星期天,大家就到野地里剜野菜,野菜洗净后用开水一烫,放点酱油就可以吃了。他们还曾到地里偷黄瓜、茄子、玉米生吃,偷枣时,他们总会买上几块糖引开看枣的小孩,自己则趁机上树去摘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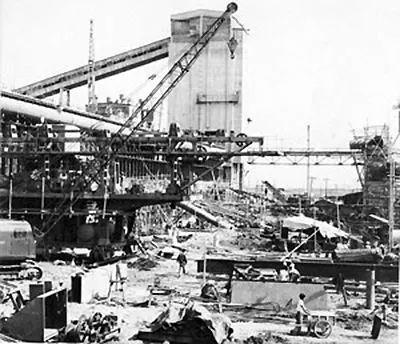
北京焦化厂旧照
陈景纯曾报名参军,并通过了身体检查,但他参军的想法遭到了祖母的反对。陈景纯的堂哥陈景全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因此,祖母的态度非常坚决。拗不过九十多岁的老人,陈景纯来到焦化厂练焦车间交换机的岗位上,当起了学徒工。
一个焦炉有几十个炉膛,每个炉膛有两个风门,位于炉膛底部的两端,进气门每半小时要调换一次。陈景纯的工作就是操作交换机。他工作认真、踏实,每月都能拿奖金,有时奖金会比工资还高。工人们的工作是三班倒,夜班从十二点至早上八点,会额外给三毛钱夜班费,陈景纯常拿它买咖啡喝。

北京焦化厂废弃的反应炉
那段时间陈景纯迷上了打兵乓球,下班后会拿着馒头边吃边练习。1964年,厂里举行兵乓球比赛,他打败了厂里几年的冠军。从此,他把冠军给得罪了,两人再也没有说过话。此后,陈景纯也再没参加过兵乓球比赛。
住在垡头小区九号楼三层宿舍时,陈景纯睡在一位老师傅的上铺。老师傅很会下象棋,每天下班都教陈景纯几招,他学得很快,也学得很好,和别人下棋虽然有输有赢,但总是很快活。只是下完棋他常常辗转反侧睡不着,忍不住要琢磨棋步到深夜,甚至失眠。后来,他便也不怎么下象棋了。
1964年初,陈景纯的祖母去世了。第二年元月,他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海军。在家过完年,厂里开了欢送会,他们便坐上了从北京南站出发的新兵专列。出发前,双方家长提出必须先领结婚证才能去当兵,陈景纯于是匆匆与青梅竹马的“准媳妇”史秀荣结了婚。
新兵蛋子们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终于抵达了广州湛江火车站,又转乘军队卡车去往雷州半岛新兵训练团。当时南海舰队工程部缺少潜水员,就把来自北京的十五个年轻人调到了南海,在工程部潜水排进行潜水业务训练和学习。他们先在陆地上学着装、吸气、排气,再在水下训练上升下降、进气排气、控制潜水衣气体保持平衡。那会儿的潜水教材,陈景纯现在还保存着一份。

南海舰队某潜水分队潜水员正在训练
1966年,北京传来搞文化大革命,砸四旧、立四新的消息,有的战友家里被抄,大伙的内心充满了困惑与焦灼。1967年,地方上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部队受命支左,大家看不惯造反派,实际上支持了保皇派。在湛江,他们没收了造反派偷出来的子弹,批评了其停工停课的行为。
就在这一年,部队将他们调往广州市下川岛学习整顿一年,并改派朱熙文做他们的指导员。他们原来的指导员姓薛,曾经讲过“文功武卫”是“两派打仗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就应将江青打跑”。因为这句话,他被判了八年徒刑,好在后来得到了平反。

如今的广州市下川岛
下川岛不大,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和500头用于备战的牛,没有其他居民,一切食品用品都需要用船运到岛上。岛上也没有电,他们平时只能用蜡烛、油灯和手电照明。士兵们整天学习,偶尔休息时,便在供战士出操的简易篮球场上打一打篮球。
第二年夏天,陈景纯的母亲捡杏摔断了腿。那年12月,他被提为排长,但考虑到家里的情况,他还是提出了退伍。复员后,他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厂子里先后担任车间主任、行政主任,1984年开始又负责管理供应处,直到退休。
陈景纯和史秀荣夫妇对石板房村充满了眷恋。他们在燕山有房子,家里不少小辈也住在燕山,但除了冬天,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待在石板房。
虽然年已古稀,他们在两地仍有忙不完的农活。在石板房,他们照料着一片小小的菜园;2015年春天,他们还在儿子们的帮助下在燕山的家里挖了一个长一米六、宽一米四、深一米的菜窖,由于是在花岗岩地面上动的工,这活儿对老人家来说还真不简单。但夫妇俩并不觉得有多劳累,陈景纯还说:“每天挖一点儿、出一点汗,对身体有好处。”

陈景纯和史秀荣在接受访谈
在其他人的眼里,陈景纯家算是村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而这是一家人踏实劳作的结果。在史秀荣看来,在农村并非无法自给自足,至少在低保的基础上能够有所补贴。“我觉得能干就要干一点,可能跟我们这种血液有关系吧,随我父亲。”“埋怨”过家里能干的老一辈“坑”了孩子们的她,谈起父亲时还是充满了敬意。“我有时候就跟孩子讲,不要浪费一粒粮食。你们姥爷8岁就开始放羊,那时候的生活过得多苦啊。你们以后生活再好,也不能忘本。”
2015年6月7日,陈景纯的大孙女陈雨赢参加了高考,并被湖南师范大学录取。这位学霸少女对自己的高考成绩不是特别满意,但她的爷爷奶奶已经非常为她自豪了。28年前,就在陈景纯的两个儿子填志愿的前两天,公安局通知:他们全家的农民户口变成了居民户口。在那个年代,两个少年差点因为农民户口的借读生身份而不能填表,与继续学习的机会失之交臂。那时,户口办成了,似乎一生的难事都办成了一般。

陈景纯老人在包饺子
现在,七十岁的陈景纯还是个“潮男”,农活和娱乐之余,他也上网冲冲浪、写写回忆录。时不时地,他会在word文档里记录下那些说到他心坎上了的段子:“我今天看到一首诗,讲的是人生只两件事,第一睡,第二吃。人能睡说明身体没有大的问题,能吃饱是最幸福的。”
他说他喜欢道家观点,那让他联想到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场景。有时,他爬山锻练体力,到了山顶就打一套太极拳;然后从山顶向四周瞭望,任凭辽阔的绿意,填满他历尽千帆的眼睛。
RCRA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行动,聚合全国农研专家、志愿组织、公益社团、乡友力量,为亟需支持的乡村提供乡土调研、创意传播、社区凝聚、人才培训、生态修复、乡村设计、品牌孵化、创业众筹等多项志愿服务。作为北京志愿者联合会一级社团,RCRA本着精准造血、务实坚持、接力跨界、合作创新的态度,为全国乡村能力建设提供志愿服务。欢迎广大乡村基层管理者、社团领袖、研究人士、设计师、志愿者加入我们,一起实现“文化乡村梦”!

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乡村文化人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