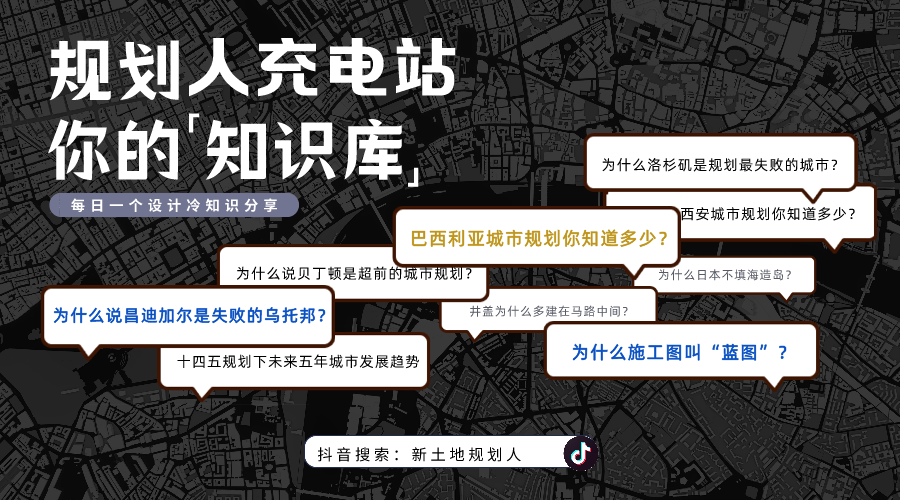
基于治理理论,从中央—地方以及政府—市场关系维度,分别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在国家治理变迁影响下的演变历程与总体趋向。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面向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变革与治理体系重构的举措,但是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再建构还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1)充分理解“国土空间”的多元价值属性,重视国土空间规划对多元目标的统筹平衡,不能把空间简单化为“自然资源”载体,谨防规 划蜕化为单纯的“资源环境管控技术工具”;(2)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建立与政府事权相对应、层级差异有序的空间规划体系;(3)高度重视规划研究和非法定规划的作用,为空间规划的科学 性提供有力支撑。
2018年全国“两会”做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中一项重要的变化是由 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统一承担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监督实施职责[1]。2019年5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 台,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这是国家在体制层面构建 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 举动。
从国际经验看,空间规划不仅是实现对空间环境进行“刚性管控”的有力工具, 也是实现“战略引领”的重要政策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上升到 了治国理政的高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空 间规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背景下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重 构空间规划体系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而言,此轮国家机构调整 以及空间规划体系重构都属于表象,而藉此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才是实质和关键。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并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必须基于国家实 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需求的背景。从这个角度来剖析中国空间规 划发展变迁与转型重构,也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PART 01
从博弈到整合:治理视角下解读空间规划体系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看,空间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于具有强政府传统并实行城乡土地公有制的中国而言,则更是如此。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空间规划领域出现了“多规并存”的现象,这些不同类型的空 间规划分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同层级、不同维度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将全国的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 体功能区,体现了国家对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意图以及对地方发展的控制和约束,从而完成垂直方向上中央—地方政府权利关系调整[3];土地利用规划则重在调整垂直的府际关 系,以及横向上政府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中央政府通过把控各级地方用地指标供给、 控制农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的转换,从而实现国家对土地用途的宏观管控及对地方发展 空间的计划管理[4]。城乡规划则重在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利益格局,作为“各种冲突 力量进行谈判、协调的方式”[5],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权利主体的诉求,对空间资 源的使用和收益进行综合分配。
这些“多规”实际投射的是不同权利主体的治理理念与目标差异。因此,前些年出 现并愈演愈烈的“多规冲突”,其本质上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部门机构之间的权利 博弈[6]。从更深层次看,“多规冲突”的乱象则是在国家治理体系转型过渡的特殊时期,治理逻辑混沌摇摆、集权与分权交叉反复的具体表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中国已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基本方向,并开始着手重构现代治理体系。中央政府在此时提出“多规合 一”,建构新的空间规划体系,本质上是对纵向府际关系与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 ——即垂直与水平治理体系的全面重构。由此可见,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对未来的政 府、市场和社会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也绝不能仅仅从行业内 部“技术工具优化”的角度来认识、思考,而必须兼顾实现统一与多元、效率与效应、 规制与活力等多重目标关系。
PART 02
发达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变迁的经验借鉴

“空间规划”广泛存在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中[7],但是各国的空间规划体系 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并不存在所谓通用的空间规划体系。综合考察英国、德国、荷 兰、日本等具有比较成熟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实践经验的国家,得出以下共同启示:
(1) 发达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普遍受到国家—市场—社会间关系及国家治理模式 变化的牵引,与各个国家的制度架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相耦合。例如法国作为单一 中央集权制国家,其空间规划体系更体现出中央政府的垂直控制能力,空间规划非常强 调国家与区域层面战略的实施及对地方的引导;而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的代表,其空间 规划体系受到政体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纵向分权特点,地方市镇规划成为规划体系的 主体与核心。
(2) 发达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普遍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变化、国家治理 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进行适应性的调整[8] (图1),从中亦可折射出各级政府、市场、社会 等多元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以英国为例,其空间规划先是在二战结束后国家凯恩 斯主义的主导下成为国家宏观调控、自上而下空间管制的手段(单一发展规划),后又在 1970年代末随着新自由主义、企业化政府的治理思想的盛行而走向“结构规划”+“地 方规划”的地方分权;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先后 影响,空间规划又经历了一轮从纵向分权到中央集权控制再到权力下放、地方规划权强化的反复过程。
图1 发达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历程——以英国为例
(3) 发达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层级清晰,与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分工明确对应, 中央政府重点强调宏观战略、指引的编制,地方层面则更多负责具体的发展任务安排[10]。 英国空间规划体系自“结构规划”+“地方规划”的两级体系形成起即确立了中央与地方 政府规划事权的明确分工,并随着“国家规划政策文件”+“区域空间战略”+“地方发展 框架”三级体系的形成而进一步完善;近年来,虽然规划体系层级下沉,“区域空间战略” 被废除,空间规划体系被简化为纲领化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地方发展框架”[10],地方层面的规划权力不断扩大,但各层级规划事权依然与层级政府职能清晰对应。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空间规划发展经验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 国家制度背景、发展环境的巨大差异,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的 模式,而是需要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模式、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等更加紧密地 契合,从而探索空间规划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PART 03
国家治理变迁下的中国空间规划演变总体历程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既长期受到中央集权传统的深刻影响,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11],改革开放以来尤为如此。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宏观背景 下,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在各个时期亦受到多元交织的时代环境影响,并与中央—地 方、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利格局息息相关。本文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视角, 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间规划的演变历程总体划分为五个阶段(表1):
计划经济时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空间落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刚经历过长期的战争洗礼,亟需稳定政治与经济形势、快速 恢复生产,因此在各领域全面效仿苏联,构建了一套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由 “全能型”政府制定并执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中央集权式国家治理体制。在经济领域,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制,自上而下形成对各级政府、整个经济部 门事无巨细的计划指令式管理,国家经济生产高度依赖政府对资源的调控和分配;在社会领域,则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来实现对社会群体与个人的高度整合和有效管理。
配合中央集权、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时期的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作为主 要的空间规划类型,成为国家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工具。在当时 的计划经济环境中,一切城乡空间的权利主体都是国家,空间所有及空间使用的权利也 均由各级政府或集体占有。在整个国家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中,区域规划、城 市规划都是从属于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承担着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行单向、被动 空间落实的功能,即空间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空间图解”。
“双轨制”并存时期:集权—分权交织的规划体系
1978年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启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随着对长期固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调整、放弃,在国民经济生产与消费领域中国家 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主体的作用逐渐增强,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完全支配的 局面不断趋于放松。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 谁主谁次的争议中摇摆,自上而下的管控和“计划”色彩依然还比较强 烈,因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独特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双 轨制”局面。
受到国家治理体系“双轨制”影响,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此时也表现出集权—分权 相交织的特征。一方面,空间规划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 的色彩,由计划部门牵头编制宏观层面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并藉此体现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的空间布局意图;另一方面,随着垂直计划性指令的不断弱化,地方发展的自主 性不断增强,各地市纷纷启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在其中着力体现地方的发展 诉求。到1988年底,全国的城市、县城总体规划已全部完成,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 市还进一步编制了详细规划和各种专业规划。由此初步构建起了从国家层面 (全国国土 规划) 到区域层面 (区域性国土规划) 再到地方层面 (城市总体规划等) 的空间规划 体系[12],尤其是1990年《城市规划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以城市规划为主体的、完整 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
“增长主义”导向时期: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工具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 ,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标志着中国从此转向外向型、 市场化的经济增长道路,由此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则在实质上 完成了中央向地方的行政性分权过程,加之此前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改革,此后的取消 住房福利化分配体制、中央提出城镇化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被赋予 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经济发展。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共同信奉,使得这一时期中国自上而下全面形成了以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目标、高度企业化的 增长型政府[13],掌握着土地资源的地方政府尤其如此,并进而演化成中国特色的“土地 财政”。
这一时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分权化的导向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心随之下沉,形 成了以地方 (城市) 为核心、高度分权的空间规划体系。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国土规 划、区域规划随着中央政府职能的改革而趋于沉寂,地方层面上基于增长导向的城市总 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快速发展,试图努力突破上位规划、法定规划约束的城市发 展战略规划等“非法定规划”也是风起云涌[14]。对于高度企业化的地方政府而言,空间 规划的角色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分税制带来的地方财政饥渴和土地财政 诱惑下,土地成为城市政府最为关注的“资产”[15],通过空间规划来超前、超值实现城 市土地经营以发挥其最大价值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于是,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开始更 多服务于城市经营、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市场资本的竞赛,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工具;而作为约束城市扩张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地方政府强烈的增长诉求 下则显得软弱无力。
“调控—刺激”反复期:多规冲突、多元体系并存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上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发 展粗放、生态恶化、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开始集中暴露。为了纠正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增 长的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目标, 进而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表达出中央政府的发展价值 取向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总体放权而导致的地方发展失序状 况,中央政府再度开始谋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管制的尝试。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家并 未形成清晰的治理思路,一方面中央政府既希望加强集中管制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受到 刺激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需求掣肘,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导致国家的政策在集权—分权、调控—刺激之间反复摇摆,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 死”的怪圈[16]。在广大的地方政府层面,GDP与财政收入增长仍然是主要追求的目标, 增长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时仍难以根本扭转。“中央统筹的目标”与“地方发展的冲动”之 间的拉锯式博弈,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格局。
这一时期受到国家治理政策反复、治理方向不清、治理体系不明的影响,国家空间 规划体系呈现出表面“繁荣”与内在“混乱”并存的局面,多规冲突,多元规划体系冲 突。一方面,空间规划作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此时获得了中央政府前所未 有的重视,长三角、珠三角、中原经济区等众多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相继出 台;而地方政府为了能够挤进国家的“政策包”,也纷纷努力将地方性、地区性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中央各部委间出于争夺话语权、资源分配权的需要,也争相推出并强 化各自的空间规划[17],如发展改革部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的 土地利用规划、国土规划,环境保护部门的生态环境规划、生态红线规划等,住房与城 乡建设部门传统的城市规划也拓展成了“城乡规划”。中国的空间规划进入了多规冲突、 多元混乱体系并存的“战国时代”。
层出不穷、相互冲突的空间规划,不仅无一可以成为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空间治理的有效手段,而且也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应对多规冲突的矛盾,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在矛盾最为集中的三大空间规划类型中,城乡总体规划的实际编制主体是地方政 府,更多地体现了地方发展意志;土地利用规划是对地方空间发展资源的严格管控,但是手段单一、“刚性有余,弹性不足”;主体功能区规划更多地体现了对地方分类发展的 引导,但是缺乏有关配套政策机制等实施手段 (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已经实 施)。加之各类空间规划之间编制时序不统一、技术规范相异、管理对象交叉、审批程序 相互独立等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在类型 构成、层级对应、事权划分、技术标准等方面都是非常混乱的。
治理体系全面重构期:多规合一与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 目标,首次在国家政治层面明确提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标志着中央开始着 手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全面的重构[18]。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关键,在 于针对中国国情统筹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建立起分层有序、责权清晰、传导有力、活 力充盈的治理格局。
习近平高度重视规划工作,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调整,中国的空间规划也迎来 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刻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 系”,并要求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2014年国家开始推 动“多规合一”工作,并在28个地区展开试点,探索建立空间规划的协调机制[19];2018 年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等空间规划职能统一划归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由其承担“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职责。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发布,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标志着国家空间规划体 系重构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土 空间规划将消除此前的多规矛盾冲突,实现空间规划的体系与职能整合,全面重构各级 政府事权,成为中央对地方发展进行有效规制的重要手段[20]。
PART 04
对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再建构的思考

人类社会进步过程总体上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 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逐步步入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已成为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深刻改革的重大 命题。基于此,国土空间规划既有别于传统以发展建设为主体导向的城乡规划,也不同 于传统要素单一、纯管控思维的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对空间规划理 念与方法进行重大的调整与重构。前一段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已经在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层级传导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技术性探索,但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国 家空间规划体系重构,既要实现诸多技术层面的整合、创新,更要促进国家实现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统筹多方面的目标,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 必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调适、完善过程。《意见》的出台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道 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与实施总体框架已基本形 成[2],但在此基础上,为了能针对中国的国情、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更好地对其进一步 完善,我们还需要在一些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
重视“国土空间”的多元价值属性,实现规划多元目标间的统筹平衡
古今中外的国家治理发展经验都表明,不论是政府、市场还是社会,都并不是万能 的,良好的国家治理体制离不开各主体的共同合作、协调平衡。国土空间作为一切自然 资源存在、经济社会活动开展的物质载体,实际承载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众多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因而同时具有了自然资源属性、资产与资本属性、人文社会属性等多重价值属性。国土空间不是纯粹的物质几何空间,而是现实经济 社会活动与需求的鲜活投影,也是充满人性、文化和活力的“场所”[21],空间就是社会[5]。而空间规划的角色功能在过去的70年中为了适应不同阶段的国家治理需要,也在 不断发生转变,尤其是历史最为悠久、发展最为持续的城乡规划,先后作为计划经济的 空间供给工具、迎合地方增长需求的工具,直至在2008年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 明确将城乡规划定位于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属性的确立,意味着空间规划 已经超越了空间布局管控技术工具的角色,而成为对空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进行统筹配 置的复杂治理活动[22]。这就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在面对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各自 利益取向时,不能仅仅追求单一的目标,而是需要调和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对多 元化目标的统筹平衡。
随着中国发展模式由过去的增长优先导向转向生态文明导向,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将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23]。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并 非简单、静态、绝对的生态保护,而是经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追求,旨在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的发展,是更高层面发展与保护的统筹协调。目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已被 确立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目标,以山水林田湖草代表的自然资源属性价值已 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提升,但相对而言,对国土空间所具有的人文社会属性、资产与资本 属性却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见物不见人”。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首先应基于对“国土空 间”多元价值属性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不仅需要高度重视对自然资源要素的有效保 护与管控,更需要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24]。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围绕国土空间规划所进行的大量讨论与实践探索,表现出一系列倾向性偏差,诸如高度重视空间的“自然资源”价值,而对空间的资产、资本价值重视不足;高度关注空间的静态特征刻画,而忽略了城乡空间不断发生的动态变化过程;高度关注空 间规划作为“技术工具”的功能,而对空间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关注不足;高度重视空间规划的“刚性管控”作用,而对空间规划的“发展引领”作用谋划不够。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要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最佳路径就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完 成发展阶段的升级,实现从资源驱动型增长向环境友好的品质、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型。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一度争论规划到底是“发展的敌人”,还是“发展的朋友”?最 终还是认同规划是发展 (而不是简单的GDP增长) 的“朋友”,规划是为了实现更好、 更可持续的发展。对于国土空间规划而言,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控固然是前提和 基础,但并非规划内容的全部,更不能将国土空间规划狭隘化为“生态资源保护规划”。
总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前提是对空间多元价值属性的准确认识,既要通过 对空间“自然资源”价值属性的强调,对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的“增长主义”所导致的问 题进行纠偏;也要充分认识到国土空间所具备的更广泛、更实际的人文社会属性、资本 与资产属性;而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目标应当聚焦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时代根本矛盾。必须超越“空间管控技术 工具”的角色,真正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全面理解国土空间规划的功能定位,统筹 考虑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统筹效益、秩序、品质的 关系,统筹长远目标与实施时序的关系。
建立与政府事权相对应、差异有序的层级体系
受到社会传统、政治制度、历史环境等具体国情的影响,各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 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面对愈加复杂的经济社会状况,无论是单一制集权传统的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分权传统的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求走向“计划 与市场结合”“集权与分权平衡”的新治理观[25]。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 中国必须跳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集权、分权”反复的怪圈,明晰各级政府、市场、社 会之间的权利边界,空间规划体系对各级政府事权、各利益主体权益的划分将成为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
应当正确理解中央对空间规划“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并 非是一种单一形式、一统到底的具体规划类型,而是一个由各个层级、多种规划类型共 同构成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国的现实国情是,由于资源掌控差异及政绩考核、税收体制 等的原因,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利益诉求和关注重点并不相同:中央政府首要关注的是生 态环境保护、国土开发秩序、可持续发展;市县地方政府首要关注的是地方发展、空间 开发绩效;省级政府则居于二者之间,必须上下传导、兼顾中央与地方的需求。对应不 同层级政府的事权,不同层级的空间规划内容、重点及表达形式等也自然应当有所差异。“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要求,其本质含义是要实现对国土空间管制的全覆盖,而不是用某种简单的、垂直传导的规制体系来统一辽阔国土上的所有空间规划,更不可能 简单理解成在数据平台上用比例缩放来绘制全国“大一统”的空间规划。
同时,也必须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权益与行为边界,统筹好集权与分权的有机 结合关系,既不能简单延续传统的计划管控思维,也不能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失 控。如果国土空间规划仅仅将有关的目标和指标进行自上而下的分解,实行单向度的严 格管控、层层传导,甚至在国家、省域层面即精细化地确定本应在市县地方层面确定的 具体规划内容,那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地方的发展动力与灵活应对能力,反而会使国家的 空间治理陷入僵局[26]。总之,建立起与政府事权相对应、差异有序的国土空间规划层级 体系,其本身就是深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科学的规划研究支撑国土空间规划
空间规划是政府实施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因此,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空间治理的水平。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指出,规 划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不言而喻,作为由自然要素、经济要素、社 会要素、空间要素等众多要素交织构成的巨系统,国土空间的发展规律极其复杂。如果 一味强调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环境的管控与刚性传导,其结果可能是空间规划的“权威 性”凸显了,但是空间规划的“说理性”“科学性”则被大大弱化。因此,大量深入、前瞻的规划研究不可或缺。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旨在建构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体系,但是“规划法定”并非意味 着只编“法定规划”,不进行非法定的规划研究。从西方发达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经 验来看,法定规划政策文件形成的背后都离不开大量非法定规划、规划研究的支撑和储 备。从此前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看,没有发展战略规划的前期研究,城市总体规划的一 些重大问题就无法明确;没有城市设计,就无法进行精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没有大量 的科学研究,就无法支撑许多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出台。非法定规划、规划研究可以作为 法定规划的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撑,是保障法定规划科学性、合理性的重要前提。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建构,仅仅关注法定规划类型是不够的,还要构架好规划研究、非法定规 划向法定规划转换的桥梁。在法定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要注重与相关非法定规划、规划 研究的沟通、衔接,使后者的成果、精髓能够顺利转化或融入到法定规划之中[27]。
PART 05
结论

随着中国发展步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矛盾考验着国家的治理水平。由于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国家制度等的不同,中西方国家治理的目 标、模式、机制、手段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体制、模式、经验 固然可以借鉴,但是不可能直接套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17]。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单一制集权下“治国理 政”,又不同于西方倾向政府分权、多中心治理、社会自治的思潮,而是要努力建立起一 种与中国实际国情紧密契合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这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作为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工具与公共政策,空间规划是各级政府、社会、市场 等利益主体围绕空间使用、收益权利关系进行博弈的平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空间 规划体系的变迁始终受到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如今在国家实现治理现代 化的明确目标导引下,中国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优化的问题, 而理当被视为国家对治理结构进行全面调整并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只有从这个高 度和角度来认识,才能准确理解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内涵与目标,把握空间规划发展的 基本方向,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两会受权发布)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8lh/2018-03/14/c_1122533011.html,2018-03-14.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PRC. Notes on the State Council’s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gra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14/c_1122533011.html, 2018-03-1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http://www. gov.cn/zhengce/2019-05-23/content_5394187.htm, 2019-05-23.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RC.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Establishing a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Sys-tem and Supervising Implementation.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
23/content_5394187.htm, 2019-05-23.]
[3] 孙鹏, 曾刚. 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的我国地域主体功能区规划解读. 改革与战略, 2009, 25(11): 95-98. [SUN P, ZENG G. On the development priority zone planning in China based on new regionalism.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09, 25(11): 95-98.]
[4] 王玉波. 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1(4): 73-79. [WANG Y B. On governing land use planning gaming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11(4): 73-79.]
[5] CASTELLS M.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Palgrave, 1978: 174-182.
[6] 林坚, 陈诗弘, 许超诣, 等. 空间规划的博弈分析.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1): 10-14. [LIN J, CHEN S H, XU C Y, et al. Game analysis of spatial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 (1):10-14.]
[7] FRIEDMANN J.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longer range.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04, 5(1): 49-67.
[8] HALL P, TEWDWR-JONES M.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08-155.
[9] NADIN V.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UK: From land use to spatial planning. http://hdl.handle.net/2099.2/1117, 2009-04- 23.
[10] 罗超, 王国恩, 孙靓雯. 中外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综述. 国际城市规划, 2018, 33(5): 121-129. [LUO C, WANG G EN, SUN L W. Research review of spatial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China and abroad.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8, 33(5): 121-129.]
[11] 俞可平.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 当代世界, 2014, (10): 24-25. [YU K P. Towa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ontemporary World, 2014, (10): 24-25.]
[12] 胡序威. 中国区域规划的演变与展望. 城市规划, 2006, 61(6): 585-592. [HU X W.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regional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2006, 61(6): 585-592.]
[13] WU 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79-118.
[14] 张京祥, 吴缚龙, 崔功豪.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透视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地方政府管治. 人文地理, 2004, 19(3): 1-5. [ZHANG J X, WU F L, CUI G H.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in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s. Human Geography, 2004, 19(3): 1-5.]
[15] 陈坤秋, 龙花楼.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2): 221-235. [CHEN K Q, LONG H L. Impacts of land market on urban-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 (2): 221-235.]
[16] 张京祥, 罗震东. 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65-166. [ZHANG J X, LUO Z D. New China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oughts.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5-166.]
[17] 何冬华. 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宏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对话: 来自国家四部委“多规合一”试点的案例启示. 规划师, 2017, 33(2): 12-18. [HE D H.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macro governance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 enlightenment from multi-plans experimental cities. Planners, 2017, 33(2): 12-18.]
[18] 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方向.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 (3): 4-10. [HU A G. Characteristics and direc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4, (3): 4-10.]
[19] 林坚, 文爱平. 林坚: 重构中国特色空间规划体系. 北京规划建设, 2018, (4): 184-187. [LIN J, WEN A P. LIN J: Re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2018, (4): 184-187.]
[20] 张京祥, 林怀策, 陈浩.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40年的变迁与改革. 经济地理, 2018, 38(7): 1-6. [ZHANG J X, LIN H C, CHEN H. 40-Year changes and reforms of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7): 1-6.]
[21] 杨保军. 城市规划30年回顾与展望. 城市规划学刊, 2010, (1): 14-23. [YANG B J. Urban planning 30 years: Reviews and prospect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 (1): 14-23.]
[22] 张京祥, 陈浩. 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城市规划, 2014, 38(11): 9-15. [ZHANG J X, CHEN H. Spacial govern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Urban Planning, 2014, 38 (11): 9-15.]
[23] 沈镭, 张红丽, 钟帅, 等. 新时代下中国自然资源安全的战略思考.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5): 721-734. [SHEN L, ZHANG H L, ZHONG S, et al.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ecur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5): 721-734.]
[24] 梁鹤年. 再谈“城市人”: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城市规划, 2014, 38(9): 64-75. [LIANG H N. Further discussion on homourbanicus: Human-based urbanization. Urban Planning, 2014, 38(9): 64-75.]
[25] 张京祥, 庄林德. 管治及城市与区域管治: 一种新制度性规划理念. 城市规划, 2000, 24(6): 36-39. [ZHANG J X, ZHUANG L D.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for city and region. Urban Planning, 2000, 24(6): 36-39.]
[26] 谢英挺. 基于治理能力提升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规划师, 2017, 33(2): 24-27. [XIE Y T.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 Planners, 2017, 33(2): 24-27.]
[27] 李和平, 余廷墨, 张海龙. 非法定规划的实践价值和技术策略. 规划师, 2012, 28(1): 61-65. [LI H P, YU T M, ZHANG H L. Non-statutory planning’s value and techniques. Planners, 2012, 28(1): 6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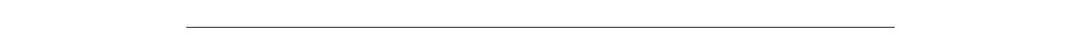
文章来源
国际城市规划
作者:张京祥 夏天慈
编辑排版
中规建业城市规划设计院 信息中心
CONTACT US
合作/投稿/转载请联系
xjxtd@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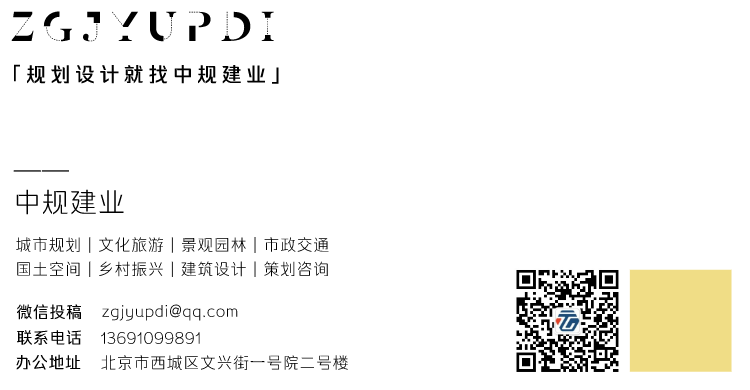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土地规划人):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变迁与重构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