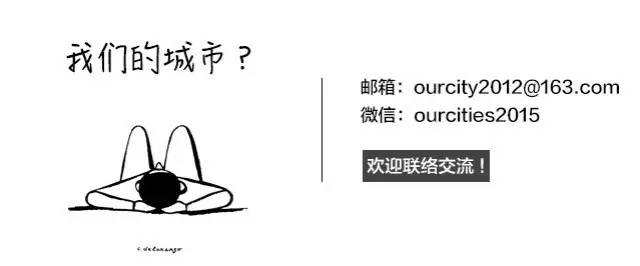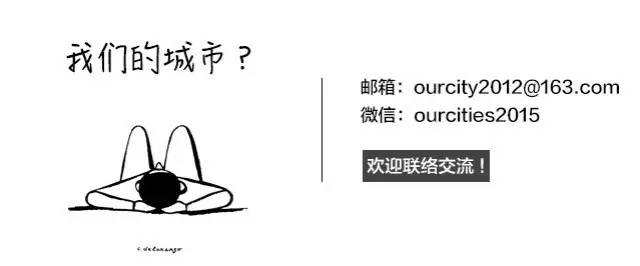书店是我们从小就开始逛的地方,熟的不得了,闲扯也可以扯出一堆话题。但是,大家可曾想过,如果禁止谈“我就是爱纸质书的那种触觉、那种在春日夕阳微风下打开书页的享受”等很私人的体验,那么关于书店,我们还能谈些什么?
前一阵,我参加了出版社举办的一次研讨会,讨论“理想的学术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想”。三个小时的发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名是:王云五、袁行霈、陆灏。王云五时代的商务印书馆,无可争议地代表了学人和出版人心中“理想的学术出版”。袁行霈建言总书记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的偶然事件,蝴蝶效应般有中国特色地促成了大量出版资金资助翻译出版。“四书五经”等等典籍的大规模翻译会制造文化盛世还是文化垃圾,与之相关的是“项目书”概念——花三五万块的项目经费就可以出版的学术书。陆灏主编的《上海书评》,则因为敢于为学术书挑错的批评精神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可。
今天,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不可复制,《上海书评》的成功不可复制,大项目、大垃圾的灾难亦不可复制(去年我国发行图书的品种是25万种,学术书2.5万种,但好书有几本?),一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的不再、左岸等上海最有特色小书店的倒闭,这几个名字(更多是与他们有关的事情)的在场与缺失,亦代表了书店业/出版业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书店,全世界的书店都有类似的问题。去年,在地铁阅读文化最发达的英国,独立书店倒闭的速度是每周两家。
你我不高兴,书店也不高兴。无奈的背后,是一连串亟待思考的问题:
在今天市场化的出版中,如何进一步提高与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学术出版是否应该设立最低门槛?
在出版产业格局变动、学术出版盈利艰难的生态下,认真的学术出版如何面对不规范竞争与所谓的学术畅销书?
上海有特色的小书店不断倒闭,像渡口那样开得下来的小书店依赖的是“人以店聚”而非从前的“人以书聚”,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上海的书店文化本身就没有问题吗?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与书有关的文化变迁?
和教育等智力产品一样,书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市场化。但一直以来,书业一直在努力让公众将这一产业和其它产业区别对待。书店,作为介于文化和商业之间的场所,通常意味着激发想象的地方,它本身具备重新定义“效率优先”、“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的可能,却为资本所收编;书商,带着文化理想来做商业,却在商业的影响下,以咖啡、签售、社交等功能成功地将书店定义为消闲场所;文人团体,作为文化使命承担者,本身具备克服消费文化的能量,却主导流行时尚,引发社会效仿;书店文化消费者,本身具备反抗的精神和动力,却满足于消费……
不管是出版业还是书店业,数字化网络化为产业带来的变革恐怕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局外人,我们“危急时刻的文化想象”可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