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文 | 谭啸,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浙江省西南山区,山多树密。车子在绵延曲折的盘山公路上行驶,一路上竹林密布,溪水碧绿澄净。
从丽水市区出发两个多小时后,柳暗花明忽一村,一个世外桃源豁然而至,那便是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
沿
坑
岭
头
沿坑岭头是小港流域枫坪乡境内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县城西南部,距松阳县城60公里,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是松阳县小有名气的“画家村”。相遇她,需穿越松阴溪南侧群山的一个个皱褶。
她原本是一个沉静烂漫的村庄,只有在漫山的金枣柿成熟的时候,才会显得热闹起来。全村被180余颗金枣柿树环绕着,这些柿树有的站在茂竹丛,有的站在旷野中,有的就高高地站在屋后。

培根摄影
据当地人说,它们是叶氏一族为避战乱自松阳县古市镇迁居于此时带来的品种,自那时起,已有三百余年光景。它们见证了沿坑岭头的世事变化,像观众,又像沉默的守护者。
村中有两座叶氏祠堂,一家正堂悬挂“茂进共祠”匾额,一家悬挂“士开公祠”匾额,两个祠堂格局相似,对联都含迁居立业、家族繁衍之意,并以唐代道教天师叶法善为荣。

培根摄影
而今的沿坑岭头村无论秋冬都非凡热闹,这源于一位来自附近城里一所高校的美术教师的到来。
到枫坪乡担任农村指导员的他,在沿坑岭头村写生时,发现了这里满村的金枣柿树和未被破坏的生态。他通过个人画展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写生者,激活了这个小村庄的生命力,促使政府改变整村搬迁的计划,决定对沿坑岭头进行合理保护和有效开发。
这也让原本隐于小村的制鼓传承人叶关汉开始为外界所熟知。
巧
手
制
鼓
叶关汉,浙江松阳人,现年65岁。他住在枫坪沿坑岭,年轻时便跟着师傅学做鼓,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在叶关汉家,院子和屋内几乎摆满了牛皮、木条片、半成品或刚刷上漆的鼓。

在村里,只要随“咚咚咚”的敲打声沿路而行,就能寻到叶关汉和他的制鼓作坊。

叶关汉的鼓里里外外全都是手工制作而成,鼓板杉木,鼓面牛皮,细处削竹成钉,这样的鼓据说可以用上四五十年。

一面鼓的制作,包括选材、刨板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首先解板。就地取材的杉木是做鼓身的好材料。根据鼓身大小,将木料锯成不同弧度的木板,再把杉木切割成弧形烘干。

南方多潮,梅雨季节过后才能将木片拼接起来制成鼓腔。坚硬笨重的木材在他手中如柔软湖水,随形而就,自成方圆。
再经烘烤定型,用胶水粘成圆形,绝不能有空隙,不然就得返工。之后要经过抛光、上腻子、上漆等工艺,一个初具雏形的鼓腔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就是鞔牛皮了,这是制作一面好鼓最关键的地方:“要选用本地优质新鲜的黄牛皮,外表的牛毛要有光泽、均匀、多而密,内层不可以有屠宰时造成的刀伤。”
叶关汉说,他不知道市场上卖的鼓皮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总之不是很符合自己对鼓皮颇为苛刻的要求:一定要用黄牛皮,不同材质做出的鼓,声音是不同的。只要听说临近村庄有黄牛皮卖,他总会登门抢购,拿回家裁剪、晾晒、囤积。

制鼓时,要将干皮取出,用清水浸泡,少则五日,多则十数天,直到柔软且富有弹性才能使用。
绷鼓皮时,要用麻绳穿过牛皮边缘的开孔,固定、拉伸、绷紧,一般两三天才做完一面。

做完这些,就要爬上鼓面踩鼓皮。这是为了让鼓面绷得更紧,声音更洪亮。
再用细细的竹钉固定,小鼓面120枚,大鼓面近800枚。这一工序既考验技艺,又需要耐心。
叶关汉说,光将竹片削成1寸左右的钉子,再用茶油翻炒硬化,也很费工时。


“所有材料齐备,从开工到成品,需十多天时间。”
叶关汉说,鼓的需求量少,从前祠堂、庙里会用一些,松阳高腔戏曲班社会买一些,加上制鼓费时费力,一直以来,他只把制鼓当成副业,在有人订购或农闲时,才会动手做上几个,赚点小钱,顺便满足下手瘾。
情
之
所
钟
“现在不一样了,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邻村、邻乡办民俗活动也越来越多,所以鼓卖得越来越好,凑到节庆活动,我还要赶工。”
在叶关汉这20多年的制鼓经历中,这几年是最忙碌的,几乎每年都能卖出大大小小的鼓50来个。

叶关汉不善言辞,说普通话的时候甚至有些结巴,但话语间始流露着一种质朴的执着,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就像常年居住在村里的其他村民一样,他明白外面的挣钱机会更多。然而出于对做鼓的热爱,出于对黄土地的眷恋,他们选择成为一个不离不弃的守望者,在故乡默默耕耘。

大概很多匠人都是这样,貌似普通却身怀绝技,择了一事便终其一生,在城市的一隅坚守着,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风霜裂变都留在了手上。

匠人们像扫地僧般深藏不露,又如苦行僧般甘于寂寞。有多少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怀着敬畏之心,把事情做到极致?
他们中总有人“一不小心就干了22年”。
但越来越难的手艺传承,也让叶关汉颇感无奈。“儿女们都在外地,徒弟也没有,没人肯学,附近村庄也没听说有谁会这门手艺的。我就是自己喜欢做这个鼓,以后要是做不动了,有人想修个鼓,都难找到人喽!”

村里的柿子红了一度又一度,高腔的曲牌唱了一出又一出,沿坑岭头的村民也换了一代又一代。环绕村庄的金柿老树们则宛如守护者,守着这个村落一直屹立于此,不惧风吹雨打。
也许,不久的将来,这门手艺终会在叶关汉的叹息声中消失在沿坑岭头。又或许,它会相逢知音,再发新芽。

乡村 | 文化 | 社会 | 公益
RCRA
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
志愿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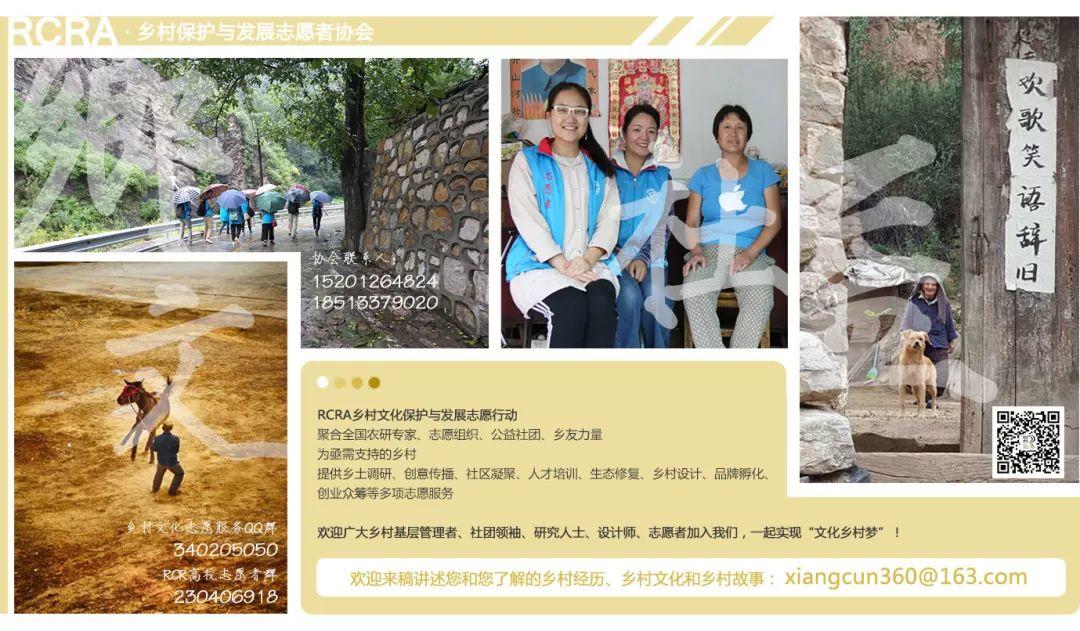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