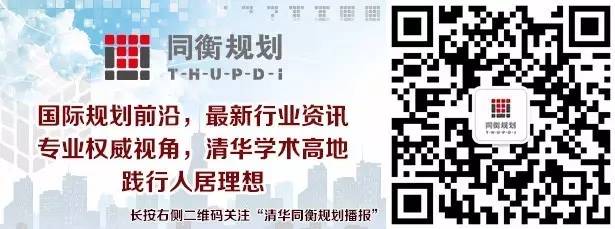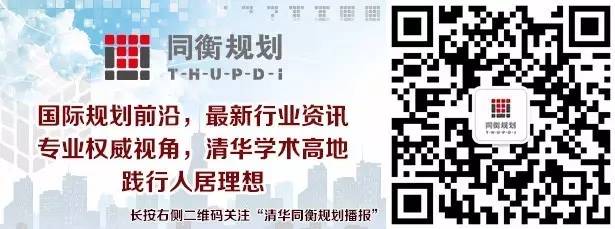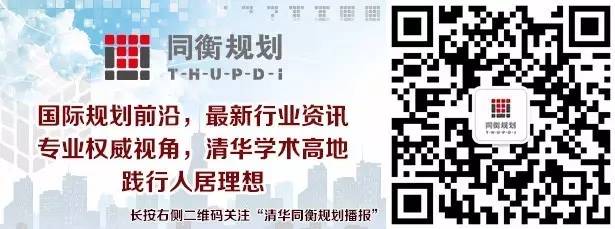2016-07-13
分类:人文空间
阅读(88) 评论(0)
北京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这张“金名片”,使城市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近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做客北京城市广播FM107.3“城市零距离”栏目,围绕这一话题与公众展开对话,本期内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权威解答。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北京的历史已经走过3060年,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北京也担得起“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您走在北京哪些地方会让您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印象特别深?
张杰:北京在相当一段时间作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国都,紫禁城、天坛等和皇家相关的地方,还有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地方——胡同,都反映了北京文化非常核心的部分。对于世界上只要知道北京的人来讲都是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风貌或者说城市的印象,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讲,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感受。
主持人:10年前或者20年前和今天去这些地方时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张杰:我觉得变化还是非常大的,1991年我到清华大学工作时,老城很多地方还没有改造,基本上保持80年代或者说70年代老北京的状况,多数胡同虽然比较拥挤,但保留了很多50年代以前的老四合院。在任何一个胡同中,大家的贫富状况没有差别很大,胡同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大家都比较在意,所以相对来说,胡同的公共环境维护可能要比现在好很多。但是现在胡同衰败的迹象很严重,这是这一二十年我感受比较深的变化。
张杰:发生变化当然离不开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任何城市都是这样。巴黎、伦敦、柏林、巴塞罗那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也都反映着他们国家随着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要发生的变化,北京从它的内涵上讲城市功能可能发生变化。虽然我们国家的行政中心还在老城里,但是其他的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再比如说很多四合院的居住人群发生了变化,有些四合院以前可能是居住现在变成了公司等等,这种变化很多。
主持人: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中有一个就是全国文化中心,您觉得怎么理解文化的概念和范畴,才能和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当中的文化中心最吻合?
张杰:习总书记对北京四个中心的定位非常准,我个人认为,对于北京来讲,它作为文化中心跟其他三个中心的职能的关系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而且有非常大的互动性。
首先,无论从现状还是北京的条件,它作为政治中心是毋庸置疑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以及最高的行政机构等。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北京本来就是国都,元明清都是国都。它保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不光是从物质上能看到的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文化的积淀。我们都知道民国或者晚清有很多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比如说上海、天津等,但是作为文化中心,北京从来就没让出过这一席之地。对文化中心我的理解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几千年文化没断脉的一个文明,在北京的传承显然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非常重礼、重文,北京在这方面的积累显然也是其他任何城市不能比拟的。我们去一趟国子监,就能看到那些刻有翰林院士名字的碑,它们记载了各个朝代的文化精英,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脉络。
最后,北京作为国都,长时间积累的民间的、地方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近现代以来北京作为国都和文化中心,积累了很多能量,很多潜在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北京作为文化中心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现在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或者说民族与民族的竞争实际上就是说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和文化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北京几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积淀都是重要的资源。
主持人:历史文化名城一方面需要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护和传承。很多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觉得北京面对这个课题有难度,您觉得难吗?难度系数有多大?
张杰:难度系数一个具体的数字我可能给不出,但是确实相当难。
首先在观念上,全社会应当确立一个城市的保护要从一个单独的房子保护做到一个区域、一个面保护的观念。梁思成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奠基人,上世纪50年代那场争论——“北京是不是应该完整的保护一个古都,开辟一个新的区域建设新的行政区、工业区等”。从狭义的概念来说,保护一个城远远地难于保护一栋房子。今天我觉着需要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居住在四合院里的老百姓、或者旅游者、或者政府某一个主管部门等,要树立把一片胡同或者把不同的胡同和整个城市连在一片来保护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中国城市历来注重山水,北京城作为中国古代城市一个非常典范的城市,过去周边的水很多,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山。习总书记讲“看山、见水、乡愁”,实际上非常精略地把城市的文化概括起来,所以一栋房子、一个城区的保护不要忘记城外的山山水水。城市的保护从房子到整个城,从整个城到整个区域的山山水水来保护,这个观念的确立仍然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北京城是全世界最美的城之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城里就有山有水,这种城在全世界是不多见的。
主持人:国际上有没有哪些城市成功地肩负了这样的一种定位?它在建设与发展、保护与传承做的很不错,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张杰:欧洲历史悠久,城市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存在。你可以感受到,这些在国内的城市现在感受比较弱甚至几乎荡然无存,应该说北京这方面还有很多地方是不错的。
我认为国外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城市要有一个整体的风貌。保护古都风貌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几十年了,但是的确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北京是一个水平展开的城市,中间的景山、前面的皇城是比较高大的,然后其他的民居是灰色的、绝大多数为一层,同时在这些灰色的民居中还有一些高级高一点的国家政府部门,比如衙署、庙宇等。所以实际上北京过去的风貌是以皇城至高无上的统领地位加上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宇、王府这些有一定级别的建筑为骨架,其他就是老百姓的平房。这样一个格局是北京曾经存在过的,今天在某些区域我们还能够体会到,但已不完整。
巴黎的整体风貌保护是非常出色的,如果到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山上,在圣心大教堂往南看,巴黎的普通建筑多半是公寓式的,它们基本是5层到7层高。高出这个高度之上的基本上就是大的教堂或者政府的重要机构,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它高出其他建筑很多。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不同时代“长出来”的重要的公共建筑。在较高大的公共建筑周边会有一个“平的基底”——一般普通建筑扮演着配角。这样的结构反映着巴黎的构建历史的积累,后来巴洛克时代做了一些轴线把很多重要的公共建筑连了起来。所以,从平面上讲,巴黎城市有主要的街道、广场,而广场会与教堂、重要的公共建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结构和风貌。
第二,保护整体风貌要有强有力的规划控制。城市规划对建筑的高度都有规定,我们不能随意找个理由就可以再高一点。任何国家保护古都风貌高度控制都是第一位的,比如日本京都,它的老城区域控制在12米高,老城南边可以建设现代化的建筑,30米高,两个高度控制就管住了。
北京原来是四合院,有非常重要的胡同文化,这些怎么能够和今天的生活相关是现在保护胡同大家争议比较多的。这个话题如果放在50年代和今天会不一样,即使50年代面临的也是四合院,但那时不是大杂院,房子也没有长年失修。今天讲这个问题,有四合院的问题还有胡同的问题。在过去六、七十年对于住宅尤其是老城住宅的欠账过多,房子长期低租金、越住越挤、没人修。我们对四合院和胡同欠的六七十年的帐。今天还这个帐怎么还?一个是保护,很多好一点的四合院如果里头都搭棚子是没法修,也没法去保护。但是大杂院的人要迁出去,谁愿意迁出去?谁不愿意走?这里又有一个社会的矛盾在里头。
习总书记2014年去胡同视察时随机地问了三家老百姓,有两家说愿意留在这儿,一家愿走。一方面,愿意走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机制使这些老百姓的生活不受特别大的干扰甚至不受干扰,生活不能改善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愿意走?另一方面,愿意留下的人,我们可以再去做更细更全面的调研。有的老百姓会问是不是能够就地上楼?这又跟保护产生了矛盾。所以四合院的保护、社区的传承、居民的利益等,这些矛盾的解决的确是需要非常高的社会共识和政府工作的力度。要让居民各道实惠,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调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
网友提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关键得摸准城市的特色与风貌,保护北京特色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杰:我认为抓住北京是国都这一特点是非常重要的。梁思成先生勾勒出北京是以紫禁城/中轴线为统领的一个水平展开的城市。北京作为一个国都,除了紫禁城/中轴线外 ,过去还有城墙和城门作为统领,其余水平展开还有很多庙宇、王府等公共建筑以及北京的山水,所以北京有很多制高点,这些是北京作为一个国都、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要保护好这些除了紫禁城之外的重要文物,比如白塔寺,它是城市的制高点之一,但是白塔寺周边有很多民居,把这些重要文物周边的环境控制好、保护好,是辅佐于以中轴线为统领的城市非常重要的一环。
此外,城市发展历史是叠加的,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所以大的结构下,城市有很多不同时期的信息。比如前门区域有很多民国、西洋的建筑,它肯定是北京的,但它不是典型的清朝或明朝的北京民居,所以要有历史包容的心态来把历史沉淀下来的这些丰富内容都保留下来。
概括一下,北京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轴线和中轴线周边的重要文物点、街区以及它们形成的整体,另一个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真实的东西,它们对保护特色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提问:埃及开罗、意大利罗马、威尼斯这些城市的历史气息感觉特别浓厚和鲜明,但是北京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为什么?
张杰:从全北京来讲,还是有一些能反映老北京文化和风貌的地方。北京人口过于拥挤,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舒适的环境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前提。所以如何使老城能够有一个基于四合院基底的合理的居住密度,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上,这都是需要的。
其次老城很多地方基础设施非常差,胡同里基本靠公厕来维持日常生活,院子里有厕所的极少,更不用提一家一户的冲水马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北京旧城区有62平方公里,现在至少有20多平方公里是平房保护区,或者说控制区,这个区域基础设施的提高和千家万户的生活关系太密切了。
主持人:北京的发展当中,曾经也有一些规划的实施,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规划保护区域划定建设控制地带……现在回首来看,这些保护成果,您满意吗?
张杰:和房子相关的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就是和“拆”相抗争的一个结果。对于北京过去整体的风貌和它蕴藏的特质的东西的保护,多数人都觉着有很多遗憾。政府划定了保护对象后,还要有很多后续跟进的政策、法规以及所有管理配套的东西。保护应该以什么样的机制进行?市场的机制显然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以财政的机制来保护?但我们要意识到,政府财政还要解决很多其他社会福利问题,如养老、教育等。所以如何做,现在矛盾比较大。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胡同、还是整个老城的保护,我们需要创新。首先政策上要有共识,并把这种共识变成行动的共识。
有了这些保护的概念后,保护工作就真正令人满意吗?答案是,远远不够。发达国家有很多法律层面的配套政策,比如说税收方面,你投入老房子做维修,用的得体可以免税,甚至到银行去可以贷款,贷款可能是低息、甚至是无息的。还比如,在国外有一种文化彩票,每两周开一次,像英国文化彩票的收入的15%是用于文化建设,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修房子、保护历史街区。
主持人:在建设和发展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之下,怎么样更好的实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核心还是文化牌,怎么打好这个文化牌,请您谈一谈自己的建议。
张杰:结合中央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要区域协调发展,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北京放,有一些功能要从北京疏散出去。北京的四个中心任务实际上都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文化中心,北京很多遗产要素怎么来保护好、利用好,能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我心目中,一个保护好的北京,它深厚的历史底蕴能够让我们一天有一天的感受,待十天有十天的感受,住十年有十年的感受;同时作为日常生活的城市,我们可以在很多从不起眼小事中体会它的韵味。
本内容由清华同衡 科研与信息中心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欢迎公众投稿,投稿邮箱:info@thupdi.com;请在标题处标明“微信投稿”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