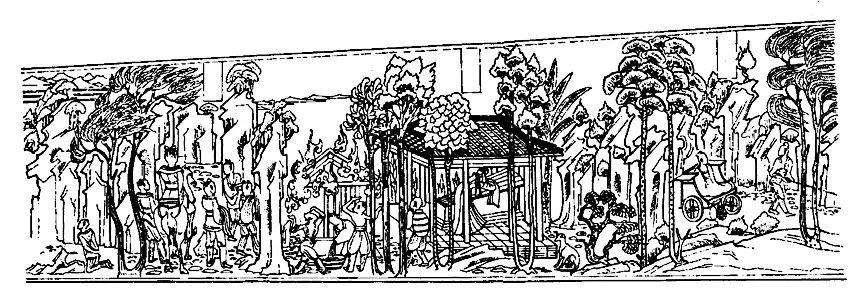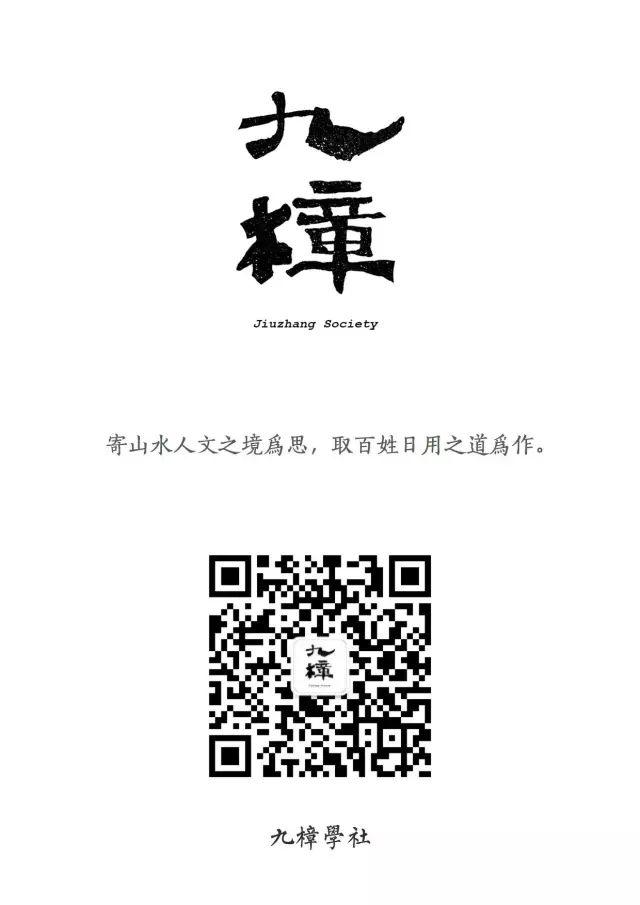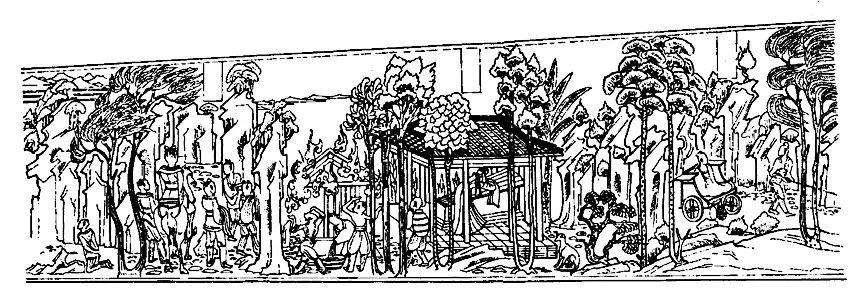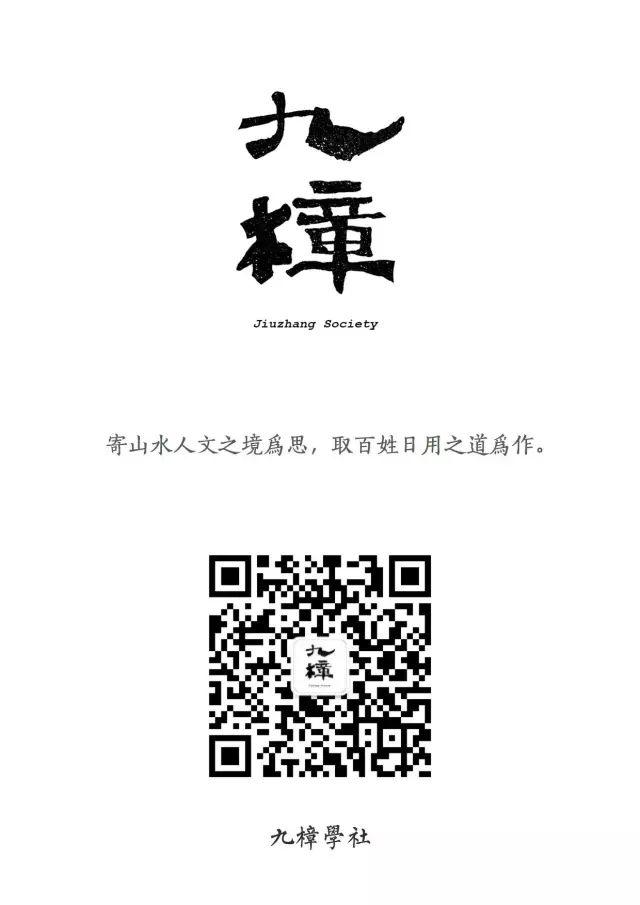萧纲(503―551),字世缵,为武帝萧衍第三子。由于同母长兄萧统的早逝,于中大通三年(531年)继为太子。随着萧纲入主东宫,其与围绕着其身边的文学侍从(兼及其异母弟萧绎)的诗风流行一时,唤作“宫体诗” [1]。其下一首便为萧纲所作,描述了梁室宫苑中一处(南庭)之景色。
[1]:田晓菲言道,“第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词。准确地说,‘宫体’这个词专指萧纲及其宫臣在六世纪三至四十年代所写的诗歌,‘宫’特指‘东宫’,皇太子居住的宫邸。第二,‘体’的意思是‘文体’,也即是说一种诗歌写作的体裁和形式,和诗歌内容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
▼
[2]:谢惠连乃谢灵运族弟,亦为南朝宋时著名诗人。
萧纲此诗气质典雅、描写精致,并且于叙述之中不夹带主观情绪,仅是就视觉性层面给出了一帧帧静态的画面,而诸多色彩用词的甄选给这一春日景象添上明丽的美感。
我意指的“静态”并不是说诗中描绘的画面都仅于时间线上占据一点,事实上它们都绵延了完整的一段,但是在每一个描摹的场景中都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有在画面切换的时刻时间才开始流动,然后,复又静止。
这一观念可以从萧纲对于落日与日影的描述中有所体悟,“落日斜阶上、日影去迟迟”,凝固了的场景、静止了的时间,这两句仅仅是说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日暮之时,而不意在表达动态时间的流逝,更不在于发表时光将尽的感慨。
相同的例子又见萧纲的另一句诗,“幔阴通碧砌,日影度城隅”。帷幔投下的阴翳拂过碧玉台阶,而日光的影子经过了城墙一角。“通” 与 “度” 表达了一种动态的过程,然而阳光偏移的缓慢使得这一时间被拉伸得十分冗长,切分成局部的片段后,场景变显得毫无动感而近于静止的沉谧。
此般描述的选择与身处于宫苑之中的萧纲自身心态的平和有着紧密的联系。反例可见南朝齐人谢朓的诗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谢朓彼时因受谗言而仕途失利被迫返京,此诗正作于返程,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诗人心中因悲愤难已而产生的剧烈波动。
而有关静态的时间感的描摹也反馈回作为诗人(或言之为诗中主角)对于身体状态的选择之上,田晓菲解释道,“因为身体的静止,诗人反而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世界”。
春风复有情,拂幔且开楹。开楹开碧烟,拂幔拂垂莲。偏使红花散,飘飏落眼前。
诗歌中隐匿的地点无疑是室内,而主人正静坐其间,春风似是别有情谊,吹动了帘帷,室内香炉的烟气因而飘散出去,拂过莲花的帘帷击散了花瓣,荡落于主人眼前。
珠绳翡翠帷,绮幕芙蓉帐。香烟出窗里,落日斜阶上。日影去迟迟,节华咸在兹。桃花红若点,柳叶乱如丝。丝条转暮光,影落暮阴长。春燕双双舞,春心处处扬。
庇护于室内的观察者将视线由近及远地向外缓推,分别落眼于:张拉于楹间的珠帷、从室内溢出到室外的香烟、斜斜地映照在石阶之上的日影、艳红若点的桃花、风中凌乱如丝的柳叶、在暮光中影子越拉越长的细枝条以及成双舞动的飞燕。
日暮时分用膳完毕本应心满意足,身处室内的主人却似仍难忘心中愁思 [3]。
[3]:刘燕歌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古诗歌中的自然描写》中认为此诗“将景拟人化,使其成为侵入女性生活空间的有情物”,而诗中的主人自是独守闺房的女嫔,所怀之愁思实乃“春日思念、伤感、孤寂的缠绵情思”,谨作一说。
我们可以看到,萧纲在描写庭园时着眼于多样景(物)的刻画之上。然而在诗人对于具体的景(物)进行凝视时,它也就自我封闭了,而安乐哲与郝大维这样说道,“由于各种事物之间具有流动和变化的边界,对于任何特定的事物来说,完整性都不意味着静态存在的整体,甚或是其自身内在潜能的现实化。或者说,完整性是始终在同其他事物的共同创造性的关系之中成长为整体的那样一种东西。完整性就是圆满的关联性”。萧纲并没有于本诗中就景(物)之间的关联性做出更多关注,因此即使他描写了不止一样的景(物)也仅仅是纯粹的罗列而已,精美的描述反映出来的是一幅幅互相孤立的静态画面而缺乏时间感的置入。
田晓菲可能并不会认同我的判断,她认为,“一首宫体诗所呈现的不是由各种不同的物象拼凑而成的版图,而是具有一个中心,诗中的一切因素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运作”。
田氏太想批驳过往对于宫体诗是乏味的静物画的观念而努力地去挖掘诗人们的哲思,却近于牵强。我自不会认为萧纲于本诗中描摹的画面乏味,反而惊叹于诗人独具的“赏心”,平凡的事物通过诗人独具的视角而展现出别样的魅力,于诗人的文字流动间变得异样鲜活。这无疑也是极具价值的贡献。
– 余论 –
顾彬对于齐梁诗歌背后的园林发展趋势作如此总结道,“自然的园林化出现于从齐向梁的过渡时期,在园林艺术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繁荣之后,人们开始按山水的格局仿造自然。随之出现了在隐逸与自然观方面的一个新变化。荒野的自然作为退隐之地、散怀之地和寻药求仙之所现在被私人园林所取代,在这里美妙的大自然作为个体进入了人的意识之中。与此相应的是一种‘漠然’的享受——多是在欢乐的、无拘无束的聚会以及花、鸟、风、月之中——如此便不再称‘爱山水’,而称‘爱泉石’或‘欣玩林石’。”
“……就是说诗人所爱已不再是整体的自然,而是自然中的各种单一现象这个变化与园林文化的发展有本质上的关联,因为园林文化再现了由各种单一现象构成的自然。”
这似可从上述萧纲的描写中窥见一二,诗中所着眼的是具体而分离的景(物)。我并不意图就诗歌内容作考古式地论断,这样的尝试显得徒劳。我想一作反驳的是,中国园林文化的妙处并不在于单一景(物)的多样化,而在于——就如安乐哲与郝大维所言——具体景(物)之间的关联性、景(物)被归拢进一组组关系场域之中。
有关此的“观看”于梁一代亦有所体现,具体地说便是对庾信所言“影来池里”的现象的偏爱与刻画。水镜的反照将外在的物象与水池结合在了一起,孤立的景(物)之间产生了扭结的关联。
《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七韵应司徒教诗》 王融[4] 南朝·齐
[4]:王融虽定为南朝齐人,但其实年幼于梁武帝萧衍以及沈约,并与二者共列席为“竟陵八友”。仅是参与齐宫政变失利而于27岁上被处死,未能入梁。
于个人的欣赏中,以上诸首皆不若庾肩吾(庾信之父)此首典型。
沈玉成对于此句作这般解读,“月光射到水面,水光又反映到石壁上,那悬在壁上的波光随着水波的起伏而跳荡,夜色朦胧中似是石壁在晃摇。远山上树木葱茏,那翠色似乎要流下山来,使江水更添几分绿意”。
沈老将“荡壁”理解为“石壁”,“山翠”看作是借自远山的绿意。田晓菲则将“荡壁”解释为“宫墙”,而把下一句拓展为“山翠倒映在水中,好像给池水增添了流量”。而以我个人的理解,更倾向于将“荡壁”看成土石相成的壁山(正如顾彬指出的,“提到‘山’时,又多指园林中人造的高丘”),而“山翠”亦不必来自远方,实为壁山之上栽培的绿植。
于是,观察者将目光从水面投向壁山,又从壁山回转至水面,视线不再若萧纲那首般做线性地延展,而是迂回的,水光的映射也使得山—水之间不再是孤立的分离,就如诗人感受到的,水光的晃荡倒像是山体自身在摇动,山—水已然难两分。这一句不似是在描摹景(物)了,倒不如说是一次叙事,于诗歌展现的“一念”,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与客体的山—水的形象互相映照,诗歌中绵延的时间也变得鲜活而具体。
庾肩吾于此句中展现的角度是我所欣赏的对于园林的一种“观看”。
-End-

作者:杨雍恩
编辑:孙欣悦
九樟学社编辑部
| 版权声明 |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
| 联系邮箱 |
jiuzhangsociety@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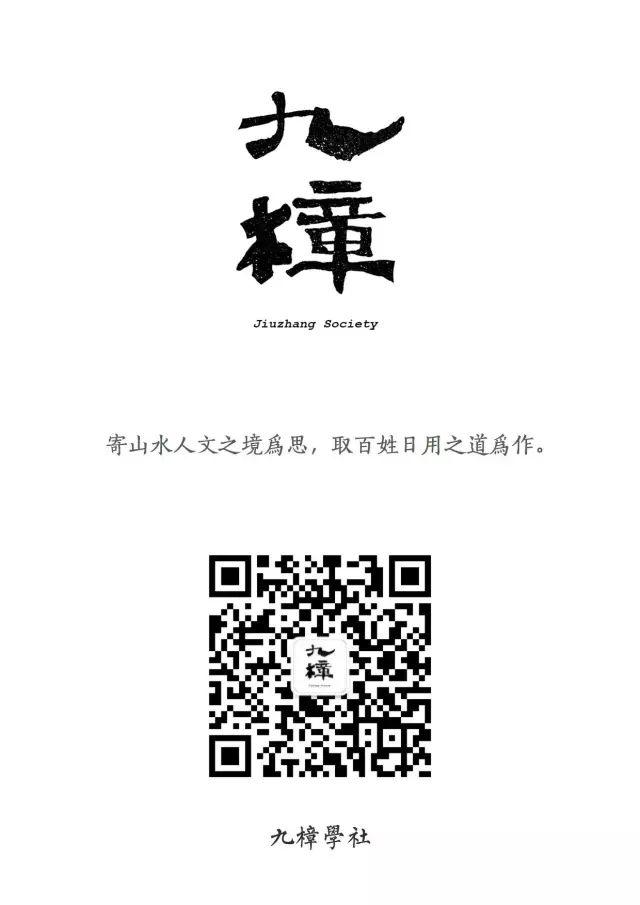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九樟学社):赏萧纲诗一首兼议水中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