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村的“万亩良田”

地戏(屯堡人称为“跳神”)自诞生之初,便与土地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仪式,高堂庙宇它不入;作为艺术,村中空地即舞台。而从意义来看,正月间“跳神”寓意迎春纳福,禳灾消难,七月间跳“米花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地戏关乎土地与村落农业生产,关乎村民一年的生计。
因此,对固守乡土、依赖农业的萧村而言,地戏的地位更是重要。文革“破四旧”时期,地戏作为“封建迷信”一度中断。村民们偷偷将地戏队的脸谱分头藏于家中,幸而躲过一劫。文革过后,地戏快速地恢复起来,萧村地戏队的规模达到20余人。每次演出,都有来自本村和周边村落的几百人前来观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并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足够的资本组织一堂“神”(即一支地戏队)。因此对村民而言,拥有自己村寨的地戏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地戏队员相当于村落的“文化精英”,受到村民热烈的追捧,“正月间每天都有几家人请我们吃饭”。

萧村的地戏脸谱
离土
然而,进入90年代,农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农业收入不断减少。萧村的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开始离土离乡,到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打工。萧村的地戏队员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跳地戏本身并不能挣钱,加上电视机逐渐普及,人们的娱乐活动更加多样化,喜欢看地戏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为了谋生,很多地戏队队员离开萧村到外地打工,七月的“米花神”就此中断。更糟糕的是,村落社会主体的大量流失,使得地戏的传承出现断层。十余年间,萧村地戏队员渐渐老去,至2009年,除了一名鼓师以外,萧村地戏队仅余3人,且都已年过花甲。
与此同时,依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村中的许多家庭将原来老旧的屯堡石板民居拆除,建起新式的砖楼。除了老妇人身上的“凤阳汉装”之外,萧村看上去与广大的农村并无二致,完全看不出其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其作为屯堡村落的物质文化表征所剩无几……

萧村中的新式楼房
村落社会主体的大量流失最终引发了地戏的“流变”,老年协会的出现改变了萧村地戏队的命运。
在过去,地戏队员均为男性,所用的脸谱需要“开光”。妇女和小孩不仅不能触摸象征着神灵的脸谱,甚至“连看都不让看”。为了保住村落的传统文化,2010年,萧村老年协会牵头成立女子地戏队。女子地戏队的诞生充满波折,先是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反对,认为女子跳地戏有违规制;后是部分妇女及其家人的观念比较守旧,认为妇女不应出去“抛头露面”。但经过老年协会、妇联等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选拔出16位喜欢地戏又符合条件的妇女。平日里,老年协会请来3位男队员担任她们的“教练”,帮助地戏队寻找资金支持,并出让协会的办公地作为训练场地。每逢参加比赛,老年协会不仅赞助服装、道具和设备,会长和骨干还会陪同参赛。
更值得注意的是,萧村地戏队并没有因为性别的改变而丧失其高度的神圣性。女子地戏队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她们所用的脸谱需要开光,并按照传统的时间,在春节和七月半“跳神”;若有人新房落成或者生意人“扫霉气”,就要请女子地戏队去“开财门”,取个好彩头。可见,萧村地戏队只是在性别上完成了一次“置换反应”。

萧村女子地戏队(翻拍自小吴记者)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性”、“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在农业大村萧村有着很好的体现。然而,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潮冲击下,基层社会的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型。当前的中国农村这种熟人社会,已经与从前那种强调“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的熟人社会有所不同。当村落社会主体中的男性大量流失,留守在乡村的女性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守土”与“离土”两股力量交织的同时,传统文化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
图文作者:许泳霞
编辑:庞兆玲、王思雅
图文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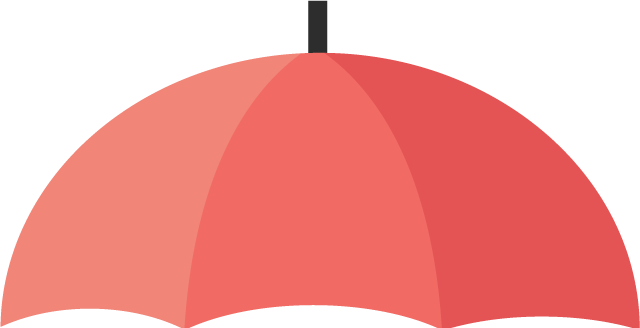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