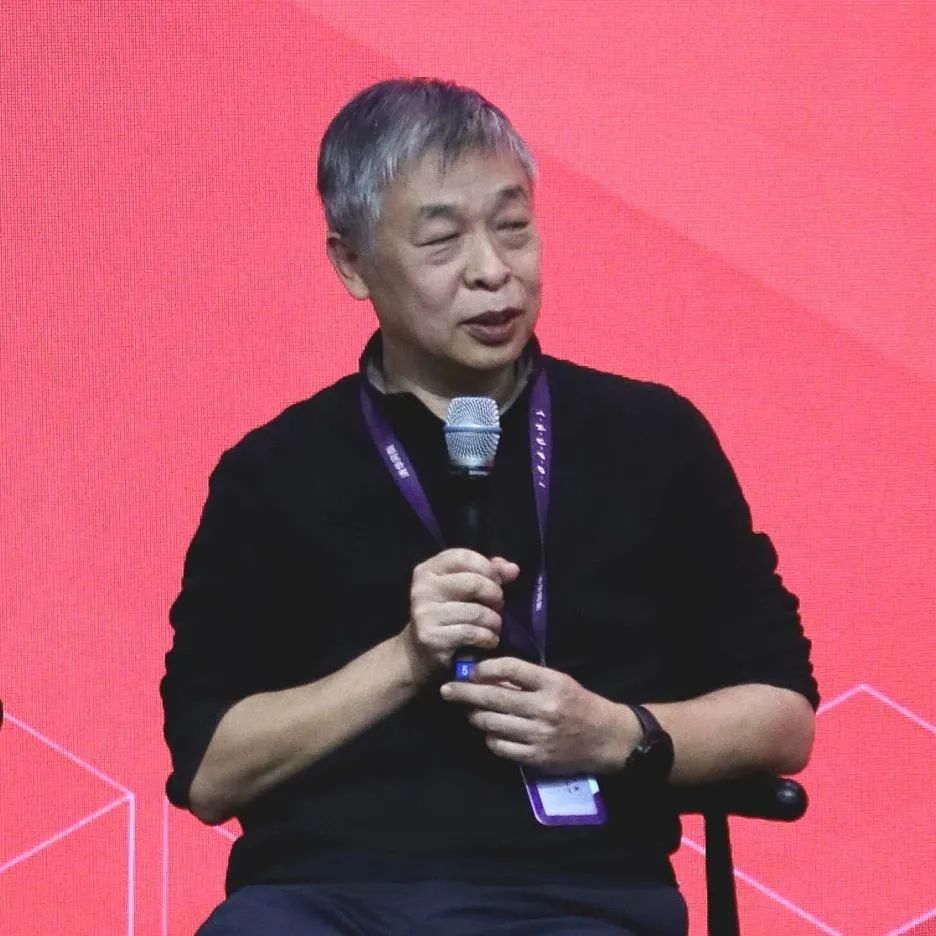导 读
2023年11月17日下午,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徐苏宁教授受邀出席我院“大师讲堂”系列活动,以《何以“诗意地栖居”》为题作主题讲座,并与清华同衡专家展开学术交流。讲座就如何理解“诗意地栖居”、如何营造“诗意地栖居”、如何使最大多数的普通人实现“诗意地栖居”等方面作了深入阐述。讲座结束后,徐苏宁教授与清华同衡专家围绕“诗意地栖居”开展了学术对话交流。本篇根据学术对话内容整理。
对话嘉宾:
徐苏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城市设计学部委员
袁 昕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专委会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袁 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风景园林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分会委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
张险峰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分会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委员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会委员
相秉军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长三角分院院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
江苏省城市规划协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对话主持人:
徐 刚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总工办主任、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专委会副秘书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委员

“
徐 刚: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讲座,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清华同衡的袁昕院长、袁牧副院长、张险峰总工程师、相秉军总工程师一起来探讨“诗意地栖居”这个话题。下面有请袁昕院长给我们总结一下。
“
袁 昕: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今天徐老师更多的是从“道”的角度讲我们规划师所从事工作的意义所在。我理解徐老师所谈的“诗意地栖居”是跟幸福相关,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都有各自不同的幸福,大家追求的幸福是多元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要求下,或者说是多元需求的考量下,徐老师提到的包括对私权利的尊重、对烟火气的营造等方面就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幸福都是细微的点滴累计起来的,而这个维度是我们规划师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诗意地栖居”我认为还跟经济基础是相关联的。回过头来想想诗人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及唐诗发展到巅峰的时期,都是经济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因此真正想要让大家有更好的“诗意地栖居”,还得有一个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背景。并且在不同阶段,不同层级对幸福的追求,或者是对有限幸福的追求都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我们的目标追求并没有设定到遥不可及的高度。当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在有限的目标上,才能感受到幸福的存在。徐老师的讲座在很多细节都给了我启发,就不一一展开了。
“
徐 刚:
非常感谢袁院长的总结,今天下午徐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永恒深刻,但是又很应景的话题。听完这个报告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一方面是“诗意地栖居”的追求者,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诗意地栖居”。但是同时在另外一个角度,从我们的职业身份出发,我们又是“诗意地栖居”的创造参与者。并且我觉得这个话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话题,它已经突破了技术理论范畴,更多的是一个社会话题。只有我们把“诗意地栖居”这个概念理解清楚,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去更贴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开始访谈之前我想增加一个小环节,就是请我们在座的这些同事每个人用一两句话先谈谈自己理解的“诗意地栖居”是什么?
“
现场观众:
观众一:
刚才听了徐老师的演讲,最主要的感受就是栖居是个比较容易达到的状态,但是“诗意地栖居”需要上升到一定高度才能达到的状态,不同阶段人对“诗意地栖居”的追求层次不同。而我比较困惑的就是我们作为“诗意地栖居”的创造者,在塑造人居环境、塑造社区的时候,是先着重于当前需求的满足,还是要始终把人居的理想生活状态作为唯一标准?
观众二:
非常感谢徐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深度的讲座,对于我个人来讲,小时候生活的那种有亲密邻里关系的大院就是“诗意地栖居”。同时也有一个问题想跟徐老师讨论,就是如何定义“诗意地栖居”,我们现在的很多案例都是以第三视角去看,但是对于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是不是觉得所生活的氛围是诗意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观众三:
结合徐老师的讲座我认为“诗意地栖居”从字面意思展开,就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把日子过的有韵味。但是诗也有很多种,有悲伤色彩的,有非常圆满的,所以不同的对象对于“诗意地栖居”也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对于我个人来说个人生活的满足感、舒适感就是“诗意地栖居”。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诗意地栖居”的创造者,在项目中要扎根基层,要研究每个人、每个对象的需求,统筹他们的需求后再做考量。
“
徐苏宁:
感谢坐在下面的各位同事所讲的感悟及所提的问题。今天讲的内容是我近期的一些思考,因为准备的时间比较短,很多问题还没有想到,所以讲的不是很全面、很准确。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比如说不同层次审美需求的问题,所有这些提问后续都将有助于帮我完善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到底该怎么理解,因此我特别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
徐 刚:
既然徐老师说他也很想听听大家怎么理解“诗意地栖居”,那么请几位院长及总工一起来谈谈这个开放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先请相总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感想。
“
相秉军:
我一方面非常同意刚才袁昕院长说的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才能够“诗意地栖居”。首先要栖居了,才会有后面讲的“诗意地栖居”。另一方面我想“诗意地栖居”应该是跟历史文化有关的。我认为从精神层面或者是从非物质文化层面来讨论这个事情可能更有价值或者是更有意义。在城市更新的环境中如何把历史文化传承下去是实现“诗意地栖居”的关键所在,当然所谓的历史文化可能也不能完全与我们现在做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里面的历史文化划等号,因为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历史文化保护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规矩,而我想说的历史文化应该是一种文化氛围的营造。比如苏州市吴江区的开弦弓村,放眼整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苏州,开弦弓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这里既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也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更没有出过家喻户晓的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它如同中国绝大多数的村庄一样。然而,它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乡村,社会学家费孝通1936年在此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江村经济》,开弦弓村自此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标识,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首选标本。很多游客觉得居住在这个村庄里是“诗意地栖居”,也是因为这个普通的村子被费孝通赋予的文化氛围。
每个人心目中的“诗意地栖居”就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栖居。比如说我居住在苏州工业园区,我认为它不舒服、不方便,苏州工业园区有“洁癖”,你看不到烟火气,它没有琳琅满目的街巷生活,消费需求得去集中的邻里中心满足。而我儿子出生长大都在苏州工业园,他觉得苏州工业园很好。回过头来再到我们的专业,我认为在城市更新里还是要保持各种的可能。
“
徐 刚:
刚才相总强调了历史文化在“诗意地栖居”当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要保留足够的包容,让更多人可以追求到自己心目当中的“诗意地栖居”。接下来我们请险峰总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感想。
“
张险峰:
今天徐老师的讲座先回顾了先哲们的思考,不管是东西方,让我们感受到“诗意地栖居”是由来已久的,是人类非常早就追求、向往的一种境界。其实人类在探索世界的进程中一直在探讨这个东西,包括乌托邦、一些原始的规划理论,无外乎就是技术、方法不一样。从个体来讲,我们完全有自由的发言权,但是我们的另外一层身份是规划师,站在这个角度我们需要思考自己有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诗意地栖居”的坚守?如果连我们规划师都不能坚守,那么谁还能坚守?所以这是这次讲座给我最大的启发。
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很多人也在谈“人民性”。而以人为本中这个“人民”代表谁,是值得大家思考的。有没有把所有人,包括贫穷者都关怀好,这是我们作一个为规划师、一个社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别人可以做“小我”,但是我们要有“大我”的概念。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规划师要想清楚无为、有为、强为这三者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活动是“无为”的,比如很多公共空间、居住形式是自发地形成并被使用者赋予用途的。而“强为”就是强行的引导这个空间必须要干什么,这里面存在很多的主观判断。而“有为”与“无为”、“强为”不一样,“有为”恰恰是我们规划师需要做的,它是处于“无为”和“强为”之间的一种存在形式。“有为”的度是我们规划师需要把握的。
想要“有为”,阻力来源于哪?通过刚才的讲座大家首先树立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就是“诗意地栖居”是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每个人都有个体不同的自我追求。而规划师所追求的方向是多方需求的考量。但是在向这个方向推进的过程中阻力到底来源于哪,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眼界、思考,还是来自甲方的压力或资本的力量?在跟权力、资本博弈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界和学识需要作为一种工具,去促使我们实现大多数人“诗意地栖居”。只有在博弈过程中不断地增强本领,才可能为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
徐 刚:
险峰总是从双重视角来理解“诗意地栖居”,一个是作为普通人怎么理解,另外一个是作为专业人士怎么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下面请袁总跟我们谈谈他的观点。
“
袁 牧:
“诗意地栖居”这个讲座的命名十分有意思。“栖居”是一个动词,其实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诗意”是很主观的形容词,这两个词一个是非常理性的状态,一个是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这就跟城市设计一样,“城市”是理性的客观存在,而是“设计”又十分感性。所以说“诗意地栖居”和“城市设计”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概念,就是用一种相对比较感性的手段和做法去对待一个相对比较理性但是又要求做到满足基本条件的事情。并且城市设计不是规划,规划是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则,非常的明确也非常的理性。而城市设计不是去制定一系列的条款,它带有设计的感性色彩,去满足大多数人的栖居。
因为不同的人对诗意有不同的理解,这就跟城市设计一样,规划角度和建筑角度对设计的解读就不同,不同的人对未来不同的期许、对理想不同的认知,决定了我们在做的城市设计时所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院内很多部门都在做城市设计,包括详规中心、总体中心、遗产中心、风景园林中心、建筑分院等等,各个部门对城市的认知以及技术手段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做设计,去塑造这个城市该有的特色。这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需要允许这个过程的发生。
“
徐 刚:
谢谢袁总,又把我们今天的话题拉回到城市设计这个领域里。当然人的需求太多元化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简单共识,而这恰恰是城市设计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我们请袁院长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
袁 昕:
刚才大家说了很多了关于“诗意”的话题,而诗这种东西其实是最没用的,历史上诗人也不是一个职业,街头艺人可以卖画卖字,但是没人靠卖诗谋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经济基础的人有着不同的精神追求。如果总结成人类共性的目标,那可以把诗意理解为幸福。财富只是幸福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基础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先保障自己的生存,然后才能有诗意地的追求。
“诗意”在徐老师的报告里没有停留在高高在上的虚无层面,而是通过“私权利”和“烟火气”转化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其核心就是丰富的多样性。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中的“人”,不应该是一个群体的总和,而是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如同我们做城市更新深入胡同四合院中去调研,推开每一个院落的大门时看到的那样,每一家人都各有各的生活。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人肩上就是一座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是因为无论他们在哪个阶层、是哪个民族,都可以设定一个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当这个目标实现了,或者他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他们就能感受到幸福。有人在宝马车里哭,有人在自行车后笑,有人去邻里中心都很困难,有人为了喂鸽子就飞了一趟巴黎。城市要给所有人选择的权力和机会,要提供多样性的空间去承载他们各自的幸福。
那么我们所追求的诗意是什么?即在规模和集聚下追求多样性,既要保留前人的创造,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又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东西。多样性是城市的灵魂和魅力,在城市中创造更加丰富的多样性是规划师对诗意的追求。这种多样性不是保持现有差异,特别是贫富差距,相反我们应该追求平等和共同富裕。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并没有完全回答新几内亚土著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有那么多货物,而我们只有很少”。他的地理决定论只说明了工业革命前的地理差异,但是工业革命后,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西方殖民而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就是因为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掠夺,而非通过传播先进技术实现平等,这才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城市中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平等和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也是诗意的一种追求。
“
徐 刚:
袁院长从规划师的角度想给大家以勉励,在“诗意地栖居”的创造过程中,大家要做到袁院长刚才说的从人的本质需求出发去理解我们的工作,以此来把我们的工作做的更好。
我简单谈一下今天的感受。“诗意地栖居”某种意义上就像马斯洛需求理论所说的,人的需求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才会有更多的追求。比如说从生存到生活,然后再到诗意地生活,然后再到更多人集体的诗意地生活,这是一个需求不断上升的过程。
第二个感受就是“诗意地栖居”需要从两个视角来看,如果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人的诗意或者是一个家庭的诗意。如果我们从一个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我们追求的是更多的群体的诗意。只有在更多的人在社会中、在城市生活中都实现自己“诗意地栖居”的时候,我们专业价值才会真正得到体现。所以我们在谈“诗意地栖居”的时候,其实讲的是探索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一个过程,诗意是我们想不断接近的一个状态,尽管我们也许永远达不到使城市中每个人都获得“诗意地栖居”,但我们的专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不断地使更多人趋近“诗意地栖居”,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就感。
今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盛宴,借用徐老师报告中的一个词就是“饕餮大餐”,第12期清华同衡大师讲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相关链接
编辑/排版|王淑芸
封面图/图片|供稿部门
供稿|清华同衡 总工办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清华同衡规划播报):大师讲堂|第十二期:对话徐苏宁教授 聚焦“诗意地栖居”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