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一个空间规划制度理论层面的探讨,认为提出一些基本问题比解释现有的做法更有价值。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警惕“用途管制”概念平移的问题,应厘清相似概念的本义区别,考虑概念适用的环境变化,重视空间差异性对管制概念的影响。
第一,用途必然伴随着人使用土地和空间的行为,与城市规划中用地的类型、功能、性质等概念有相似之处,但这些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于用途。例如,居住行为可以发生在住宅,也可以发生在宾馆、公寓、工厂宿舍。反之,居住用地主要做居住之用,但也可以允许居家远程办公、疫情居家隔离或局部商业经营。显然,用地性质管理和土地用途管制在概念上不能替换,在工作中不能混淆。
第二,新时期的用途管制不等于过去的用途管制。我认为,用途管制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层面下的一种特定安排。在城市快速扩张时期,城乡土地价值差距巨大,土地用途管制是控制城市蔓延、保护耕地、保育生态的必要和有效手段,采取大地类的管理方式,规则简洁明确,原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部门依各自权责长期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而今,城市的扩张建设明显放缓,特定时期成了过去式,国土空间“多规合一”,使多部门、大地类的特定层面特征消失,尤其是过去部门博弈中相互之间的纠错纠偏机制已经不再。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结合环境的变化去调整用途管制的机制和方法。
第三,不同活跃度的国土空间需要有不同的管制规则。不同类型的国土空间有不同的活跃度,需要不同的用途管制制度。耕地的国土活跃度最低,要做到最少的变动,适用简明严格的管制规则。城市建设用地的活跃度最高,甚至需要做到动态的适时调整,适用精细有序、刚弹结合的管制规则。其他类型空间则居于中间。过去各大类国土空间各有自己的管制制度,在国土空间“多规合一”的统一管制下,仍应基于国土活跃度来设计用途管制制度的“带宽”和强度。我们应该用大类管理国土活跃度低的地区,比如农用地、未利用地、生态用地等,但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去管理城市内部建设用地,则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2024年第1期 年会学术对话栏目
延展阅读(点击标题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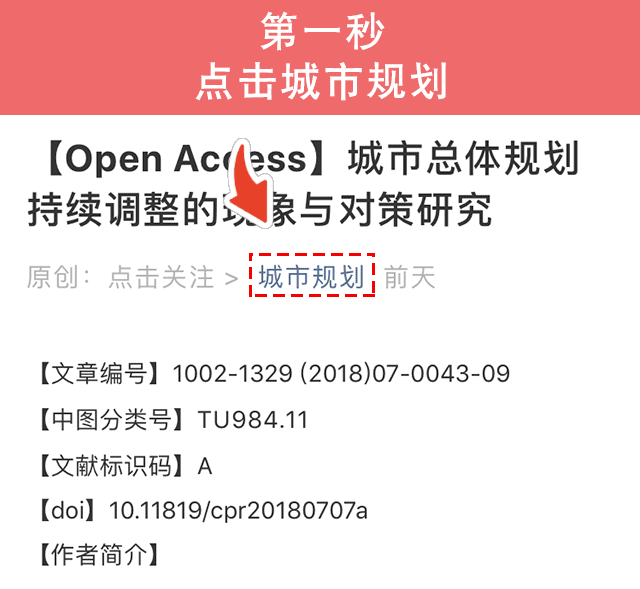
官方投稿网址:http://www.planning.com.cn
微博:http://weibo.com/cityplanningreview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推文目的在于信息交流与共享。若有来源误注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持权属证明与本公众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关注、分享、在看与点赞,让我体验一下吧~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学术分享】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警惕概念平移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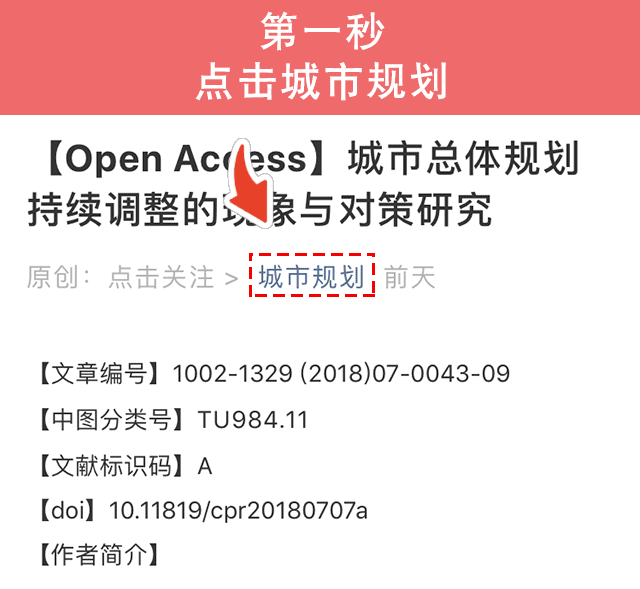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