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后结构主义带来的“关系转向”思想背景,组装思想的起源、译法、主要含义,组装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本专辑的6篇文章。为使读者理解组装思想及其背后的德勒兹—瓜塔里哲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体系,笔者挑选并简要解释了以下概念:多元体,辖域/解域,强度/广延/质,潜在/现实/真实,块茎/树形图式,生成,能动性,物体或对象,行动者/行动素,演成,转译,扁平,对称。
后结构主义与关系思维
兴起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思想和学说组成的松散思想运动。自其诞生以来,后结构主义展现出强大的时代诊断力,对社会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算不上社会研究的主流范式,但后结构主义仍然冲击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顾名思义,所谓“后”结构主义是指结构主义“之后”(after)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确切地说,是对索绪尔—斯特劳斯结构主义(Saussurian and Lévi-Straussian structuralism)传统的背离。结构主义致力于寻找深层结构,认为文化、社会、文本等都是底层结构决定的系统。在底层结构中,元素以不变顺序被锁定在一起,由此形成的隐藏机制成为决定论式现象解释的根据。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所有系统是开放、动态、流动的,意义和行动需要置于广泛关系语境中考量,意义会以矛盾方式扩散。结构主义专注于法则系统(the system of law),并认为法则可以结构和约束个体行动。相比之下,后结构主义关注异质关系,甚至包括跨越人与物质区分的人类与非人类的混合关系[1]3。关系思维是后结构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本质。
值得一提的是,后结构主义自诞生之初就与空间概念紧密关联,例如福柯的“异托邦”、德勒兹—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界域/辖域/解域/再辖域”,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我们可以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为后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组成。不仅因为空间生产学说是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空间生产是关注空间关系联合、变化、生成的学说,而不是针对物质实体空间的学说】等概念。顺理成章,后结构主义思想很快渗透到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不仅影响后者的研究内容,也影响其研究方式。由此,人文地理学领域涌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议题,例如斯里夫特(Nigel Thrift)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2]、马西(Doreen Massey)的“权利几何”[3]、索亚(Edward W. Soja)的“第三空间”[4]、希尔兹(Rob Schields)的“文化拓扑学”[5]等。经由人文地理学,后结构主义也逐渐影响城市研究[6-10]、城市规划[11-21]、城市设计[22-26]等相关领域。
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人文地理学、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研究出现“关系转向”趋势。大部分社会空间理论都承认实体因其在关系格局中的位置而获得形式、效能和意义,但这种“关系转向”很快转变为新的思维定式。例如杰索普等(Jessop et al.)提出了“社会空间关系性”,通过空间关系的四个维度即领土(territory)、场所、尺度、网络认识社会空间关系的多态、多维特征[27]。但正如安德森等(Anderson et al.)所批判的,杰索普等试图将社会关系还原成一套已知、公认、一致同意的模式、原则、形式,只给那些与之不同的事物留下有限余地[28]176。这种机械且先验的关系构造主张实际上重回到结构主义的老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新东西”[28]176。
组装思想的起源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抵制关系思维日益僵化趋势的概念工具,组装(assemblage)思想开始兴起,广泛流行于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等领域。除了坚持任何实体都是有关系的和关系产物的常规论调,组装通过设定关系外部性原则,将社会空间看作人类与非人类等异质要素组成的开放、流动、临时的整体形构,而不是无缝的有机整体。在社会科学领域,组装被广泛用于指称现象的不确定、涌现、生成(becoming)、过程、动态以及社会物质性[10]24。
组装源于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思想,最早出现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下称《千高原》)一书中[29]。书中有多处文字涉及组装的定义,但没有给出组装的完整系统阐述,这与其哲学理念有关。
组装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理论工具首先归功于德兰达(Manuel DeLanda)的贡献。自20 世纪末以来,德兰达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组装概念发展成相对成熟、内涵完整的理论工具[30-32]。在其著作中,德兰达梳理了散落于德勒兹后期著述中的组装思想,将之与德勒兹的早期差异哲学思考关联起来,发展出了“组装理论2.0”[31]4。在使组装概念脱离纯粹哲学思辨成为有力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上,德兰达的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组装思想的发展还得益于科技与社会学派(STS: Science, Techonology and Society)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Actor-Network Theory)的兴起。以拉图尔(Bruno Latour)、卡隆(Michel Callon)、劳(John Law)、摩尔(Annemarie Mol)为代表的ANT理论家,将人类学工作方法引入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在ANT学者看来,社会不是稳定状态,不是特殊范围、具体领域、特定种类的事物,而是非常特定的再联结(re-association)和再组装(reassembling)的运动[33]7。法里亚斯(Ignacio Farias)敏锐地注意到,拉图尔没有使用名词assemblage而是动词assembling 来理解人类与非人类元素的联结【详见本期专辑第2篇主题文章《城市组装——去中心化的城市研究对象》】。
自21世纪初,组装理论逐渐进入城市研究领域。它首先出现在赛博城市主义、城市社会—自然、城市新陈代谢的研究中[34-35]。其中,组装理论被用于描述社会—物质状态的转变过程。组装城市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品是贝内特(Jane Bennett)的《活力物质——事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贝内特以2003年北美大断电事故为例,探讨了物质能动性图景[36-37]。贝内特认为,能动性总是处于人类—非人类共同协作的群组中,不是离散事物的能力,而是聚合异质群组的功能。麦格沃克和道宁(McGuirk & Dowling)用组装概念讨论了悉尼的规划地产开发(MPREs: Master Planned Residential Estates)[7]。他们认为这些住宅开发不是新自由主义扩大私人产权,内嵌市场逻辑和私人管治的工具,而是多元项目、实践、程序起作用的偶然生产[7]174。在城市设计领域,澳大利亚学者多维(Kim Dovey)利用组装理论开拓出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多维将城市视为由不同组成部分相互联结和流动形成的整体,其功能来自部分间的流动、联合、协同,城市有无数个社会空间集群;另一方面,多维试图用组装的概念框架组合不同的城市理论,使之联合、协同、动态变化,促成新的城市设计思维方式生成,他称之为“复杂适应组装”(complex adaptive assemblage)[22-23]。
迄今为止,把相关研究全面“组装”起来的成果,当属2010年法里亚斯和本德(Thomas Bender)编辑的《城市组装——行动者网络理论如何改变城市研究》(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文集[8]。这本书全方位介绍了应用组装理论的城市研究,从扁平的本体论到城市非人实体的积极作用,再到城市集体在公共领域中的分布、流通、构成。书中同时穿插着与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富有开创精神的人文学者如斯里夫特、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希尔兹的对话。此外,2011年《城市》(City)杂志连续4期出版介绍城市组装理论的专刊[9],刊登了组装理论与传统批判都市理论之间的争论。其他人文地理学、城市研究、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期刊也陆续刊登了相关论文。组装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影响由此迅速扩散。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法语原文中,组装是agencement一词。福斯(Paul Foss)和帕顿(Paul Patton)最早使用英文词汇assemblage 翻译agencement,后来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翻译《千高原》一书时沿用了这一译法[38]108,assemblage一词随后在英语世界被广泛接受。但也有许多作者指出,assemblage 并不能准确传达出法文agencement的含义[8]15[32]1[38]108。在法语中,agencement 有“安排”“布置”“配合”“装配”“整理”之意。更重要的是,组装既指将一组部件组合起来的行动,也指这种行动的结果,即组装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而英文的assemblage仅抓住了第二种含义[32]7。
在汉语学界,agencement有“配置”[29]、“装配”[39]、“拼装”[40]等多种译法。日文中,agencement被译为“集合”。所有这些译法都无法完整传递出法语原词即agencement的丰富内涵,即使本专辑所使用的“组装”一词也是如此。这是翻译难以避免的损失,我们希望读者对此有所警惕。
在德勒兹有关组装的说法中,下面一段文字被频繁引用:
“组装是什么?它是一种由很多异质的项构成的多元体,而且这一多元体在项之间建立联系、关系,跨越了年龄、性别、领域——不同的本性。因此,组装的唯一统一性是共同运行:这是一种共生、‘同感’。重要的不是亲属关系、而是联盟与和亲;不是继承、后裔,而是接触传染、流行病、风。”[39]103
这段引用涵盖了组装概念的两个要义:关系的外部性与涌现的整体。
首先,组装是联盟关系而非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也是内部关系,称其为内部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决定了构成关系各部分的身份(identity)。例如父母、子女的身份由血缘关系决定。内部关系不会尊重其组成部分的异质性,而倾向于将不同部分平滑或粗暴地纳入同质整体中[32]2。常见的有机体隐喻内嵌了这种同质整体的想象。与之不同,组装关系并非无缝整体,其部分在参与组装时保持自我独立性,它们可随时从一个组装中退出并参与另一组装。部分被其组成关系调节(conditioned),但并不由其确定(determined)[28]177。
组装的第二个特点是涌现的整体。一方面,组装是不同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德勒兹用“共同运行”“共生”“同感”来表述协同整体。另一方面,即便参与组合,要素仍然具有自主性,这就导致组装出的整体是临时、不稳定、不确定的。组装世界的因果性不是预先既定的某个或某些重要因子,而是部件相互作用的非线性过程。
组装思想属于传统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结构认识论向复杂科学的后结构认识论转向的一部分。经典社会理论大家,如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试图建构根基于稳定性和线性因果论逻辑的社会结构概念,这种宏大结构论早已遭到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评。同样,近年来社会学科对机械中层理论和美式实用主义社会学倾向的反思也层出不穷。不仅如此,当代自然科学也开始出现诸多新兴学科方向,它们强调不确定性、适应性、非线性、多线性的过程和时间,例如生物学理论(自创生、胚胎生成论)、后结构主义数学(混沌、弦)、物理学的耗散结构理论、粒子物理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组装思想是广义科学哲学思想范式转型的一部分。
麦克法兰(Colin McFarlane)总结了组装的三个主要贡献。一是作为经验工具(描述导向),二是作为社会物质概念,三是作为一种想象[9]208。
首先,作为经验抓手,组装有助于描述和理解实存的城市情境如何在历史与潜能中被生产。以组装方式研究,需就对象展开详细的民族志调查。其次,作为社会物质概念,组装颠覆了我们对能动性的理解。从身边平凡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到遥远的基础设施和高科技,组装对物质能动性的关注有助于探究技术和材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随着智能手机、大数据、算法在我们所生活世界中无处不在,我们需要审视物质、技术、材料在形成社会不平等与控制上的能动性。例如基于传统技术观的“智慧城市”会将数字技术视作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工具,并认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和提升生活质量。然而事实是,日常生活越来越依附于数据,这种依附一定程度上是被掌控数据的平台以“智慧”的名义建构、利用和操纵的结果。如果坚持传统的物质被动性观点,我们很难超越传统政治与社会伦理的讨论可能,往往将依附性及其利用与操纵归结为制度、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装视角坚持将材料和技术从被动接受者状态中解放出来,将能动性分配到社会和物质实体中,由此塑造了新的政治实践领域。通过承认非人元素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共同创造不同形式的知识,这种新的政治形式既承认也吸收这些新知识[41]32,因此增加了批判性干预的可能。最后,组装作为一种想象与实验性精神密切相关。通过追踪异质元素,跟随组装共同运行状态,映射(map)元素与外部力量的相遇,可理解秩序的持存性。不限于描述,这种实验性同时是干预(如中断或重铸关系),可以抵制封闭性,保持与世界接触的开放可能[28]176。
组装方法的局限
持结构主义立场的城市理论家对组装城市研究提出了如下批评:在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过程分析上保持沉默;把批判的空间政治经济概念工具与元叙事边缘化;过度重视微观层面的互动甚至将其拜物化(fetishization)【该词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意指对商品关系的崇拜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此处引申为对“微观层面的互动”的崇拜】,从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结构与超地方性(supralocal)的语境;忽视结构化和制度化的权力关系(如私有财产,投资与撤资,生产与再生产,管制、去管制、剥夺等)或对其缺乏理论总结,而这些权力关系是调节日常生活的底层建筑[42]742。
这些指责体现出部分城市理论家对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域和对某些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绝对原则的执着。尽管麦克法兰试图调和这些嫌隙[9],但他的努力并未得到认可。笔者认为,组装研究脱离空间政治经济问题域的做法无可厚非,这正是组装对城市问题的拓展。以旧标准要求新本体论问题域,或许问题没有提到点子上。
更需要重视的是博任纳等对组装方法论的批评。如果说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提出超脱具体现象描述与分类的理论解释,所谓的科学命题不仅能够说明是什么,还能说明为什么[43]1,那么组装理论会因其“幼稚的客观主义”(naïve objectivism)或“自然认识论”倍受攻讦。
“结构—能动性”关系是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命题。基于其本体论,组装分析拒绝结构概念,更确切地说,拒绝结构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有着严苛因果关系的假设。组装反对固定的结构因果性,以涌现的因果性取代之[28]180。为了彻底脱离结构因果性,组装本体论将物体(object)视为关系效应,而非通常意义上与环境清晰分离实质(substance),以此来维系实体的持续形成和变形的可能性。按照这种物质符号学的观念,即使人也只是一个网络,依赖于纸、笔、计算机、身处的建筑物的相互关系。
彻底的关系性要求组装研究采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民族志方法,然而组装的深描接近于无限描述的境地。正如本德所指出的,一些组装的深描“不加区分地将元素吸收进行动者网络中,带有抹平所有行动者重要性的效应”[44]305。吉尔茨等人类学家开创的深描方法是从中发展出对事物意义的反思性诠释。有别于这一点,组装深描的反思性不足,因此博任纳等将组装研究称为“幼稚的客观主义”或“自然认识论”[42,45]。这种分析模式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互联系可以自己说话,而无需中介,或通过理论假设与解释图示激活。事实是不言自明的,只需做出数据收集。
此外,排斥结构和系统的做法使组装的涌现因果解释缺乏学科累积性。因为每次解释都是独一无二的,组装与组装之间不存在共通性和规律性,一旦总结就会落入同一性窠臼。组装理论家试图创造一些概念来解决这一麻烦,例如德勒兹的“层”(strata)和“抽象机器”的概念以及德兰达的“吸引子”(attractor)概念,尝试描述某种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因果关系。然而现实操作中,这些术语往往指向不同的理解和再诠释,带来了学术解释的不可累积性。
(狭义)组装理论与ANT 的区别
尽管德勒兹、德兰达、ANT学者(拉图尔、卡隆、劳)之间的理论倾向、方法体系和术语各不相同,对组装的理解也有分歧,但他们都坚持社会是相互作用的异质元素联合,这种联合不服从于先验的知识和经验的观点。在本体论和更具体的层面,如人类—非人类的分布能动性,关系的生成,从过程性和社会物质性角度思考权力、政治、空间关系等,ANT与组装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ANT是更哲学的组装思想的经验主义“姊妹”[41]30。对于经验研究者,ANT与组装思维的融合可以将两者的优势和敏感性结合起来。
但是德勒兹—瓜塔里—德兰达组装学说与ANT学说仍然有所差别。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即狭义组装学说或理论缺乏能够介入经验现实的解释工具。与之相比,ANT提供了更具体的、可以用于实证工作的工具,如“计算中心”、“独景窥视”(oligopticon)、“不可变移动”、“转译”、“溢出”[41]31,换言之,ANT更易于经验应用。
此外,狭义组装学说或理论与ANT有不同的能动性(agency)认知。ANT认为能动性无法脱离联结(association)而存在,因此能动性是一种转译的成就。如果要行动,物体需聚合并找到联盟者,通过生产行动者网络产生能动性;在联结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41]30。然而组装的关系外部性原则坚持了组装组成部分的独立品质。组装的能动性(或者称能力[capacity])不可预测且保持开放,并超出组成部分的属性。由此,ANT被批评为对联结之外的东西视而不见,然而这些东西会塑造联结[41]31。
专辑的“组装”
通过“组装理论与城市研究”这一专辑的讨论,我们希望向国内城市研究、城市规划和设计学者引介这一社会科学和城市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包括但不限于梳理组装理论背后的哲学社会学脉络与背景,解析其思想内涵,探究其对中国当下城市问题研究的潜能,促成更具有创新城市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形成。
本专辑组织了6篇论文,围绕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侧重于梳理和介绍组装理论的形成背景、哲学立场和理论要点,使读者对其轮廓有清晰的认知。这部分的内容包括3篇论文。第一篇是伊格纳西奥·法里亚斯所著的《城市组装——去中心化的城市研究对象》。这篇文章是法里亚斯与本德2010年共同编辑的《城市组装》一书的前言。文中,作者简要回顾了ANT为城市研究提供的工具箱,描绘了诸多基于ANT的研究如何以不同方式去中心化城市研究。作者指出,这些研究隐含的认知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彻底关系性和对称性角度来理解城市,动摇了将城市视为有界稳定实体的单一假设。作为多元物体,城市来自城市组装的复数涌现。
第二篇是科林·麦克法兰撰写的《作为组装的城市——居住与城市空间》。麦克法兰是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界讨论组装的重要推动者,发表了多篇与组装相关的论文。文中,麦克法兰围绕海德格尔“居住”与组装概念的相互联系展开论述。他认为组装是持续的关系共同生产。其中,居于城市的空间性不可定位且没有边界。组装概念将过程、流动、超地方性的含义注入传统居住概念中,动摇了居住概念所携带的沉重地方主义和根植性内涵,并突破了传统的人本中心论,使人们注意到人类—非人类的分布能动性。从圣保罗和孟买的非正规住宅的持续组装出发,麦克法兰将更广泛的城市过程和形式纳入组装内涵中。
第三篇文章《从砖头到外卖员——论城市组装》从人文学者视角展开讨论。这篇文章体现了本专辑的主旨——引入异质要素,形成共生,刺激差异生成。作者陆兴华在文中论述了20余种城市组装,既有矿物质与凝胶、气溶胶、肌肉、神经的组装,也有市中心对各区的组装、地铁对人流的组装。许多组装与传统规划话语体系格格不入,但如果了解作者近年的工作,或许可了解其用意。作者将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尺度放在人类世文明层面上考量。人类世全球城市化聚合了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的全球化使全球城市集体遭遇气候危机,需要考虑气候和地质两个要素及其所引发的后果;二是数字技术革命所致的城市平台化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的器官界面化后果【请参见该文第7小节】[46]3。这两方面都体现出深刻的组装纠缠。文章的重心落在了城市平台化的论述上。用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概念来解释,城市已成为“集体体外化器官”。由此不难理解厨师与厨具、军队组织与军事技术、快递员与平台和手机的隐含联系。这篇论文不在意局部实际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但作者的思考可以帮助城市规划者拓展思考的边界。然而,作者显得随性的行文方式与庞杂的知识体系对于城市规划及其相关领域的读者提出了挑战,缺乏明显的逻辑主线也加剧了理解困难,文章最后对平台城市的论述匆匆落在云计算失败的城市组装也稍显论证不足。
专辑的第二部分关注组装思想指引下的经验问题研究。这些研究用更丰富的经验材料展现出城市组装理论的多元可能。
《组装视角下文化创意集群差异生成分析——以田子坊和“南京1865”为例》一文针对文化创意集群同质化现象展开批判。无论是文创集群空间生产的同质化,还是其产品和服务的创意不足,或是其研究狭隘性,都折射出其背后同一本体论的局限。文章借用德勒兹—瓜塔里的组装理论来分析这一现象。《千高原》论述了两种组装——树形组装和块茎组装。这两类组装可被视为两种不同但互不排斥的解读世界的方式。文章基于此分析解读了田子坊和“南京1865”两个文化创意集群。前者在1998—2008年形成过“块茎组装”,后者自2006年至今则以“树形组装”模式延续至今。文章追踪了这一时期田子坊的逃逸线与块茎组装的形成,以及受集群理论等超编码抽象机器影响的“南京1865”树形组装的形成。文章指出,类似于热力学的远离平衡的强度场域,由逃逸线组成的块茎组装是逃离捕获装置的社会强度场域。在这种场域中,强度差异没有被均等,可以维持非同一性生产张力。文章借此反思隐蔽在当下文化创意集群规划、管理、研究中根深蒂固的类型学与本质主义观念,并认为它们恰恰是空间生产同质化的观念源头。这篇论文以回溯的方式梳理了两个案例的历史进程,但限于条件,对其历史进程的细节挖掘得不算充分。此外,仅以两个案例证明树形/块茎组装与文创集群的联系,案例的典型性、丰富度有所不足。
与前一篇文章类似,《历史街区的本体论转向——以“日常之物”建构差异性的秩序》一文也将矛头指向了空间生产的同质化,聚焦于历史街区的保护理念与认知方式的不足。在作者薛芃看来,造成这种同质化的关键在于历史街区物质遗存往往被抽象成可辨识的空间结构和文化符号,这样做既冻结了历史街区形成过程中的鲜活社会关系,也忽视了非人元素在此过程中的能动性。借用拉图尔对“物”的双重定义,文章针对清末民初北京大栅栏绸缎庄的“洋式店面”展开细致分析。作者将洋式店面视为持续存在并参与不同日常实践的“日常之物”,并认为这类日常之物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街区自在差异形成的关键。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细腻的笔触揭示出这些洋式店面的空间生产过程,它们如何既作为构建商店内部秩序的“行动素”(actant),即作为不可化约的实体,又作为激发竞争者构建差异秩序的“行动者”(actor),即作为可认知关系的对象,承担着双面性差异秩序生成的作用。作者借此指出,日常之物的双面性是突破基于文化表征的传统保护理论的关键。然而作者阐述的洋式店面和双面性秩序构建发生在清末民初,是当时社会需求、消费模式、文化偏好、商业模式、产销模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如果不考虑背景的时过境迁,泛泛得出双面性的结论似乎问题不大。一旦进入具体的保护语境,由过去历史语境中挖掘出来的双面性在新社会条件会产生什么变化,这是作者交待不足的,而这是反驳旧的历史街区类型学方法论的重要一环。否则,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的双面性或许也会被固化成某种概念和知识类型。
本专辑最后一篇文章《作为潜在—现实联系的边界空间——以北京旧鼓楼住区为例》尝试挖掘组装研究中被讨论较少的“潜在”层面。作者朱天禹和李琪以北京旧鼓楼社区大石桥胡同入口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情景图绘追踪空间中潜在和现实因素的相互纠缠。作者将“边界空间”定义为“潜在和现实相互开放和连接的媒介”,并将之作为有具体指向的解释框架,解读潜在如何影响现实。针对北京旧鼓楼社区在“疏促整”行动前后的变化,作者积累了丰富细腻的田野调查素材。论文拓展了城市研究中潜在本体论的讨论边界,发展出一套阐述复杂性的图绘工具,这是可贵的创新与探索。但其研究也有不足。一是如果仅仅将边界空间定义成为“潜在与现实相互开放和连接的媒介”,可能带来边界空间的泛化。二是作者将过去分解为若干历史事件,称其为潜在行动者,实际上是对潜在整体的简化。更确切地说,如果这些行动者可被清晰表征,它们就不再“潜在”,而是“现实”。同时,不在场行动者更像是行动者的能动性,或者说一种“能力”(capacity)。三是文章的图绘与人文社会学科的深描区别不大,可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图形化。如果图绘不是描摹/追踪(tracing),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创造性实践,那么图绘的能动性不仅应该让设计师和规划者在已有复杂性和矛盾性中看到潜力,而且还可以现实化这种潜力[47]214。关于后一点,这篇论文讨论得稍显不足。
术语解释
许多立足于德勒兹哲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快速有效地穿过“概念丛林”将关键思路传递给读者的问题。无论是德勒兹还是ANT学者,都构造出大量概念和术语以推进其思想实验。如何解读这些术语和概念已颇费周章,更不要说基于这些思想展开经验研究。为此,本文选取专辑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术语,简单解释其含义,以期读者对这些理论有概貌了解,进而更准确地理解文章主旨。这些术语一部分来自德勒兹、瓜塔里、德兰达的理论,一部分来自拉图尔、卡隆、劳、摩尔的ANT。
多元体(multiplicity):本文译为“多元体”,也有译为“繁复体”[48],这一概念是德勒兹哲学的重要基石,它贯穿了德勒兹所有作品,是其他重要概念如“块茎”“组装”的基础。包括ANT在内的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也采纳了这一概念。其定义是高度技术性的,既有来自不同数学分支的影响,如微分几何、群论、动态系统理论,与“流形”(manifold)密切相关[30];也有来自柏格森(Henri Bergson)哲学的影响,如柏格森关于绵延多元体和广延多元体的区分【转引自参考文献[49]82-83,是邦达斯(Boundas)对柏格森提出的绵延多元体和广延多元体的论述】。多元体是一种复杂的、与预先的一致性无关的结构。德兰达认为,在德勒兹哲学中,多元体的作用是取代更古老的哲学概念——本质(essence)[30]。德勒兹用其来避开一与多的抽象对立。多元体应被理解为名词,所有事物都是以其方式存在的多元体。因此,多元体以复数形式出现。
辖域(territorialization)、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德勒兹和瓜塔里从生物学的“领地”或“界域”(territory)的概念出发,延伸出“辖域”“解域”“再辖域”的概念,他们以这些词汇强调事物如何联结,而非“是”(be)什么。在一段时间内使不同元素保持为整体的方式就是辖域,辖域是力(forces)的联系,生产出不同整体,它们使组装稳定[29]120。但每一次辖域都会伴随解域的力(power),“组装具有卷携着它的解域之刃”[29]120。组装处于时刻不停的辖域、解域、再辖域的连续过程,而非静态稳定的状况。德勒兹和瓜塔里将解域的运作方式描述为逃逸线(line of flight),解域意味着释放组装的创造性潜力。需要指出的是,辖域和解域是用来克服二元对立关系的,它们自身没有二元对立。作为转变向量,解域内在于组装,具有解放组装的变化潜能[50]67。
强度(intensity)、广延(extensity)、质(quality):物理学的广延属性一般指长度、面积、体积、能量和熵等可度量属性,它们是可分割属性——如果把某个重量物质分成两半,我们得到两半重量。然而,类似温度、速度、密度、压力之类的强度属性不能如此划分——如果把90℃的水分为两份,我们不可能得到两份45℃的水[30]18。区别于广延,强度属性是内在不可分割的。更确切地说,强度属性是不涉及种类变化的不可分割属性。强度也有别于质。虽然质和强度一样都是内在不可分割的,但强度内的差异可以驱动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如温度、压力,而质的差异无法实现这一点[30]63,如红色、绿色。德勒兹最早意识到强度、广延、质差别的形而上学意义,这些差别构成了他的差异本体论基础。
潜在(the virtual)【the virtual 可译作“潜在”或“虚拟”,本专辑的文章选用“潜在”的译法。“潜在”在人类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人类学中的仪式研究,其“阈限”(liminoid)就是一种潜在。“潜在”也是人类心智的重要组成,例如梦、记忆、过去。德勒兹将此概念扩展至非人类事物。“潜在”这一概念具有可以捕捉虽存在但无形且不具体的活动和对象的性质,例如趋势。毫无疑问,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数字形式的赛博空间也是一种“潜在”。在中文世界,这种潜在被专称为“虚拟”“虚拟现实”。本专辑文章选择“潜在”而非“虚拟”译法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潜在”是目前大陆学界引介德勒兹作品的常用译法;另一方面,希望区别于狭义的计算机化赛博虚拟概念,避免读者陷入先入为主的认知中】、现实(the actual)、真实(the real):在德勒兹的本体论中,潜在与现实是两个相互排斥但共同组成真实的充分条件。德勒兹引用普鲁斯特的语言来说明潜在:“虽是真实的,但并不是现实的;虽是理念的,但并不是抽象的”[48]354。现实或真实是事物的状况、身体、个体;潜在或真实属于纯粹过去,可以是记忆、氛围、趋势,过去永远不能完全呈现;尽管潜在不是现实,但是潜在有能力产生现实[51]296-297。西方思想的问题在于总是通过已经被表达和被构成之物来强调现实,然而被现实化的只是诸多未实现路径和潜能的一种。也只有考虑潜在和未实现潜能,我们才能将当下转变为真正新的未来[52]xxx。
块茎(rhizome)、树形图式(arborescent schema):与解域、辖域一样,块茎同样是从生物学中发展出的哲学隐喻。块茎是地下的块状根系,它们水平延伸并发育出新植物。块茎概念描述了发生在毫不相干的物体、场所、人的联系,可以被用于定位网络的、关系的、横贯的思维的过程。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块茎描述为抽象实体(音乐、政治、经济、生态等)的行动,其本性是移动的基体,由有机和非有机部分组成,按照暂时和非确定的线路形成共生与平行的联系[53]。对比于块茎模式,树形图式非常常见。它是严格等级制的,特定要素和个体的重要性、生产性、创造性与树形图式的先验性相比无足轻重。在树形图式中,事物和人被置于监管秩序中,创造力被限制[54]。
生成(becoming):“生成”和“差异”是德勒兹作品的核心概念,是德勒兹本体论的基石。德勒兹用生成反对存在(being)和同一(identity)不合理的主导关系[55]。生成可以描述事件构成中内在差异的持续生产。生成既不是最终产物,也不是过渡阶段,而是变化的动态(the very dynamism of change),处于异质项中,并不朝向特定的目标或终止状态[55]。所有可感知的事物和状态都是生成的产物。
能动性(agency):在ANT中,能动性与人的主观意向性无关,而是可以引发影响(affect)的能力(capacity),这种能力导致事物状况发生变化。正如拉图尔所说,如果没有可见的影响,那么能动性就不存在[33]52-53。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非人行动者或物体拥有激发影响的能动性。
物体或对象(object):Object有多层含义。拉图尔认为海德格尔关于“物”(Ding/thing)的词源分析揭示了“物”同时作为“对象”(可认知关系)和“事实”(不可化约的实体)两层含义[56]233。ANT中的实体既是对象也是实体。
行动者(actor)、行动素(actant):在ANT中,行动者做了什么是定义行动者的关键。一般理解中,行动者往往与人类行动者相关。因此,拉图尔借助文学理论中的“行动素”一词来区别行动者,将非人类包含在内。在这里,能动性成为区别行动者和行动素的关键。行动者往往侧重于是什么赋予行动素行动的主观性、意向性、道德性[57]18,303。
演成(enact):Enact 是ANT的关键术语。在关节硬化医学民族志的研究中,ANT 学者摩尔发现医学中关节硬化没有固定的同一定义,而是病人、外科医生、医院、显微镜相互作用的结果。摩尔将这种“医学及其对象在各式各样业务中协调、相互作用、塑造的方式”称为“演成”[58]vii。演成被用于指称对象/物体是关系生成的结果。
转译(translation):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关系原则。转译不是语言翻译,而是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在此过程中,核心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转译涉及四个阶段: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利益集结(interessement)、承诺(enrolment)和代言(spokesmanship)[59]。
扁平的(flat):扁平意指现代哲学的一种新型本体论,即扁平的本体论(flat ontology)。德兰达在《强度科学与潜在哲学》(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中率先提出这种本体论,它由独特、单一个体组成,这些个体虽然在时空尺度上不同,但在本体论地位上没有区别[48]51。扁平与等级、垂直等意义相对。传统的本体论由有机体、种、属等层级化的本体论类别构成。哲学家哈曼认为拉图尔是扁平本体论的先驱,而不是德兰达及其思想启蒙者德勒兹。扁平的本体论在劳、摩尔以及德兰达、拉图尔、哈曼等众多当代思想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很清晰。和前述“对称”原则一样,扁平视角消除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工之间的二元对立。
对称的(symmetrical):对称意指“(广义)对称性”原则。针对科学哲学家无法解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真实存在的差异这一问题,卡隆、拉图尔等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一般认为,这一原则在本体论上抹杀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差别,但实质内涵是要求“人类学家必须将自己摆在中点的位置上,从而可以同时追踪非人类和人类属性的归属”。所谓中点指拟客体,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杂合体,处于自然与社会两极的中间,自然和社会仅仅是人类赋予拟客体以秩序之后的结果[60]liv。UPI
参考文献
[1] MURDOCH J.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y: a guide to relational spac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2] THRIFT 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politics/affect[M]. London: Routledge, 2008.
[3] 马西. 空间、地方与性别[M]. 毛彩凤, 袁久红, 丁乙, 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4] 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5] 希尔兹. 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M]. 谢文娟, 张顺生,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
[6] AMIN A, THRIFT N. Cities: reimaging the urba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7] McGUIRK P, DOWLING R. Neoliberal privatization? remapping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 Sydney’s masterplanned residential estat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9, 28(3): 174-185.
[8] FARÍAS I, BENDER T.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9] McFARLANE C.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ism[J]. City, 2011, 15(2): 204-224.
[10] McFARLANE C. Learning the city: knowledge and translocal assemblage[M].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1.
[11] HILLIER J. Straddling the post-structuralist abyss: between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J]. Planning theory, 2005, 4(3): 271-299.
[12] HILLIER J. Stretching beyond the horizon: a multiplanar theory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M]. Aldershot: Ashgate, 2007.
[13] HILLIER J. Plan(e) speaking: a multiplanar theory of spatial planning[J]. Planning theory, 2008, 7(1): 24-50.
[14] HILLIER J. Strategic navigation across multiple planes: towards a Deleuzeaninspired methodology for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11, 82(5): 503-527.
[15] WEZEMAEL J V. The contribution of assemblage theory and minor politics for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J]. Planning theory, 2008, 7(2): 165-185.
[16] 斯蒂芬·伍德. 欲望的港区:德勒兹与城市规划话语[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5): 60-72, 95.
[17] RYDIN Y. Using actor-network theory to understand planning practice: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tants in regulating low-carbon commercial development[J]. Planning theory, 2012, 12(1): 23-45.
[18] PURCELL M. A new 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 and planning[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3, 14(1): 20-38.
[19] ARAABI H F. Deleuz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e impact on planning[J]. City, 2014, 18(4/5): 589-593.
[20] RYDIN Y. The challenges of the “material turn” for planning studies[J].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s, 2014, 15(4): 590-595.
[21] BEAUREGARD R A. Planning matter: acting with thing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22] DOVEY K. Becoming places: urbanism/architecture/identity/power[M]. London: Rutledge, 2010.
[23] DOVEY K. Urban design thinking: a conceptual tookit[M]. London: Bloomsbury, 2016.
[24] TORNAGHI C, KNIERBEIN S. Public space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new challenges for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M]. London: Routledge, 2012.
[25] ARAABI H F, McDONALD A. Towards a Deleuzoguattarian methodology for urban design[J]. Journal of urbanism, 2019, 12(2):172-187.
[26] SENDRA P, SENNETT R. Experiments and disruptions in the city[M]. London: Verso, 2022.
[27] JESSOP B, BRENNER N, JONES M. Theorizing sociospatial relation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8, 26(3): 389-401.
[28] ANDERSON B, KEARNES M, McFARLANE C, et al. On assemblages and geography[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171(2): 171-189.
[29]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析(卷2):千高原[M].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30] DELANDA M. 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02.
[31] DELANDA M.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M]. London: Continuum, 2006.
[32] DELANDA M. Assemblage theor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2016.
[33]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4] GANDY M. Cyborg urbanization: complexity and monstro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5, 29(1): 26-49.
[35] SWYNGEDOUW E.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hybrid) natures and(cyborg) cities[J]. Science as culture, 2006, 15(2): 105-121.
[36] BENNETT J. The agency of assemblages and the North American blackout[J]. Public culture, 2005, 17(3): 445-466.
[37] BENNETT J.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8] PHILLIPS J. Agencement/assemblage[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 23(2/3): 108-109.
[39] 德勒兹, 帕尔奈. 对话[M]. 董树宝, 译.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8.
[40] 王瑶. 乡村的社会——物质拼装:开启乡村研究的新视角[J]. 人文地理, 2023, 38(2): 145-154.
[41] MÜLLER M. 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 rethinking socio-material power, politics and space[J]. Geography compass, 2015, 9(1): 24-41.
[42] WACHSMUTH D, MADDEN D J, BRENNER N. Between abstraction and complexity: meta-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assemblage debate[J]. City, 2011, 15(6): 740-750.
[43] 彭玉生. 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1, 26(3): 1-32, 243.
[44] BENDER T. Reassembling the city: networks and urban imaginaries[M] //FARÍAS I, BENDER T, eds.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303-323.
[45] BRENNER N, MADDEN D, WACHSMUTH D. Assemblage urbanism and the challenges of critical urban theory[J]. City, 2011, 15(2): 225-240.
[46] 陆兴华. 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 1[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47] CORNER J. The agency of mapping: speculation, critique and invention[M] // COSGROVE D, ed. Mappings.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 213-252.
[48] 德勒兹. 差异与重复[M]. 安靖, 张子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49] BOUNDAS C V. Deleuze-Bergson: an ontology of the virtual[M] // PATTON P, ed. Deleuze: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6: 81-106.
[50] PARR A. Deterritorialisation / reterritorialisation[M] //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66-69.
[51] BOUNDAS C V. Virtual/virtuality[M] // PARR A,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6-298.
[52] COLEBROOK C. Understanding Deleuze[M]. Crows Nest NSW: Allen & Unwin,2002.
[53] COLMAN F. Rhizome[M] // PARR A,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1-233.
[54] STAGOLL C. Arborescent schema[M] // PARR A,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14.
[55] STAGOLL C. Becoming[M] // PARR A,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24, 28.
[56] LATOUR B.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J]. Critical inquiry, 2004, 30(2): 225-248.
[57] LATOUR B.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8] MOL A. The body multiple: ontology in medical practice[M]. Duk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9]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M] // LAW J, ed. Power,action,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6: 196-233.
[60] 刘鹏. 译者前言:拉图尔哲学的人类学特质[M] //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刘鹏, 安涅思,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xi-lxxiv.
作者:杨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y_sampan@sina.cn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组装理论与城市研究【2025.1期主题·优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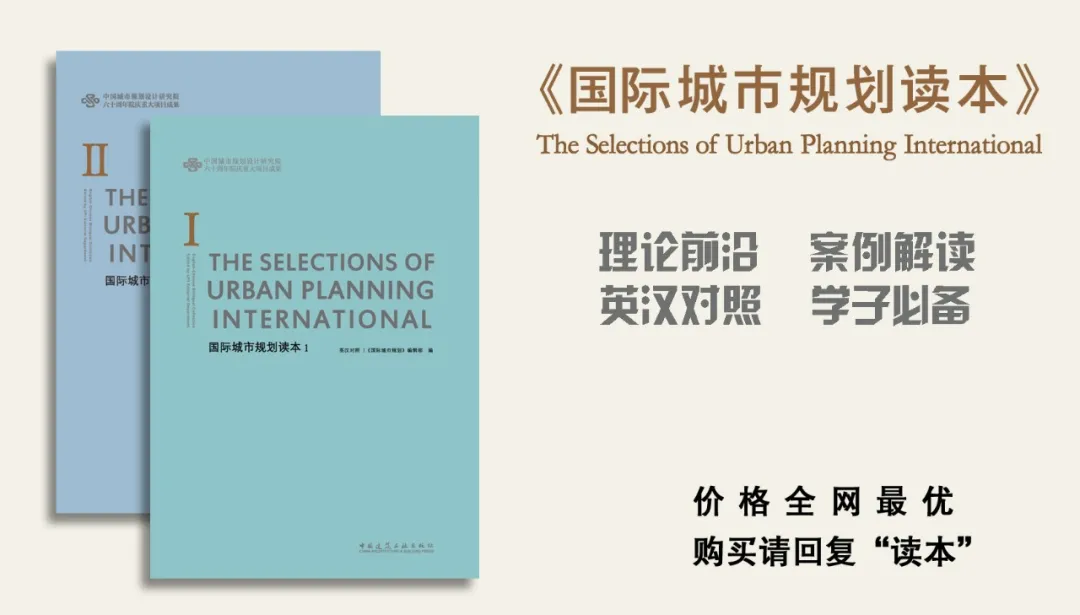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