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手机组装是城市组装的最新格式。从1.24万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兴起以来,这种叫作“城市”的组装从未停滞,在今天则是陷于云计算平台和气候变化的交互或思辨之中了。从德勒兹到德兰达的组装理论为我们描述城市组装过程提供了一系列哲学预制件,能协助我们从城市哲学、建筑学和城市平台设计的视角,探索今天人类世界的城市组装的新语法。城市是组装的开端,而不是结果。
0
关于组装的理论也是可被组装的。
1
这一加入的矿物质是动物多样性和文化设计多样性的来源。实际上,城市塑源是比内骨骼塑源更根本性的。世界城市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新月沃地(The Fertile Crescent)。自那之后,人类外骨骼的进化便大大超过了内骨骼的进化。城市化不可遏止地到来,像被安装上了一根发条,在工业革命之后,更像组合家具那样不停地组装开来,直到我们正在面对的史无前例的、掘地三尺的全球城市化中的中国城市化或中国城市的被全球化。这就是6000多年来的城市组装在今天的我们眼里的样子。
2
德勒兹对“组装”的定义是:“组装是什么?它是一种由很多异质的项构成的多元体,而且这一多元体在项之间建立联系、关系,跨越了年龄、性别、领域——不同的本性。因此,组装的唯一统一性是共同运行:这是一种共生、‘同感’。重要的不是亲属关系,而是联盟与和亲;不是继承、后裔,而是接触传染、流行病、风。”[4]69
3
德兰达的组装理论最终走向了这样一个结论:生命是一架计算机,并且自己会建模。生命现象是建模后产生的一次次涌现的叠加。由此也可以建立关于我们社会的一种组装理论:没有一种组装是能够主导一切的。话语式组装并不优先。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这方面都犯了错。
4
根据哈曼(Graham Harman)的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或人类世新形而上学,所有时代的开罗都存在于它的街上的涂鸦之中,都争相要在当代青少年的涂鸦中出场。当代北京或当代上海或哪哪,都并不是格外存在的。一个城市的所有时代的版本,都是扁平地共存着的。民国时代的上海是与“文革”时的上海、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并存在我们面前的。在城市里,买不起的东西也扁平地在那里陈列着,我们可以替代性地占有它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具有一种自己的城市风格或时尚,如果不能在文化时尚和艺术的某一方向上领导潮流,至少能在穿着、装饰、家用物品、美食和发型上,在某个时刻独树一帜,去代表这座城市[8]15。什么是城市?没有定义。福克斯说,城市是人口集中的中心[8]23。蔡尔德说,城市是有真正的纪念碑式建筑的地方,是10倍于村庄的地方[8]23。在古巴,2000人以上的地方就能算城市了。在当代中国,只有(同时)有苹果手机店和奔驰4S店的地方,才能被称为二线城市。中国的五线城市又是以哪些元素为标志的呢?
5
14世纪后的阿姆斯特丹对世界市场作出了组装[5]109。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千高原》开头是这样写的:阿姆斯特丹是块茎。它的运河网是世界市场的深层语法。其实,威尼斯也是。国家是后来的和表面的。它是有了火炮后才值得被保卫的。城市是块茎式组装,民族国家则是树形的。
6
在关于城市的组装理论看来,城市语境(context)的说法是不对的。语境式保护,如苏州、绍兴的老城保护,是在给“尸体上涂油”,阻断了城市的活力,使原有的纪念碑式的城市人工物断了气,这会使它们死得更快。这种保护所隐含的城市自然主义必然导向“死城”。
7
视网膜一开始是从一条光线里获得了一个光学数列的切面的,像照相机将一缕光投到它的背部平面那样,但它与照相机的相似也仅止于此[10]79-286。视网膜不是拍下了与对象相似的图片,而是只摄取了与切面中的光学现象同形(isomorph)的张度(intensity)的数列。视网膜向原视觉皮层送去张度的裸数列。第三种情况是视网膜直接连上皮层。所以我们必须说,城市是视网膜与脑之间的组装,计算机视觉是被挡在这一组装之外的。云计算平台对城市的组装,只是数学式意淫。UPI
参考文献
[1] DELANDA M. 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M]. New York: Swerve, 2000.
[2] 陆兴华. 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 1[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3] 陆兴华. 中国城市化前传:城市哲学 2[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4] DELEUZE G, PARNET C. Dialogues I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DELA NDA M. Assemblage theor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6] DELANDA M. Deleuze: history and science[M]. New York: Atropos Press, 2010.
[7] DELANDA M. Philosophy and simulation: the emergence of synthetic reason[M]. London: Continuum, 2011.
[8] SMITH M L. Cities: the first 6000 year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20: 9.
[9] TILLY C.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 DELANDA M.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11] ROSSI A.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14.
作者:陆兴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luxinghua@tongji.edu.cn
排版 | 徐嘟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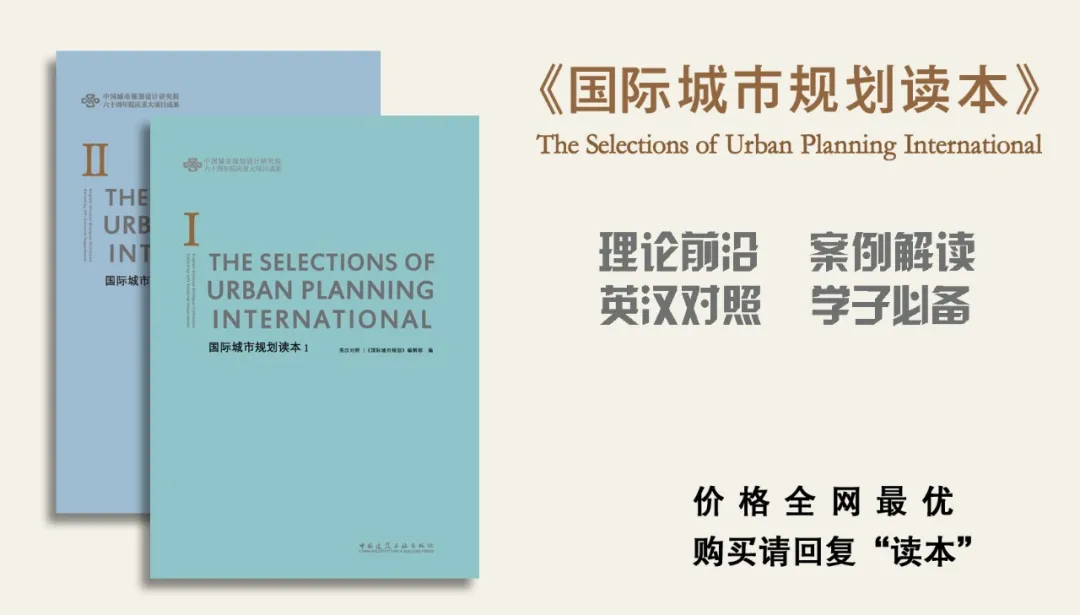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从砖头到外卖员——论城市组装【2025.1期主题 · 优先看】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