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教授级高工,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2016到2017年,我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县(市)域城镇化研究。结合近年来的观察,当时的几个研究观察与结论依旧有效,在县域城镇化研究中有三点差异值得注意。
首先,要关注县域中人的差异,需要将笼统的“人民”进一步细分为“人群”,才能考虑到县域青年需求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选择偏好的县域青年拥有不同的生存能力,需求上也存在异同;另一方面,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青年也有不同的主导诉求。县域城镇化不能只关注到少数几类群体。
其次,要关注到县本身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政策。县的分类方式非常多样。我们的研究采用了长期稳定因素和慢变量因素(区位、地理特征、人口密度等)作为分类依据,将中国近2 000个县域分为六类:大城市周边县、人口高密度平原县、人口低密度平原县、人口高密度山区县、人口低密度山区县和生态严苛地区县。其中,大城市周边县本身能够获得大城市的发展资源外溢,其县域内的农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是典型的城市化方式,因此其面临的是城乡一体化问题,而非县域发展问题。其他五类县域则面临各不相同的县域发展问题,必须要差异化对待。
最后,要关注到对中国县域研究在不同时间维度下的视角差异。短期内要看政策。县域的各类新政策可以对青年人产生巨大的吸引,但要避免“运动式”政策造成的不可持续以及资源浪费。中期要看制度。当下的所有基础性制度都是在快速增长阶段形成的,这些政策都具有二元化趋向,都是以鼓励城市、鼓励基建、鼓励房地产发展为导向。如果没有制度性改革,城乡二元关系就不会改变。县域具有三产融合最好的空间,如果把青年的成长和三农紧密结合起来,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结合起来,能吸引更多的青年回流到县域,回流到乡村,并参与到乡村振兴。但这些空间的成长期待行政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方方面面的根本性的转变。如果没有这些根本性的转变,创造一两个发展典型不难,但大多数青年回到县域就只能“艰苦奋斗”,乡村振兴就容易变成一种新的“寡头经济”。长期则需要看文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总体来说,凡是有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都有繁荣的乡村,从文化的角度我对中国的乡村发展绝对有信心;第二,要注意到地域文化是青年地方感、地域认同感的来源,要充分利用好地域文化对青年的吸引力;第三,文化发展会产生大量新的需求,这些需求日益增长,给乡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些需求难以解决县域内所有的三农问题。
如今县城、乡村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青年都很开明。只有制度的变革带来县域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破解掉“只有官场没有职场”等现象,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近年来县域制度变革整体趋势向好,我们再继续差异化地看待县、看待人,我觉得可以为年轻人找到成长空间。我坚信从长远看,中国的乡村一定是美好的、富裕的,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
相关阅读
-
-
特大城市总体规划中区域协同的探索——来自武汉大都市区的思考
-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
-
中外城市增长边界研究进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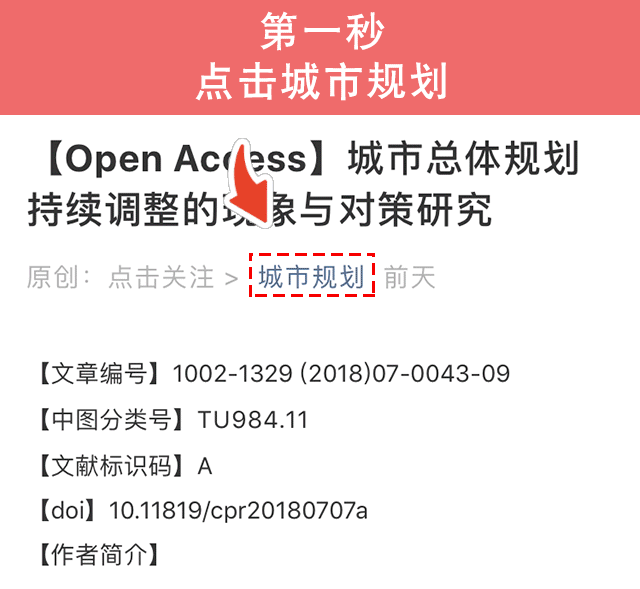
官方投稿网址:http://www.planning.com.cn
微博:http://weibo.com/cityplanningreview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推文目的在于信息交流与共享。若有来源误注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持权属证明与本公众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希望您为喜欢的内容点个赞~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学术分享】县域城镇化研究中应关注的三点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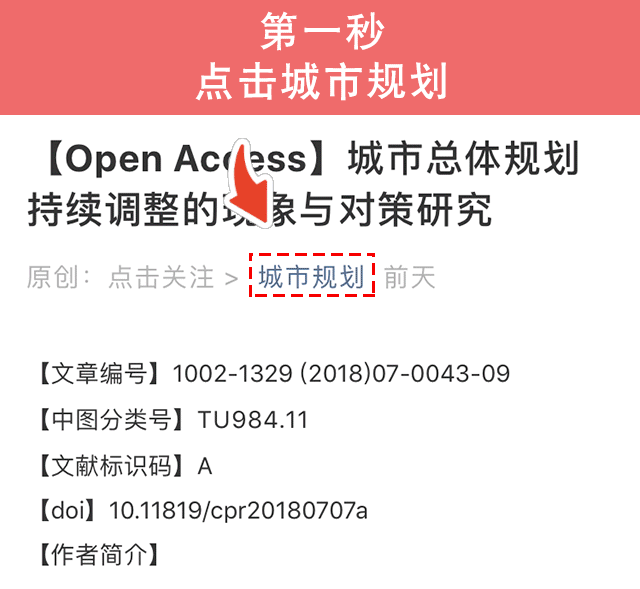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