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振 (1973-),男,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精彩导读
城市是信息技术密集应用的领地,城市规划、城市运行和城市治理越来越依赖信息网络。作为空间实践知识和工具的城市规划,需要从之前的模式转向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城市规划”,这意味着学科面临转型的挑战。从20世纪末到当下的一段时间里,大量研究文献将信息技术作为“实用技术”,探讨城市交通和管理等的信息化应用,利用各类信息平台或软件应用,收集人群的行动信息和轨迹,建设城市的“数字大脑”、智慧或智能城市——“数字驱动”越来越成为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
列斐伏尔谈到三个维度的规划。一种是物资规划,是量化的、可计算的规划(如每年产出多少吨钢铁、小麦、水泥等);一种是财政方面的规划,同样是可计量的(如每年为完成相关项目的计划财政支出);第三种是空间-时间的规划,包括事物的定位、交换网络、交通和流通等,是对时空关系的研究和安排[3]。他指出,前两种的综合是一种普遍社会控制性规划,在法国通过财政收支和银行来完成,在苏联则通过强制执行计划性的安排。但空间-时间的规划,没有能够和物资规划与财政规划整合在一起,它是单独进行的规划。进而,列斐伏尔问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存在一个同时包含有这三个维度的总体性规划。他说,“只有技术官僚想要完善这个规划。它让整个社会落入控制论的枷锁中。它赋予了当前的权力一种可怕的效力”[3]48。他接着说,似乎在1970年代,这种全面控制性的、总体性的规划“还不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因为空间-时间的规划与其他两个规划分离和错位了。然而这一状况到了1980年代伴随着信息技术兴起和整合性力量的强化发生变化,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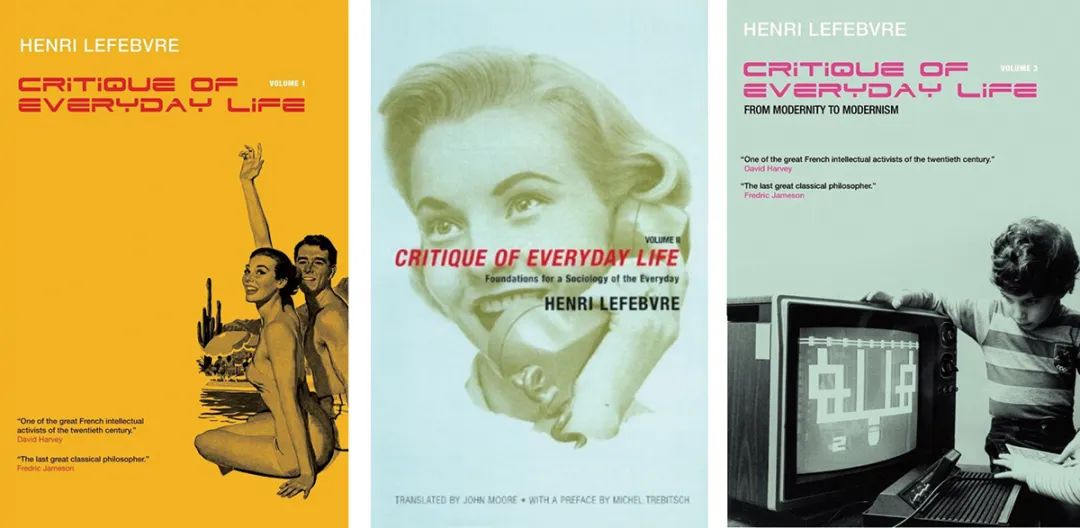
注:英文版的三卷本封面比中文版封面要有趣和命中主题。第一卷封面是战后“休闲式的旅游观光”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第二卷封面是普及化的家用设备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第三卷封面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相关。
2.1 生产方式、符号效应与全球尺度
2.2 信息社会模型:三个层次
列斐伏尔将信息社会模型划分为三个层级:国家的-社会的-个体的。最高权力控制着信息(这个层级是处在全球化与社会层级之间的信息收集、管控和生产);中间层级是社会层面的信息,“在生产物质商品经济的长期支配下,这个部分曾经被抹杀和压制”[5]655,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作用;第三个层级是个人层次,无数个体在该层次结构中博弈和争取他们的位置。这个分析模型很难不让人与《都市革命》中对于都市社会层次的G-M-P(也就是“整体的-混合的-个体的”)分析联系在一起[4],但它们在结构相似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不同。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层次分析是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信息社会模型是信息在不同层次上的生产、监察、管控和消费的问题。“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次有助于认识信息社会的构造,和之前分析不同的是,三个层次的信息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作用下日渐一体化,逐渐生产和构造出一种受严格控制的社会。
2.3 信息理论不是一体化理论(unitary theory)
列斐伏尔明确提出信息理论不是“一体化理论”②,不能抓住整体的社会现实与问题。什么是“一体化理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解释到:“目的是在孤立地理解的各个‘领域’之间……发现或建构一种理论上的统一性。”[6]17-18空间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提出完整认识空间的一种理论和方法。某种程度上,列斐伏尔也是用三元辩证法来谈论信息技术,认为它由科学理论(表征——在抽象端)、技术应用(实践)和社会日常使用(在具体端)构成。他提出信息技术进入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其间存在着各种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构不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或者说,缺少三者间辩证关系的讨论,而忽视这些问题的理论,都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有着目的性的主张)。列斐伏尔首先分析了信息理论中“冗余”(redundancy)的价值。恰恰是冗余的存在,差异的存在,使得正确理解事物成为可能,“冗余包括了惊讶,还包括了无序”[5]656。他也谈到,作为事情发展的另外一面,过多的冗余和差异阻碍了理解而失去意义。信息技术“是在关于无序的理论中构造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模式,在此技术上建立社会秩序”[5]656——与此同时,如果没有无序存在,信息技术就无法运行。
2.4 作为超级商品的信息:发展与增长
信息的特殊属性带来新问题。它没有物质形态的存在,在使用过程中被消费,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什么关系?过程中信息的生产和创造有什么区别?这是关键问题,关系到信息的增长与发展。列斐伏尔谈到,早期的探险家等通过对差异地方的联系,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创造力。列斐伏尔问,从航海、铁路、航空到现代传媒,“通信和信息的创造能力增加了吗?”他说,信息的生产能力无疑在增长,但创造力却萎缩了。“生产和创造之间的关系是逆反的……增长与发展并非对应”,“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通信和信息的创造能力正在慢慢枯竭”[5]658。这一观点映射了列斐伏尔之前谈及的差异与重复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差异愈来愈少的情况下,创造的能力就越来越低,更多是重复性的生产、量的增加。他认为现代通信只是反映现实状况(一种事无巨细的镜像),不能创造出新内容,因此,不能带来日常生活的重大变化和改进,同时产生的一个现象是,公共事物侵入了个体生活,私人生活公开化了。这是一个同时发生的两向进程,进而“通信强度的增加为日常生活的巩固、整合和限制提供了基础。通信强度的增加也包括了发生灾难的危险日趋上升”[5]659。
2.5 伪装的信息意识形态
信息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不宣称自己是形态,而是经验或实证知识,它通过消灭意识形态来生产意识形态。列斐伏尔认为信息意识形态把现实绝对化,不是把现实放到实际情况中来考察,也就是把现实中的某些方面(一种强目的性的局部选取)“提升到颠扑不破的高度”。列斐伏尔谈到,人们给了信息一种“浪漫的光环”(描绘了一种未来的美丽图景,作为一种有目的性的意识形态——例如,对于智能城市的“浪漫”想象),却对于它的另外一面(走向深渊的风险)缺乏认识。
信息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功能转化为信息装置(看似客观中立),转化为实证知识的生产和扩散,进而导致批判性和理论思维的消失。列斐伏尔预见性地谈到,民族国家和跨国势力在管理和制度上控制了信息设施,来巩固他们的操纵和统治,“实证知识不仅被还原为记录下来的和回忆中的事实,而且,每一件涉及政治的事情都会进入官方信息渠道。这种状态给独立于现存权力的任何行动都将造成最大困难,有可能导致所有反对力量的消失”[5]662。他谈到,技术权威和技术官僚用能力、效能取代了政治学的讨论(只谈“创新”能力、不遗余力追求创新却避而不谈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而扩大了全面的危机。在信息意识形态构架下,它的危险是“国家及其放大了的能力被不经检验地强化,尤其是,国家……抓住日常生活的能力的强化”[5]662。
列斐伏尔回顾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及其基础,认为前工业社会按照区域和领地构造起来,而工业社会按照开采的能源形式展开,不受地域限制,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信息建设起来,信息技术权威和官僚藐视老的矛盾(就如互联网企业家藐视房地产企业主)。同时信息理论家乐观认为质的飞跃很快要发生,信息技术将结束社会的不透明,最终社会和日常生活将被事无巨细地展陈出来,就如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瓦尔德拉达孪生双城,“在这个崭新的现实里,没有阴影,没有黑暗的犄角旮旯”[7]。于是列斐伏尔谈到一个美丽新世界诞生了:
“信息以及信息的延伸会通过最短的路径进入完全计划好的社会……我们不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是在谈论一个技术官僚的乌托邦或者意识形态,而且在谈论一个科学神话,一个电子广场的神话和令人不安的计划,该计划把用于工作场所内部控制的‘检查’延伸到了比企业大得多的空间里,对那里实施政治和警察控制”[5]663。
卡尔维诺是这样讲瓦尔德拉达孪生双城的(比照着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座实在的城,和一座电子网络构建的虚拟的城):“无论湖畔的瓦尔德拉达出现或发生什么,都会在湖中的瓦尔德拉达里再现出来,因为这座城市的结构特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反映在它的镜子里……这面镜子有时提高事物的价值,有时又给予贬低……两个瓦尔德拉达相互依存,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7]53-54。
2.6 丧失社会行动与政治实践能力
计算机化的日常生活产生一种状况,即处在虚拟空间中的个人不断地接受和发送信息,成为一种存在的方式。列斐伏尔谈到它造成虚拟空间中的个体失去“公民的尊贵”,只剩下信息的消费者和服务的接受方,使得个体“丧失社会本身和社交能力”,进而“这种孤独不是旧的个人主义的那种存在性的孤独,而是一种被消息淹没至深的孤独”[5]665。这是作为社会个体被切割、隔离、孤立化的状态,集体行动和团结的可能被消解的状态。
列斐伏尔指出,有人指望国家来制止这种危险的发生,这是天真幼稚的黄粱美梦。在新时期,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治理社会和巩固自身政权,它不可能挖掉基础使自己坍塌。国家只会坚定地进一步推进这种状况,使得个人的社会性萎缩,后退到原子化的个体和自己的小空间中——而信息技术的理论家认为其中塞满各种信息(娱乐信息、政治信息、财经信息、游戏……),个人就会觉得处于“自在的舒适区”。列斐伏尔问,“这种小天地真的不会让个人陷入焦虑、陷入喧嚣引起的痛苦之中吗?”[5]665列斐伏尔讨论的一种状况是,当个体丧失外部的社会能力,只在自身的小空间中存活时,外部力量为了本身的续存将持续侵入个体空间,将个体信息转化为商品或生产信息商品的要素。列斐伏尔描述信息技术时代的国家状态,它的基础是政治性地利用信息,控制在其中的盲目乐观的人群(他们或者完全无意识,或者妄想自身的信息活动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
列斐伏尔最后强调,信息技术只是手段,存在的问题是,在新时期所有的事情都要经由、依赖这一手段来处理。它本身不解决问题,问题“现在是政治的,将来也还会是政治的”[5]666。他认为,信息技术不具有把意义赋予不具有那种意义的事物的品质和能力,相反,它摧毁意义。因此,信息本身面临着危机,它摧毁无序、摧毁意义,摧毁生产它自身的来源。为了抵抗这种快速的“衰老”,它要主动制造出各种“差异”、各类“惊奇”“魔幻”来续命,但这一手段犹如饮鸠止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列斐伏尔没有直接提出可能的策略,但他谈到日常生活的具体性阻止走向完全的抽象,日常生活的丰富内容会改变信息的状态。列斐伏尔的办法是辩证性的,在信息走向完全抽象化、符号化的进程中,作为信息来源的日常生活鲜活的具体性有其需要重新审视的价值。只是这个阶段的日常生活状态,不再是上个阶段的状况,信息技术日常生活化了,国家与社会信息技术化了,个体日渐原子化,陷入“至深的孤独”、无助和焦虑,公与私的内涵与边界模糊化,权力通过信息技术带来的透明性对社会的监察和控制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强化。在1980年代,列斐伏尔预见了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危机,预见到一个被全面性控制的社会的来临。
3.1 空间符号化与日常生活的变化
“至深孤独”的进程不始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它深植于城市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然与人文、理性与经验和生活的分离;一个是远距离贸易。前者导致社会的整体性分裂,理性计算逐渐控制和支配城市,城市日渐有序、光明、高大、美景化,同时也日渐僵硬化和空虚化。它加强了文明对人的管控、约束和规训,它将个体人转化为固定在越来越复杂生产链上的劳动力(从无产者到资产者概莫能免,不唯基层工人),人的属性被分割、定位、隔离,个人被局限在越来越狭隘的小空间中,成为机械性的工具人进而掉入至深孤独。在信息技术时代,工业社会时期劳动分工的结构虽有变化但仍然存在,而个人的社会原子化加强了,产生困在“信息茧房”(看似无边、无限却是僵硬边界的信息场域)中另外的一种“被消息淹没的至深孤独”。劳动分工带来的隔离性孤独叠加上喧嚣信息中的孤独,相互作用、共同构造了当代人的普遍状况和精神困顿。远距离贸易是去地方化的开始,是吉登斯提出的“脱域”的开始[8]。地方的稳定性、地方化的生活和经验日渐解体和消散。它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使得地方摆脱狭隘和保守意识,另一方面加大了不确定性,导致个体陷入越来越快的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漩涡,其中的一种普遍结果是回退到家庭和个体领地,以求得某种稳定性。或者说,加强的远距离贸易形成加速变化的社会,导致个体的社会性焦虑和孤独,进而寻求和渴望一种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谈到的为求得终极安全感的“蜷缩”[9]。
信息技术同时增强了日常经验和生活的分离以及远距离贸易。它不再是哈维谈到的工业社会时期的时空压缩[10],它是一种超级时空压缩,生产了前所未有的时空观和时空感觉。空间本经由时间呈现,空间信息本经由时间和人的主体感知和认知获取,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改变了这一状况。工业社会时期的时间和空间仍然联系在一起,而在信息技术时代,空间和时间分裂了,空间的存在不再经由身体的感知和经验,符号化是它主要的存在方式。它存在于影像、图像、文字、声音等的表征符号中,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空间符号”。或者说,在信息技术时代,空间的支配性存在是符号化的存在、表征性的存在。因此这种“空间”可以瞬时传送,时间消失了,时间也就和空间的表征性存在无关。信息技术建构出越来越复杂和快速流动的贸易网,在这个网络中,没有空间距离,只有等级、节点、阀门等,进而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个体人——有着时空感知限度和生物属性的个体人,陷入以超级速度运转的信息网络之中,他/她同时也要被迫成为符号化、标签化和数量化存在,从一个立体的活人,经由各种数字设备转变成为平面的,被收集、推送信息和定义的“数字人”,列斐伏尔谈到,无数人在这个层面上博弈和竞争,苦苦挣扎求得生存的权利。
3.2 重建邻近:规划的社会价值
在这个进程中,由于距离的大量消失,邻近性接近死亡。空间的邻近性是社会生物性交往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邂逅、偶遇的基础,同时也是在信息网络时代中规划的社会价值的基础依托。工业社会的空间分区(建立空间理性与秩序)切割了随机的、无序的邻近性(它生产出冗余),但物理性并未消失,碎片化的邻近性(如在住区中,或者在公园里)仍然存在。信息技术时代,信息网络通过各类电子设备吸食个体的信息和喂养信息(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权力和资本集团监察、利用和左右),使个人沉迷和漂浮在电子符号纷繁的世界中,一个没有地方属性和时空距离的世界中。人通过“电子标签”在信息网络空间中建立没有空间距离的社会关系,抛弃了邻近性的价值,进而避免社会生物性的交往(“社恐”)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是不是此时可以更新和重写“齐美尔议题”,亦即“信息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篇章?列斐伏尔多次回顾了老巴黎街道上充满生活气息的状况,但他深知这个世界、这种直接的邻近性再也回不去。信息技术进一步导致和加速邻近性的死亡,也就意味着人的社会生物性的退化、社会团结的困难和日常生活状态的急剧改变。
列斐伏尔一直试图把握变化中的社会,不固化在旧有的概念和模式之中。列斐伏尔敏锐地抓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都市社会变化中的尖锐问题,并进一步可以说是独创性地发展了空间认识论。到了1980年代,当众多学者开始将关注点转向都市问题时,列斐伏尔最先意识到信息技术、社会控制和日常生活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又有新的认识上的“盲区”出现。社会洋溢着普遍的技术乐观主义(另外一端是怀旧主义),但对于信息技术带来的现实社会控制和日常生活状态的变化则缺少学理和批评性的认识。列斐伏尔先锋性地开拓了这个领域,他认识到信息技术应用背后的危险性,认识到国家前所未有强化控制社会,个人越来越陷入至深孤独。
列斐伏尔的学生曼纽尔·卡斯特在1989年出版《信息化城市》[11]、在世纪之交出版《网络社会的崛起》[12]《认同的力量》[13]《千年终结》[14],推进了信息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卡斯特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变动的时刻,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得以出现。民族国家的权力遭遇网络社会的严重侵蚀,但仍然是对抗全球信息网络的最重要力量;生产方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生产与消费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弹性重组;网络社会中劳动力极端两极化,绝大部分人成为可以被随时替换的一般劳动力,他们生活在激烈竞争的存在状态中(带来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危机,对象征的操弄、信息化表演成为权力显现出来的普遍状态)——卡斯特将其称之为信息资本主义。进而在信息技术时代全球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状态下,一种抵抗性认同出现——各种社群为寻求自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自发连接和团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它是今天各类合法或不合法社群,包括北美社会LGBTQ社群存在和引发各种争议的基本原因)。
列斐伏尔对于信息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分析是整体的和批判性的,城市规划需要直面其中的问题和矛盾——不仅仅将信息技术作为“实用技术”来推进和处理。信息时代的城市规划会有什么变化?它会转变成为更大范畴的“数据分析”的一部分吗?列斐伏尔提出的三种类型规划(物质的、财政的和时空的规划)在信息时代会趋向整合和一体化吗?国家层面的规划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强力监察和控制社会——和城市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又有什么关系?规划和各种集团的信息平台、掌控信息的政府部门是什么关系?在不远的将来,城市的、空间的规划和决策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吗?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够完全掌控空间吗?人的空间感知和经验与数据分析、规划与设计之间是什么关系?人群的集体性和介入社会主动性在信息网络时代又和规划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还有段义孚提出的,“什么样的亲切地方是可以规划的?如果无法规划,那我们至少还能策划人与人的相会吗”[15]167。最后是,列斐伏尔问到的,通信和信息不断增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会把人们引向何方?会给人们带来何种新秩序?规划在面对自身的转变时又与新秩序是什么关系?——许多的问题值得深思和探讨,要超越仅把信息技术当作实用技术;而列斐伏尔说,如果没有批判性就难有真正的创造性和质的发展。
未来将如何?卡斯特虽然讲“21世纪将不会是黑暗的时代”,但他似乎不那么肯定。在《千年终结》全书最后一节“终场”中,他提出了许多“假如”,进而谈到“或许我们能最终生活下去,爱同时被爱”[14]。这是一种希冀的美好愿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上看,文明的积累越来越强大,而个人越来越被原子化和陷入孤独。信息技术时代的来临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人类向来生存在一种“苦难的辩证法”中,只要自身仍然存在自觉、自发的意识,不把自己完全降低成工具,只要人的社会生物性仍然存在,希望就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社会变化有着高度敏锐性和批判性的亨利·列斐伏尔是微光中前行的引领者。或者说,列斐伏尔信息技术批判的意义不是指向文本阅读,不仅是一种书本知识,相反,它直指一种理论态度和认识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问题。只有超越喧嚣和故意制造的喧嚣(作为一种治理术),在认识真实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创造性实践的可能,才有超越只是增长而发展疲软的困境。
注释
参考文献
CASTELLS M,WANG Zhihong. The Space of Flow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06(5):69-87.
LEFEBVRE H. Espace et Politique[M]. LI Chun,trans.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
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M]. LIU Huaiyu,ZHANG Xiaoyi,ZHENG Jinchao,trans. Beijing: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8.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ume 3: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M]. YE Qimao,NI Xiaohui,Trans.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2018.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LIU Huaiyu,trans.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21.
CALVINO I. Invisible Cities[M]. ZHANG Mi,trans. Shanghai:Yili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2.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TIAN He,trans. Nanjing:Yili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0.
[9] 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BACHELARD G. The Poetics of Space[M]. ZHANG Yijing,trans. 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9.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 YAN Jia,trans. 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2003.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M]. CUI Baoguo et al.,trans. Shanghai:Yili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1.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HSIA Chu-joe et al.,trans.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2003.
CASTELLS M. The Power of Identity[M]. HSIA Chu-joe et al.,trans.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2003.
CASTELLS M. End of Millennium[M]. HSIA Chu-joe et al.,trans.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2003.
DUAN Yifu.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WANG Zhibiao,trans.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7.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在后台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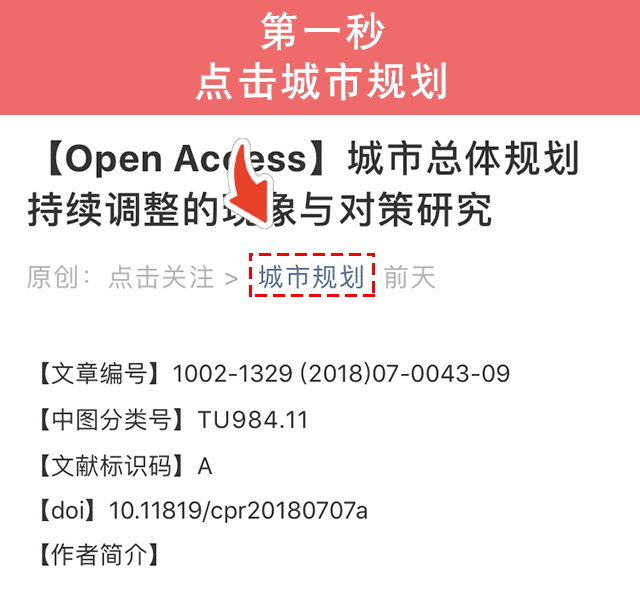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Open Access】至深孤独:信息技术、日常生活与列斐伏尔的批判——兼谈信息时代的空间与规划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