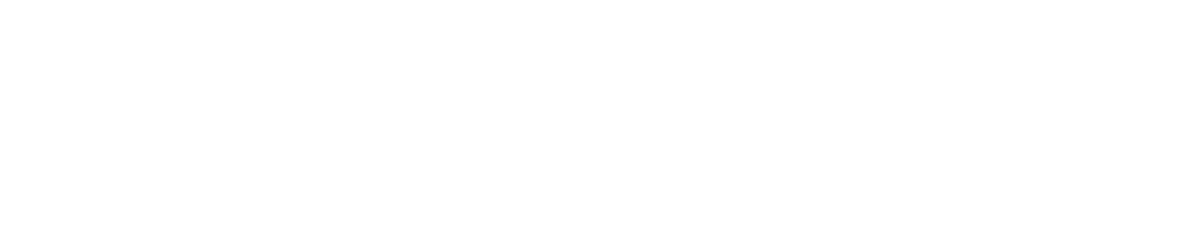

城市论坛第20期
安家落“沪”?城市包容与第二故乡的可能
本期活动简介请戳点☟
其他嘉宾发言请戳点☟
陈映芳:非常感谢三位分享,看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非常高兴,也很高兴一起讨论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今天三位嘉宾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了一些问题,那我想谈谈我的感想,还是结合我以前的研究。
有的嘉宾刚才提到了我的研究概念,比如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中国历史上曾经没有今天这样的“户口”身份制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了户口制度,很长时间内人不能自由流动。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开始,人可以在地域间自由地迁徙,包括到异地居住和工作了。关于户口的迁移,在五六十年代,上了大学,或者军队提干等也可以改变户口身份,但那个口子是非常小的。现在口子相对打开了,算是流动的社会,可是身份制度还在。而且今天几位研究者,比如李丽梅老师的分享告诉我们,制度设计是越来越精致了。还有一个概念,叫“地方公民权”,或者说“公民权碎片化”。从理论上讲,我们每个人在户口所在地都是有一套由国民身份带来的待遇与权利。但它是地方性的,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在其他地方,它是不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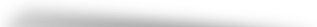


在这里我还想提到另一个概念,“移民红利”。今天大家围绕论坛的话题有点愤怒的情绪,但是又觉得是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是世界性的。确实,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红利在很多国家是被正当化的。但是在我们国内,不少学者也在讲移民红利,其实是“流动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在中国充满着诡异的味道。刚才听到,张璟航在讲自己的理性选择的时候,到哪儿去?到北京、法国、上海。她没有用“国际移民”概念,以及国际之间的流动迁移与国内的区别。刘老师则非常强调这一点。还有,上海现在是超大城市,超大城市不单单是规模的概念、人口的概念。这种概念背后是有一整套治理的制度跟进,超大、特大、中等城市、小城市的规划政策是不一样的,这是关键概念。
当我们现在讨论、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觉得愤怒或者无奈,那么问题在哪儿,分哪些层面,怎么来看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很多学者、公共舆论都在讲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国际移民制度背后存在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它有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在那儿。现代国民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是保障国民的平等公民权,包括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以及具体的社会权层面的平等,公民平等。刚才刘正强老师讲这个问题,他的愤怒,是很生动讨论了他在上海的个人感受。他同时也是个学者,他讲的是公民权问题。在中国国内,流入地政府只给国民支付碎片化的公民权,由此带来的“流动人口红利”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外来人员带来的人力资源活力给流入地城市带来了非常活跃的经济要素。这在一些学者那儿是作为正面的中国经验来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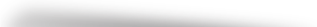


我在研究中还曾提出“身份市场”的问题,中国已经形成有种种官营的身份市场。现在国内讲社会流动,实际上主要是讲经济意义上的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开放,人们也可以通过房产市场获得合法的居住权。可是由于我们的公民身份被等级化、地方化,各地政府于是就在人们的流动和迁移中,设置各种隐性的地方身份交易规则:人们必须通过教育投入、房产投资、交纳地方性社会保险金等等,来购买城市的身份及其享受流入地公共服务的资格,包括居住身份、户口身份、职业身份等等,以此实现社会流动。近两年来二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纷纷推出“购房入户”等各种政策,加入这样的身份市场的竞争。
这样的身份市场上的流动,看上起像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之间的移民。但我们是在一国之内。现代国家是国民共同体,行政区域间没有关税壁垒,各地的自然资源被规定为国家所有,山西的煤矿资源用以上海工业,这是经济上的共同体。我们的军队、甚至包括消防队伍、武警,人员都是来自全国的义务兵,这是政治的共同体。但是在社会权层面为什么有这样的阻隔?这涉及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层面上的有些问题,不光是上海的问题,它同样是北京、深圳等全国各地城市的问题,一些制度是国家层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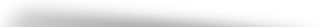


今天隐含在户口、身份问题里面的公平问题令大家感到困惑。刘老师也讲到法律层面有很多混乱,还有人们在流动中切实感受到的不公平。李丽梅老师讲到了“谁可以拥有城市权?”的问题。在近一千万的上海流动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拿到“居转户”。但是不公平的制度不限于“居转户”制度。在座的高学历者不一定能感受到,在会场之外的那些建筑工人,“居转户”这样的制度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公平?我们的大楼都是他们建造的,但他们连人才居住证都拿不到,他们不是居转户的政策对象。这也是一个社会不公问题。
此外,大家讨论的“不公”问题,其实还涉及到了另一个层面:规则的不公。既然城市政府搞身份市场,那这个身份市场里的交易是否公平?市场应该公平交易、规则清晰。家里几代人的投入,是否能获得相应的产出?从小到大,从学前教育到读硕、读博,中国的高学历者这些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化的教育竞争胜出的,包括海归博士。但是,这么高的教育投入,在流入地购得的,可能还只是“居住证”或“集体户口”、“公共户口”等等碎片化、不完整的身份,还要再购房投入才能获得“本地常住户口”的居民身份。很多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觉得这样的交易不够公平,教育投入与地位获得不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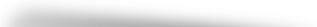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不确定性的问题。现在城市里的种种规则,撇开合法性,人们姑且“认”下来,结果还是不确定的。因为制度经常在变,难以预期。李丽梅老师在论文中讲到,数据的变化背后是政策在不断的改变。比如婚姻移民的期限总是变化。还有购房,以前买了房子就可以拿蓝印户口,后来不行,要人才。有关部门的领导公开对媒体说,人才是以后的购房预备大军。果然蓝印户口很快取消了。现在购房政策更是年年在变。公共政策的多变让人们对选择的结果难以把握。
今天我们论坛的主题叫安家落“沪”。 “家”的意味是什么?除了房子还有家人。在西语中“family”很多时候意味着“孩子”。现在投亲政策上大城市有很多限制。另外,刚才几位讲到,不知道以后自己孩子能得到多少,能得到什么?这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有的专家学者在讲中国的城市对家庭是不友好的。这不单单是城市问题,现在乡村的家庭处境也是不好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无奈。很多人因此就考虑出国移民。现在国内的身份迁移市场,迁移者的投入成本的社会权收益,有时甚至已经不如国际移民了。我有的学生在其他地方读了大学,然后来上海读研究生,留在上海,建立了小家庭,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是,父母亲怎么办?孩子以后的教育怎么办?好多问题难以解决。最后他们选择了移民国外。起码,他们的子女教育,以及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养老,在有些移民国家是可预期的。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政府多在规划如何吸纳全球人才,要我说,中国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自己的人才留住。中国现在大概是全球最大的“头脑流出”国家,最优秀的大学的毕业生成批地外流。当政府在国内经营身份市场的时候,你事实上就进入了全球身份市场的平台。道理很简单,市场上通行的是理性人原则,既然在国内同样要通过教育投入、房产投入等等来换得城市的身份权利资格、和家庭生活的保障权,那么人们就会在北京、上海和悉尼、洛杉矶等等城市间作理性的选择。在全球身份市场的平台上,中国的大城市没有多少优势:我们空气不好,食品不安全,教育有很多问题,看到小孩那么辛苦地读书家长都心疼。而且可能同样的投入所获得的身份权利还是不一样的。移民海外不容易,但如果能拿到绿卡,不少国家的绿卡意味着永久居留权,而我们这里的居住证还只有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的有效期。
今天在这讨论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我们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我们不要羡慕其他国家的公民权是哪儿来的,公民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生活者公民化的成果。今天的讨论,也是我们大家在朝着我们想要的生活,努力行动的一部分,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城市论坛往期回顾】
5年,20个周末,相聚在“我们的城市” | 城市论坛二十期记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