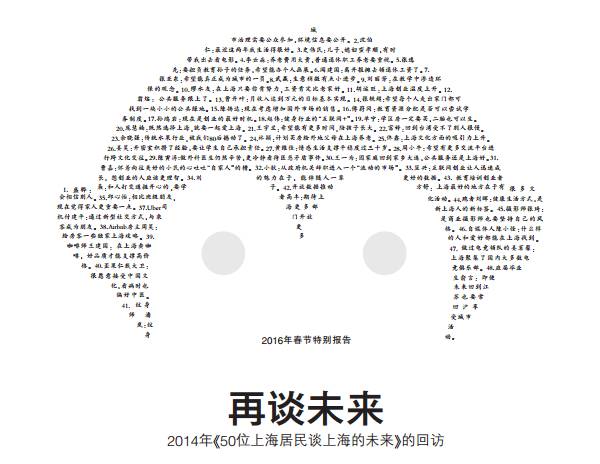
从年近古稀的老人家,到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人,这里是他们在上海留下的一些故事与心声。
在谈论公共政策的宏大命题时,我们并没有忘记,之所以谈论这些,都是为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人。
两年之前,我们曾请50位上海居民谈论自己的生活、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生活的多样性,也看到上海的各种时空脉络,进而意识到,我们也正与这座城市一起,处于时代的浪潮之中。
两年之后,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结合,“互联网+”浪潮带来的冲击,以及宏观的经济形势,等等。
那么,人们对这些情况又有怎样的感知?我们试图寻找曾经采访过的这50位上海居民,希望能对照这两年的印迹,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观察与思考。
但我们最终发现,无法如愿找到所有人。
比如,其中有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罗森店员。接受采访时,她21岁。那一年,她在上海从学生变成店长,工资也翻了个倍。她对我们说,上海让人有想学习的欲望,虽然舍不得这里,但过年后不会回来,毕竟家里有父母,未来希望能在老家创业。她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请我们不要写出她的真实姓名,因为这违反店里的规定。后来,我们真的没有再见到她。不知她在老家是否安稳,是否还想回上海打拼。
有的人则拒绝了我们的回访请求。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先生,表示自己并没有取得更高的成就,不愿意再说什么:“还没有当上基金经理。”当然,这可能是句玩笑话。人生向上的速度变慢,或许只是个人进入了平稳过日子的轨道;但一些金融机构这两年来日子确实不好过。而有人则是另一种情况,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他的生意渐渐做大起来,而他却对我们表示,没有时间接受回访——可能的确是太忙了。
还有一些人,比如在地铁站里收报纸的老奶奶、帮助管理交通的协警。当初,我们总能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遇到他们,但如今我们甚至不知他们是从哪天起从身边消失的。我们知道的是,人们早已不在地铁里看报纸,在人行横道处也安装了自动提醒不要越界的电子设备。
还有一个令采访对象失联的原因,它与技术进步有关。两年前,有一位先生的号码存在当时的手机中,因不是智能手机,转移通讯录不便;要回访时,才发现旧手机或因闲置过久,已无法开机,联系方式也无法查看。这才意识到,有这么多人用微信,不过是一两年之内的事。
只有重新检视才能发现,那些潜移默化的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
最后,我们重新采访到35个人。这就是上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结识很多擦身而过的人,但你们可能只有一次聊天机会。
我们发现,两年还是太短了些,无法承载人们较为长远的期望。环境、教育、医疗、养老、交通、房价,这里的每个问题,都包含着人们最为紧迫的需求,但或许又需要从长计议。
两年来,不少人立业成家,生儿育女,开始与孩子相关的环境、教育问题而焦虑。这正是城市最需要关切的未来。至于老人们提到最多的养老问题,对上海而言更为沉重,但这一代人的福利又必须得到重视。
互联网把一切相连,小个体户时代就此来临——这一两年里,人们普遍对此有了一定认识。不过,对所谓互联网经济,仍有很大争议。譬如,有人刚从国外回来,发现打车软件拒载严重,体验很差却又不得不用。眼下,国家层面的相应规制还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波创业热潮中,有行动力的年轻人,不仅有所收获,还获得了更多自主性。两年前,一位健身行业从业者,希望做一个永续经营的健身房,希望能有部门给出行业标准;如今他已经参与打造了一个移动互联网平台,借此不仅把小型机构串联在一起,还自己尝试推进行业标准化。可谓不必求人了。
不过,创业看似热闹,显然也并不轻松。有年轻人两年前做了一个分享梦想的平台,目前还在这条梦想的路上继续追逐,继续尝试创新。
创业也不都是平台经济,有时也意味着,一个人在打工之外,获得了另一种身份认同。譬如,我们看到,教师可以是公益人,亦可以是小业主。这两年来,他们在不同向度累积方法和经验,相较其他同事,在心理上更为自由独立。他们也让我们看到某种希望所在。
正因这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变化,我们特地找到一些人,他们与这两年来新出现并兴起的业态、文化、生活方式等紧密相关。对新生事物,固然要探讨如何完善机制,我们也希望能去往其内部,寻找新奇。
可以粗略做个区分。这些人之中,有人是面向线下消费者来生产,不那么依赖互联网平台,比如咖啡师、纹身师、摄影师、教育培训创业者;有人依托更大的网络平台来做个体户,同时也享受与人交往的过程,比如Uber司机、Airbnb房主、自媒体人;有人代表了新的消费趋向,对城市空间、文化等有更高的需求,比如应届毕业生、外国人、跑者;有人相当于从事网络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开放数据推动者、电竞领队。
这种区分也并不绝对。这些生产和消费环节互有交叉,在城市中形成了很有意思的生态链。他们也有那些所有人都有的期待,但我们也能注意到,他们对城市里的一些要素更加重视,比如空间体验、文化趣味、有序开放等。一边在酝酿,一边在享受,这就是新的力量。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