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这是我第二次随驴友团一起出行,犹记得第一次的出行,是赴东冶镇的三盘山,中途由于迷路,我们竟一直穿行在大山的悬崖峭壁间,其间的惊险与劳累,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好在平安回来,却也因此而不敢再轻易报名参加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驴友们将组织赴三窑换粮古道的徒步活动,又一次激发了我的野外探险的热情,更由于对这条承载着七十年代阳城人苦难历史的换粮古道的浓浓兴趣,于是,我便毅然报名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而正是在对这一古道历史的追寻中,我深深地感叹老一辈人艰辛的生活历程,同时,也更加感到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呢?

到河南换粮路,从阳城开始总共有三条:一条是经横河镇过磨石渠隘到河南省济源邵原;一条是经杨柏乡过莲花隘到河南济源的王屋镇前堂,但走的最多的是这条从阳城县城的窑头村起,经安阳村,过白桑、台头的东樊、涧坪到东冶的孤山,过刘腰村、上大岭堂村,越过白云隘下太行到河南济源的交地村。这条道路创建年代不祥,有人说在战国时,这条道即被称为”韩魏之要衢”,若果如此,则这条古道更显得历史之悠久,而现存道路则是清代遗存,老人们常称这条道路为“上15里下15里”,可见其路途之漫长与艰难。

清晨七点将过,我们一行整装驱车出发,具体路线是从阳济路三号隧洞处上大岭堂、下刘腰村、过桃园沟,最后抵达孤山村。汽车沿着阳济路前行,人们坐在车内,有的兴奋地一路调侃着,有的则乘机弥补一下早上未睡完的觉。坐在窗边,看着沿路的景色,心中有点忐忑不安,不知此行的山路是否会如上次前往三盘山时的险峻,倘若如此,我又是否会坚持的下来,又一想,先辈们能担着粮食行走,我又怎么不敢走呢?心放下来的同时,我不免又感慨起世事的变迁,当年,先辈们因为年年歉收,不得已从各村赶赴安阳,带上本地的特产,大多为瓷器、砂锅、木头等,然后沿着这条古道南下济源,换上粮食以养家糊口,而这种行为大约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因此,人们也只能是偷偷地进行,很多时候都是半夜就出发,换上粮食又要连夜赶回来,不能耽误第二天干活,这其中的辛酸与艰难,也许只有那一代的人们可以体会到。

在胡思乱想中,不知不觉,车已到达目的地——三号隧道。笔直的阳济公路,硬生生地将这条古道截为两段,路左是高耸云端的太行山,路右则是古道的未梢——交地村。古道与现代化的公路在此交接,现代化的公路可以将那条先辈们为了生存而被迫行走的古道截断,然而,又怎么能截断那一段苦难的历史?当这一条古道从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甚至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时,我们重走这一条道路,不仅仅是为了重温那段苦难的历史,更是为了永远记住那些为了生存而艰难奋斗的人们,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有这样的苦难,为了珍惜我们眼前的生活!

从三号隧洞往大岭堂走,起初的一段路还是非常狭窄崎岖,道路也较陡,好在我们刚起程,体力正是最盛时,走起来倒也并不觉得累。虽然已是三月天气,然而满山遍野望去,依然是枯枝衰草,一片荒凉。

这儿的古道保存的较完整,道路沿太行山山势修建,由于地势险峻,修建困难,很多地方的道路略显窄狭,有的仅有一米宽,弯弯曲曲地盘桓在山间。

走过了前面一段较陡也较窄的道路,转过几个弯,远远的就能看见大岭堂了,像个雕堡般地屹立于最高峰,海拔在一千余米,人们也将大岭头称为“云天山”。山里的气候和山外自是不同,虽然道路两侧依然是荒草萋萋,然而有的小树已盛开了艳丽的小花,尤其那半山腰处的山桃树更是开满了白色的花朵,将整片荒岭点缀的生机盎然。

在半山腰处稍作休息,也是为了等待后面的驴友。山路虽然并不难走,天气也并不炎热,然而对于并不经常野外徒步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条艰难的路了。驴友们在此调整一下,补充点水份,领队曾在孤山村居住过几年,对这儿也比较熟,自然也成了我们的向导。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集中了驴友继续前行,这儿的道路稍为宽阔,距离大岭堂也越来越近了,从这儿可以看见在山尖上插着几面红旗,那是驴友们所留下的印迹,而沿途中也随处可见有驴友们所做的各种记号,这让我们在行进中感到了一股暖暖的温情。

历尽了辛苦,终于抵达了大岭头之巅,在这儿,又怎么能不留影呢?人们将这儿称为大岭堂,向南开始下太行进河南,向北便融入沟壑纵横的太行山区,历来是兵家重地。

转过大岭堂,是一段石阶,站立在此,远眺群山,层峦叠嶂,群山环绕,山谷间烟雾迷蒙,宛若仙境,令人心旷神怡。这儿是先辈们暂时休息的地方,老人们也将这里称为“歇场”。

再往前行不远,我们来到一处险要的关隘处,老人们将这称为“仙人桥”,这座石桥平地而起,将两边的高山相连接,石桥两侧则是深不可测的深谷,让人在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也不禁胆颤心惊,太行山的气势也在此展现的淋漓尽致。据说这里原来也有个拱门,巨大的岩石上还留有人工刻凿的痕迹,在冷兵器年代,这可是个重要的兵家要地。

过了石桥,前面的古道时好时坏,两侧的低矮的灌木枯枝相互交错,将古道掩映在其中,道路上碎石遍地,显得凌乱不堪,向世人展示着曾经的历史,与世事的沧桑。

沿着荒凉的古道一路前行,终于来到了大岭堂村,也叫刘家坳,是在大岭头山顶南侧,其修建于何时已无法得知,想来因为此古道历来为南下中原之要道,起初驻兵于此,当战火过后,姓刘的人家便迁居于此,逐渐发展成一处小村庄,在村旁还建有古庙。如今的大岭堂早已荒废,唯剩下残垣断壁,仿佛时间就在此刻凝固。听领队说,这儿也是往来行人的歇脚处,人们来到这儿,就在此补充给养。当然,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开旅店的,但不知道是哪个聪明的人以孤山大队的名义开了个颇有无产阶级倾向名字的店铺“留人起火店”,其实也就是一个村办客栈。住宿的一晚上2.5角,一顿饭另加1.5角。

听老人们讲,就在这个“留人起火店”里,曾经发生过一个凄惨的故事。在阳城的某个乡村,有个小伙子刚刚结婚不久,由于家中实在揭不开锅了,只好担锅换粮。当他担了一担砂锅经过几天的行程来到大岭头,就在下山途中,连人带锅掉下山崖。虽然人没有事,所挑的货物却是打了个粉碎,小伙子懵了,又不敢空手回家,他咬咬牙,只身来到济源城,一次性卖掉了身上800CC的鲜血,用鲜血的钱换来了一担杂粮,虽然体乏疲倦,小伙子还是鼓足力气一股劲从山下回到大岭堂村的“留人起火店”,也许是几天没有吃饭,但更重要的是卖血过多,小伙子到了店里放下挑担一股气喝了一马瓢的冷水,一头栽倒床上就再也没有起来。噩耗传到小伙子家乡,小伙子的妈妈和新婚的妻子从遥远的家乡来收尸,妻子抱着小伙子的尸体哭了一天,诉说着自己不该让男人出来换粮,一天后妻子神经错乱扬长而去,据说前几年乡人还在县城的街上看到过这个可怜的女人。最可怜的是老母亲,守着自己儿子的尸身,看着儿媳崩溃而去,刹间双眼看不到任何东西。据说最后还是一位好心的过路人把母子俩一活一死的送回家乡。凄惨的故事让人唏嘘,也更让人深切体会到先辈们为了生存,而挣扎、而从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

从大岭堂出来,怀着一颗复杂的心情,往山下走去。不久,就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前几年河南人在此开采铝矾土,将整座山挖的是千疮百孔。我总在想,我们的古人靠山吃山,却只是享用大自然恩赐的东西,无意去破坏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了青山绿水和丰厚的资产。然而,我们现当代人,却为了个人私欲,肆意地向大自然索取,不知道,我们又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些什么呢?

顺山而下,这儿的古道大多已不复存在,如今的这条道路是一条乡村土路,很多驴友为了省劲,便驱车从孤山村来到刘腰村,然后再从此徒步上山。刘腰村,掩映在乡村路旁的半山腰处,旧时,也是来往行人的必经之地。古老的槐树只剩一半还屹立在村头,另一半躯干前些年不知何原因已倒在一侧的路中,一如村内的居民一样,逐渐消失在了历史前进的浪潮中,唯有残留的院落、石磨还在坚守着那些曾经的辉煌。

拖着疲惫的身子,我们一行驴友来到了桃园沟,山脚下有几处清泉,泉水清澈见底,一群群野生小鱼在水中悠闲地游着,我们无意过多地打搅它们,只是简单地洗了一下手,便又匆匆而行。路旁的老人静静地守护着他的羊群,身旁的家狗摇着尾巴,怡然自乐,仿佛一幅中国山水画,恬静安谧。

终于到达了孤山村,偌大的广场在午后的阳光下空旷而安静,几位村民围在一起,看着机器加工着被子。阳济公路将孤山村一截为二,一辆辆运煤车在轰隆隆的鸣叫声中从孤山桥上扬长而去。而路一侧的那座山峰在远处的高山下,显得孤单而矮小,孤山村也因此“孤山”而得名。

孤山脚下,有一处旧道观,山门上的木匾依稀可辩“化雨频施”四字。以前在游玩一些普济寺时,总想着佛要普度众生,又是如何去普度呢?我想,大概就是“化雨频施”吧,将一切的恩德化作雨水,经常地施舍给人间众生吧。

在孤山村里,我们一行人就在领队的亲戚家中简单吃了一顿饭,老人家早已将饸饹面和好,院子外支起了一口大铁锅,用木柴烧着火,又炒了一锅白萝卜菜和酸菜,虽然只是简单的农家饭,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山村农家温暖的情怀。我想,这儿的大多居民世代居住于此,看尽了旧时换粮人的艰辛与苦难,虽然淡泊了人世间的名利,然而留在他们身上的,永远是那份质朴与热情,还有对世事的洞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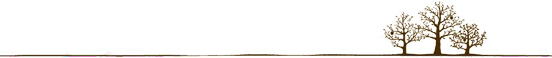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