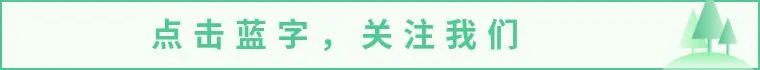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产,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解决好农民问题,现阶段关键是如何处理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问题,实质是能不能把土地的财产权利完整赋予农民,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一、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长久不变
改革是亿万农民的创造,是从农业发端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成员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从改革初期的试点,到明确承包期15年,再到延长承包期30年。党的十九大又明确在30年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那么土地承包期究竟是多少年,15年与“两个30年”承包期是何关系,相关政策如何衔接?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普遍关心的问题,又是认识不一致的现实问题。认识不一致,导致对政策宣传、执行不一致。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30年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确认,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期限,由1984年规定15年,经过1993年到党的十九大两次将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一共是75年。每次顺延的只是农户承包土地的承包期限,不是按当时人口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因此,在第一个30年承包期到期后,顺延的仍将是土地的承包期限,而不是、也绝不应该按未来的农村人口打乱重新承包土地,这一点必须坚持。在30年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将承包期(关系)直接顺延30年。不能按农村实有人口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否则,就不是土地承包关系的延长,而是重新发包。
二、二轮到期后不应按照农村人口调整土地承包关系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是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土地,不得调整土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能因不同农户家庭人口增加或减少而调整。
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关系不能、也不应按照未来的农村人口调整土地承包关系。第一,土地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不能随人口的变化调整承包关系。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变为集体所有、农户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为了稳定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预期,早在1994年,党中央就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提倡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不得收回承包地。这就排除了在承包期内随着不同农户家庭人口的变化而调整土地承包关系的可能性,从而使农民对土地有相对稳定的财产权,对土地的使用有稳定预期。第二,不同农户承包经营集体土地起点是公平的。虽然在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但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土地承包时,不同农户家庭在册人口,不论男女老少,人人都同样获得了承包土地,起点是公平的。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经营制度的变化对不同农户在制度、规则、机会上是一样、是公平的。这也是我们所应该且能做到的,我们只能做到起点公平,而不应该、也没办法实现结果公平。否则,农民对承包土地就缺少稳定预期,就会失去有效激励机制,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第三,农民获得的承包土地经营权是用益物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承包农户的绝对财产权利。这个权利已经确权到农户,本质上是不可以调整的。一旦经常性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就缺少稳定感,收益权就更没有保障,就不会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三、现实中农村调整承包土地的动因
虽然从道理、政策和法律上讲,不应随人口的变动调整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但在实践中,确有一些地方随着人口的增减变动不断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深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认识不足。由于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不了解,有的干部群众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就是农村人口人人都有份。不知道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归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只有成员才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才有资格承包经营土地。实践中,由于在农村一直没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就形成了“爷爷是成员,子孙后代都是成员”的习惯认知,农民从朴素的感情上认为,是农村人口的都有权利承包集体土地。
第二,不同农户对已有土地调整产生心理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对土地承包政策理解不到位,导致不同农户间由于人口变动而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原来分地时家庭人口少、现在人口增加的农户一定要求得到土地,否则就觉得自己吃亏了,甚至在村里会抬不起头来。这种情况下,农民追求的与其说是获得承包土地,不如说是追求权利平等的心理平衡。
第三,获得土地无成本支出。由于农村土地从法律上讲是集体所有,但对集体的含义又缺少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一个家庭只要父母是成员,其家庭新增人口就自然是集体成员,就可以同等地享受成员权利,无偿获得集体土地。实践中很多地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导致了农户家庭人口增加就要求无偿获得集体土地。如果农户家庭新增人口想获得集体土地,需要付岀成本,多数农户则是不想多要承包土地的。
第四,在不同农户间调整承包土地,可以体现村干部的权力。
第五,对社会公平缺乏正确理解。有一种看法简单认为只有按不同农户间人口的变化,不断调整土地承包关系,才能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公平。在财产占有方面,讲究社会公平,只能要求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而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结果公平。在当初承包土地时,一个集体经济组织范围的不同农户家庭,凡在册人口,不论男女老幼,人人都得到了相等的承包土地。有资格承包土地的个人,每人得到的承包土地的数量是相等的。土地承包的操作机制对不同农户是一样的,起点是公平的。这样就不需要再随着家庭人口增减调整土地,否则会引发新的不公平。
四、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强制收回
随着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城乡人口迁徙变化越来越多,农民全家迁入城市落户,家庭承包的土地是否应当收回?这是农村承包土地政策落实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用益物权,是财产权利,农民全家迁入城市落户,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予保留,不能强制收回。
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与当地原有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同对待当地原有居民一样,对他们的入学、就业、粮油供应、社会保障等一视同仁。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人员的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由其原所在的农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收回,凭收回承包地和自留地的证明,办理在小城镇落户手续。岀台这一政策规定的制度背景是,当时我国虽然已经开启改革开放,但仍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城镇居民的就学、就业、医疗、住房、生活品供应等由国家负责,按计划平价保证供应。而农民的事情则由农民自己解决,突出表现在农民生活以土地为基本保障。因此,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要有一块家庭经营的土地。农民一旦在城镇落户,需要办理转移粮油供应关系,由国有粮食系统负责供应,其生活保障则由政府负责提供。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才规定到城镇落户的农民应当交回承包土地。一个家庭不可以既在城市享受国家提供的生活保障,同时又在农村拥有一块作为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土地。
目前,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特别是诸如城乡居民户籍制度、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等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多数城市已经取消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居民登记制度,而且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待遇基本消失了。政府也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到城市落户,农民到城市(镇)落户后的就业、住房、生活保障等早已市场化,完全由落户农民自己解决。作为公民有选择居住地方的自由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用益物权,是财产权,不能因为农民到城镇落户居住,就把农民的财产权没收了。于是,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对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不再办理粮油供应关系手续;根据本人意愿,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也允许依法有偿转让。可见,这时农民进城落户政策已经与收回进城农民的承包土地脱钩。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能让农民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进城落户条件。党中央、国务院这一系列政策调整,就是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赋予农户的财产权利,不因农户到何地落户而受到剥夺。
令人欣慰的是,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有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这一法律规定体现了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保护原则,对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结语
选择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归根结底是要看哪种制度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够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作者简介

内容有所删减、改编,未经原文作者审核,完整内容请阅读原文。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谢谢!
本文着重标记系编辑为便于读者阅读而添加,与原文作者无关。
审核 | 王健
编辑 | 吴昭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土地学人):【争鸣】黄延信 | 怎么理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的延包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