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针对自然保护地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于2019年6月正式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总体部署,要求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此同时,目前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对空间资源要素实现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密切对接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管控要求。在此背景下,针对目前成都市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以期为成都市自然保护地构建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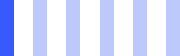
我国所建立的各类型、各级别自然保护地在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有的体系存在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管控,2019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进一步厘清了自然保护地各项主体功能及关系体系,明确了我国下一步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工作的方向和路径。成都市目前已经成立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作为市域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归口管理单位,下一步需要在国家部署要求指导下,构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实现对自然保护地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
本期前沿通过梳理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及管控内容,借鉴国外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及管控方式,并搜集国内现有的研究思路进展,为成都市下一步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工作提供思路。
2 成都现有自然保护地梳理
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提供的《四川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名录》为依据,成都市域内共涉及7类26处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1处,自然保护区5处,风景名胜区9处,森林公园7处,湿地公园2处,地质公园1处,世界遗产1处。按照国家出台的最新要求梳理,若将现有自然保护地进行直接转换,构建成都市新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定义与国家最新提出的自然保护地定义不统一,不能直接转换。根据《意见》,自然保护地定义为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成都市主要涉及的7类自然保护地,其定义与自然保护地最新定义存在不一致之处,有必要根据国家的最新要求对原来按各类资源及利用形式设立的自然保护地进行体系重构,而不能只是进行简单的直接转换。
二是由于机构改革前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各类公园分属于不同系统,缺乏统一的协调,导致在空间、标准、管理等方面存在矛盾冲突。在空间方面,目前成都市域内涉及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约60%的空间存在交叉重复。如成都市域内大熊猫国家公园与多个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在空间上交叉重合(图1)。在管控要求方面,目前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等都按照各自体系要求实行分区管控,分区标准及管控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在数据信息管理方面,目前由于各地自然保护地未建立统一的数据信息管理平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各类公园使用坐标系标准不同,导致部分自然保护地在坐标转换后出现边界偏移的情况。
三是按照国家自然保护地的最新要求,现有统计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各类公园等可能未完全包含所有应当保护的区域。《意见》中明确要求,将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系统脆弱、自然生态保护空缺的区域规划为重要的自然生态空间,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因此需要对成都市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系统摸底分析,摸清是否存在部分具有价值的自然生态环境未包含在现有的体系中,确保落实国家“应保尽保”的要求。
3 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
及管控的国外经验借鉴
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经验
(1)以保护最具特色与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对自然保护地的定义是目前全球公认的官方定义,即自然保护地是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经由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得到认可、承诺和管理,以实现对自然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1]。自然保护地因此含有了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第二它代表了全世界最丰富最具价值的自然资源。IUCN采取各国使用的类别体系中的“共同语言”,构建了全球通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形成了以保护最具特色与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的6大类7小类保护体系。
目前多个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自然保护地体系与IUCN的国际通行标准进行了对接,在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中基于目标管理的思路,清晰界定了自然保护地的定义及功能。我国既有的基于资源分类保护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与自然保护地保护目标及功能定义存在不一致之处,在本次梳理过程中,应参考保护最具特色与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国际标准,重新明确各自然保护地保护对象、保护目标及保护要求。
(2)明确划定标准及划定方法,科学确定自然保护地名录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是以大量准确、详实的资源调研为基础,通过科学、合理的划定标准、方法,综合确定自然保护地的体系及名录。
美国经过多轮规划和研究,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国家公园设立指导准则及标准[2]。美国国家公园的入选标准包括4点:国家重要性、适宜性、可行性和国家管理的不可替代性。其中,国家重要性对于筛选自然保护地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具体要求为:①是一种特定类型资源的杰出代表;②对于阐明或解说美国国家遗产的自然或文化主题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③可提供公众“享受”该资源或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好机会;④资源具有相当高的“完整性”。
澳大利亚提出“CAR”保护指导框架指导自然保护地的筛选识别,即自然保护地体系应满足综合性、充分性和代表性。基于“CAR原则”的指导,澳大利亚对国内现有国家保护地生态、景观与物种的综合价值和分类价值做了定性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保护地的定义并根据其价值制定了新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目标;对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开展普查,分析其自然资源的规模和特征,制定新的保护标准并研究划定相应的保护领域;基于物种、生态和景观类型对保护地做了分类并根据分类进一步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在完成国家保护地定性、定量与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了《澳大利亚国家保护地体系规划》,明确了国家保护地的名录、范围及保护要求。
各国由于资源要素、特色的不同,其自然保护地划定的标准各异,因此划定标准、方法的研究应基于本土资源特色。如成都市目前风景名胜区数量多达9处,每处风景名胜区资源类型、特色各有不同,难以对其进行统一的划定,应在资源统一调查的基础上,明确划定标准及评价方法,分类讨论每处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对其作出准确判定。
自然保护地管控经验
(1)实行自然保护地差异化分区管控
分区管控是各国实现自然保护地有效管控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的三分区模式,即“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core/buffer zone/transition zone)”模式,是世界范围内关于自然保护地管控分区的最早的指导性标准[4]。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根基于分区管控的思路对自然保护地实行用途管制,将分区空间与用途管制进行了良好对接,并且对各个分区中的主要功能、建设行为、活动类型等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并且在管理方式中采取了许可的形式,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又留有一定的弹性,保障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美国提出的分区类型主要基于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包括重点资源保护区、低利用荒野区、分散游憩区、密集游憩区和公园服务区,各自然保护地可根据实际需要以此为原则确定具体的管控分区[5]。以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为例,优胜美地公园在土地管理分区方面,将公园分成自然区、文化区、发展区和特殊使用区四个大区。
澳大利亚提出的分区制主要基于人类活动强度划分8个分区[6]。大堡礁国家公园的分区制度详细阐述了各个分区中允许进行的活动,规定了游客的活动范围和内容,实行旅游经营许可证制度。
加拿大将国家公园按其需要保护的情况和可对游人开放的条件,以资源状况为基础来划分成不同区域[7]。为了保护和利用的双重目的,加拿大国家公园通常划分成特别保护区、原野区、自然环境区、户外游憩区和公园服务区5个区。
(2)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及数据库,实现统一规范化管理
在自然保护地信息数据的基础上,形成自然保护地数据信息库,作为开展自然保护地系列工作的基础。数据库的建立一方面便于对自然保护地所包含的内容(范围、功能等)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也利于对自然保护地的动态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测和评估,能保障对自然保护地长期、持续的保护及开发利用。
美国针对国家公园形成基础性文件数据集(Foundation Document,简称F.D),以此为基础指导国家公园的规划及管理决策。基础性文件包括公园设立的目的、建立的意义、核心资源及其价值、代表的主题、公园地图集、规划评估要求等[8]。
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每两年向州和地区政府以及其他保护区管理收集有关自然保护地信息,整合更新澳大利亚合作保护区数据库。数据库主要用于从国家层面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统一管理,并且与国际保护地数据库进行对接,对相关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和报告。结合数据库定期更新,澳大利亚从物种入侵、物种繁衍、环境侵蚀度、环境酸碱度、森林火灾、采矿业开发、林业开发、畜牧业开发、旅游业开发9个方面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环境质量保护的系统评价,从而辅助国家保护地实施更科学的环境监管。
4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相关研究
很多学者参考借鉴国际标准及相关国家案例,提出了我国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归类的建议。如部分学者提出整合归类原则应为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弘扬民族文化,其中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风景名胜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地作用;也有学者尝试基于IUCN管理目标的思路对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梳理和重构;还有部分学者对具体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归属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认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代表了自然保护地的最高水平,应该划入最严格的保护分类,也有学者提出世界自然遗产地与保护地的关系较复杂,应该具体类别作具体分析。
自然保护地管控相关研究
部分学者结合国家要求深入研究了自然保护地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有学者研究自然保护地与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三线”的关系,建议自然保护地中的“核心保护区”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线”[9],同时应对原自然保护地边界进行优化整合,避免自然保护地的进一步破碎化。在用地类别对接方面,有学者建议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分类中,在“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基础上,增加“自然保护用地”地类,体现出自然保护地的资源特点和主导功能,同时便于自然保护地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在土地利用层面能够做到无缝衔接。
也有学者从自然保护地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包括:建议在当前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管理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自然公园,进一步研究其内部分区,根据其功能的多重性设置功能分区,并提出相应管理办法和措施;建议我国自然保护地建立科学评估方法对资源利用的价值、风险等进行评价,确定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方法;建议探索建立自然保护地内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包括在政策上制定必要的引导和鼓励措施,科学引导和控制乡村参与旅游业的规模和方式,统筹自然保护地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的协调和有机衔接。
5 对成都自然保护地体系
构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一是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开展,按照国家对于自然保护地的最新要求,对自然保护地现状进行统一系统梳理。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背景下,以“三调”为契机,结合成都实际,对自然保护地现状进行系统梳理,统一组织开展、统一法规依据、统一调查体系、统一分类标准、统一技术规范、统一数据平台,摸清类自然资源底数,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对全市自然资源开展系统性的自然保护地综合评估工作,指导下一步制定各类自然保护地划定的标准要求。
二是在对成都市自然资源特征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根据自然保护地综合评估结果,统一分类标准及管控要求,基于管理目标的思路系统统筹自然保护地体系,落实并对接国土空间的相关要求,编制自然保护地专项规划。针对成都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特点,有必要针对本地特征深入研究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划分标准与评估要求。结合划定标准和评估要求对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进行综合评估并重新定界,合理调整自然保护地范围并勘界立标,保障自然保护地不能越级减越少,同时解决空间交叉、重叠的问题,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借鉴澳大利亚统一指导,具体规划的发展思路,在完成统一的基础性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对各个保护地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明确各个自然保护地的具体发展目标、规模和划定区域。
三是强化对接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对自然保护地实现用地用途管制,重点协调自然保护地与“三区三线”关系,保障管控要求不冲突。在自然保护地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求深入研究其与国土空间管控要求的关系,在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的基础上,对接国土空间中的用途管制,明确自然保护地中各类用地用途,实现全资源要素的统一管控。建议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一般控制区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控制线,但具体用途管制还需根据更为详细的分区进行分类讨论。下一步,应深入研究自然保护地与“三区三线”关系,明确其空间范围,制定合理、适宜的管控要求,并保障两者管控要求互不冲突,相互支撑。
四是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国土空间数据管理平台,实现自然资源的统一管理,形成保护规划一张蓝图。将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纳入国土空间数据管理平台,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确定保护思路和格局,实现“总量+质量+布局”的全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将自然保护地土地用途管制相关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主动对接,明确各类分区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管控要求的对应关系,便于在管理平台中进行统一管理。
[1] 朱春全.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与管理目标[J].林业建设, 2018(05):19-26.
[2] 王欣歆,吴承照.美国国家公园总体管理规划译介[J].中国园林, 2016,30(06):120-124.
[3]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National Reserve System—Plan of Management Guidelines[R].Canberra, 2009.
[4] UNESCO. Task force on: criteria and guidelines for the choice and establishment of biosphere reserves[R]. Final report, MAB report series No. 22, UNESCO, Paris,1974.
[5] 梁诗捷.美国保护地体系研究[D]. 上海:同济大学,2008.
[6] 张妍. 澳大利亚大堡礁分区管理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J].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8(08):54-55.
[7] 张颖.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8(04):139-144.
[8] 杨伊萌.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发展新动向的启示[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沈阳市人民政府.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风景环境规划)[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沈阳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6:9.
[9] 闵庆文,马楠.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区别与联系[J].环境保护,2017,45(23):26-30.

(长按二维码识别就可关注我哦^-^)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沿信息】基于国土空间管控角度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对策研究
 规划问道
规划问道









